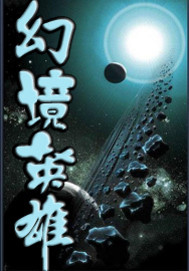柳开一睁眼便对上了一排尖锐锯齿,怔愣之间右侧臀腿处便传来一股撕扯般的剧痛,脑子还没想清楚自己一觉醒来怎么就到了哪头巨兽的牙口之间,人已经条件反射地往后滚去。
是一只半人高的狼狗,毛发长而乱地垂在地上,裂开口唇露出长而尖利的白牙,冲着自己示威,一看一击不成,抻着瘦长有力的后腿,打算再来一个冲刺。
自己大腿显然已被这畜生啃了一口,皮肉顺着破碎的裤布耷拉着,疼得人撕心裂肺。
柳开忍着疼往侧方柱子后滚去,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了这狗,让它恨自己如斯。
留意四周,才发现这是一座废弃的寺庙,地面上跌着破碗,几口米糠混着泥土,旁边趴着一个四脚趴地的人,蓬头盖面,不知生死。
怔愣间那狗又飞扑而来,柳开暗骂一声,手脚并用直接上柱,双腿死死盘住柱子与大狗面面相觑。也幸得这寺庙年久失修,原本光滑的柱子上掉了不少红漆,随着柳开的动作往下飞屑,惹得狗子汪汪乱叫的同时也为他借了不少力。
“好狗,好狗,真是对不住。不是我要抢你食吃,实在是我脑子不清醒,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大狗有大量,不要同我这个小人一般计较。”
“汪汪汪!”
那狗凶神恶煞地往上几个飞扑,几次险险蹭过她的衣角,还好她晕晕醒醒几个来回,总算是跟着跛脚老道学会了一些拳脚,打不过高手还躲得起一条恶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与狗抢食天理不容。但狗兄求你留点力气别再刨了,柱子断了不打紧,可千万东西没吃成反倒费了气力,划不来。”
地下传来一声嗤笑,狼狗被砸中了脑袋倒在地上抽搐,露出后头一张泥糊的脸。
那人踢了踢几下狗,“晕了。”
柳开从柱子上滑了下来,一靠近那人就被熏了个倒仰,“兄弟,几天没洗澡了?”
虽然她知道对初次见面的“救命恩人”说这种话有点不礼貌,但这兄弟身上的泥灰层次显然不是一天抹成的。
这人虽然身上脏污,却生了一双脉脉含情眼,看着你的时候闪闪发着光,若不是心态坚定的女子恐要生出多少离愁怨憎。
这人除了一双眼,一具干枯的身躯,浑身上下哪哪都邋遢。枯燥打结的头发,挂着米糠的长须,留着狗脚印的胸口衣裳.......等等!
柳开看了看一边的晕狗,又看了看一边摔了的狗碗,再看看那胡须上的米糠,左看看右看看,看来看去,心里就怒了。
满腔感激变冷,原来自己才是替人消灾!
那人似有所感,笑道:“听说狗不吃死物。”
柳开怒:“那是熊!”
......
动物油脂“滋滋”地顺着烤红的树枝滴落火焰,方圆五里飘着烤鹌鹑的香味。
柳开专心致志烤着晚餐,身后不断传来吞咽声。柳庭南一步步挪到柳开身后,讨好地磨蹭。
“柳兄,你姓柳,我姓柳,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就可怜可怜我,舍我一口肉吃吧。”
柳开对这位仁兄可伸可屈的行径叹为观止,将手上的两支烤好戳子拨给他一支。
柳庭南笑得眼不见牙,这位仁兄总算是在柳开的强烈嫌弃之下在水池边搓了一下午的泥,不得不说人长得倒是眉清目秀,也许是泥垢替他挡了紫外线,所以皮肤分外白皙,忽略掉那随着主人吃得一挺一动的下巴胡子,烫得龇牙咧嘴的仪态,倒是很招姑娘家的喜欢。
填饱了肚子,柳开抱着干草树枝铺在火堆旁边,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天亮了再赶路。
借着火光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饶是柳开心性再好,也忍不住叹气。
五年了,从她在酒店大床上睡过去之后再在这个世界醒来已经五年了。这是个农耕社会,她生在一个贫困百姓家,老爹不识字,是个本本分分的老黄农,母亲生她时伤了身子,变得痴傻疯癫,时不时“离家出走”,要柳开同老父到处寻找。
虽然家中贫困,但柳开从不怨天尤人,本以为既来之则安之,结果老天却不断和
她开玩笑,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她得了个“怪病”。
她八岁那年一觉醒来便到了十二岁,一觉直睡了四个年,说她昏迷成了植物人倒也不尽然,身上的肌肉没有半点萎缩,老父半点没有“老伴疯癫,小女重病”应有的悲惨,再结合乡里乡亲毫不知情的态度,这几年竟像是有人直接借了她的身体,替她吃喝拉撒,孝敬父母,帮她活着。
如此奇异惊悚的事在第二次长达两年的入睡之后,柳开含着泪接受了。心中又多了几分庆幸。
好歹在现代“娇生惯养”二十四载,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这一睡倒是能少受一些苦。
包裹中有两个元钱,是醒着的这几年在书孰帮忙教书攒来的。估算了下距离,她离国都大约七十丈,扣除吃喝休息时间,靠着她一双腿,走个三天三夜应当能够到达,一个元钱能买三十个大饼,另一个元钱等到都城时添置一些笔墨纸砚,挨着挨着也就到了。
打定主意,柳开打算靠在火光旁入眠,至于下次醒来是什么时候——反正她担心了也并没有什么用。
草堆的干燥枝杆传来被碾磨的“嘎吱嘎吱”声。
柳庭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夜深露重,方才在这位小兄弟的“压迫”之下洗净身体,谁知又闻到生肉烤熟的香味,他饥肠辘辘本就难以抵挡,害得他一激动踩了岸边滑石,抱着衣裳一起跌入了湖。虽是夏日不觉寒冷,但身上实在潮湿得难受。
这位“难兄难弟“此时闭目合眼,身上的灰布麻裳虽已洗得发白,但拾掇得十分干净整齐,三庭五眼,五官端正不显妖媚,皮肤白皙细腻,年轻少年郎,清秀非常。
“柳兄,柳兄?”
柳开没有睡着,听到声响便睁开了眼睛。
“不是兄。”
“嗯?”
“我年纪比你小。”
……
朝廷为沿途赶考的贡士提供暂时歇脚的旅社,因着全国的贡士来自五湖四海,一路穷山恶水者比比皆是,旅社提供简单酒食,不丰富却能饱腹,一床盖肚子的薄单,落在山林之间的旅社,夜晚还有众多蚊蝇缭绕。
“柳开老弟,快来帮帮忙,需得将一屋子满满乱飞的山蚊子给赶出去!否则日夜归去岂不是一屁股红包!”
柳庭南双手撑着衣裳下摆“呼啦呼啦”往上下乱拍,一团团黑影围绕他全身上下变幻,齐心协力发出“嗡嗡嗡”的震鸣声。
山蚊子久不闻人血香,哪里肯轻易放过这个进了自家营帐的傀儡,被拍倒了又爬起来,挺着尾巴上的长刺,只往他外露的皮肤上扎去。
“妈呀,我不行了。这脏东西成了精,死活赖在这臭茅坑内。”
柳开叹了一口气,心想着也许它们就是靠着这臭味生的。
柳庭南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出了屋,脸上耳旁已经现了红斑。
柳开给他打了水,清凉的井水扑了满脸沾湿了胸口的衣襟,稍微缓解了毒蚊留下的红肿热痛。
“露天席地也无需讲究,掩着树丛宽衣解带就成了,你们这破茅坑我是再不想进了,拉一回屎丢一条命,不值!”
“那草有一人高,你走得进去也不知道走不走得出来。”
柳开为赶路绕的林间小道,那看管人也受不得艰苦,早就跑得无影无踪,桌椅厨造积了厚厚一层灰,柳开几人从客房浴桶挨着墙壁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条一尺多长的黑白纹蛇,床上衣被中藏着一窝十几只的狸花幼猫。
来此旅社的贡士合两柳在内共有六人,见此场景吓跑了三个,剩下的那人虽不多话,但默默帮着两人杀蛇打鼠。
柳庭南瘫倒在井边,脸上的红包已经慢慢从平整的脸皮上浮现凸出,手捧着脸时不时有气无力地叫唤几声,显得触目惊心又滑稽可笑。
柳开蹲在旁边低着头想对策,她急着赶路,身边还跟着个柳庭南,一路上只吃干粮少喝水,此时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控制下半身,脑子难以集中,渐渐急切焦躁。
一道火光从西南冲向东北在两人面前拐了个大弯直冲入茅坑。
“酸朽!”
柳庭南啐了一声,爬起来跟了上去。
“噼里啪啦”的脆响伴着蚊子身体烧灼的气味,从茅坑暗红近黑的木头渗出的白烟带着草木香气。一个高挑人影举着火把背对着他们,右手上的草料快烧尽左手又接上一把新的,旧的撑着火光未灭扔进坑洞中,一时之间脚下又冒出一团团细蚊,在烟雾之中偃旗息鼓。
少年眼睛熏得通红,遒劲青筋突出盘绕在劲硕的手臂肌肉上,犹如神武,一动不动。
“是晒干的艾草,浓烟可驱散蛇虫,功效温散行血,多闻艾烟,于人体有益无害。”
李文远在空旷的院子中搭着架子,柳开两人捧着干枯的艾草往架子上放,堆成堆点上火,浓郁的艾香弥漫了整个旅馆。
“这会儿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柳庭南嘀咕一声,塌肩驼背地往客房走。柳开也累得慌,和李文远一前一后走着,明明干一样的活,李文远这个贡生却是精神抖擞,看看恨不得瘫成泥的柳庭南,想想人与人果真不能相比,不比较不知道自己的弱处,不知道便能自己欺骗自己,不做任何努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