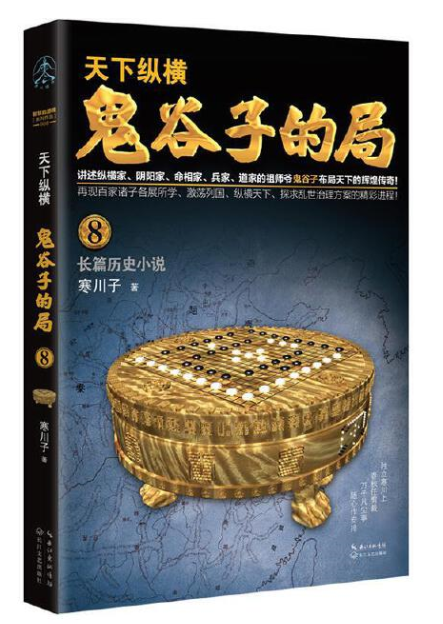北京这地方被叫作文化故都已经有些年,打我小时候就听见有人这么称呼它,没听见有人反对,可见是得到了大家认可。
既是文化故都,必得有它独特的文化面貌,什么是北京的地方文化?什么是北京的土著艺术呢?这就有争论了,不见得挂京字的就是京都土产,举例来说,“京韵大鼓”,打头就是京字,而且全国就这一份,总该没说的了吧,且慢,查查几十年前的旧笔记,你会发现它原来叫“津韵大鼓”,原本来自天津,在北京落户之后才改成这个名字,就像在美国的那些彼得·李,乔治·张一样,虽持美国护照,但非土著居民。“京韵大鼓”尚且如此,至于“京梆子”、“京皮影”、“京酱肘子”、“京酱园”那就更没准谱了。如今山西梆子、滦州皮影在本地还挑着大梁,在北京落户的一支你就敢说是北京特产?在北京开酱园的大都是河北人,肉杠子向来是山东人的专利,传到这儿一支,就列入北京土特产目录,难免叫人不服气。
虽说不服,可还不能生气,因为还有另一面道理。梆子确是从山西传到北京的,可您听听李桂云唱的跟丁果仙唱的是一个味吗?别的不说,就听唱吧,山西梆子唱念都是晋腔,京梆子唱的是京腔,就是上韵也按京戏的路子上湖广韵,跟山西口音差着几百里地呢。北京“萃华楼”的“京酱肉丝”跟济南的“酱炒肉丝”也不一个味。别听北京山东馆的掌柜说话还常带点怯口,管“吃什么”叫“漆席么”,真正山东人一听就觉得变味了。并不是北京人爱把别人粉往自己脸上擦,实在是北京的历史造成的。它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六百多年,居民既来自各省各地,也是全国精神和文化财富交流汇集之所,天长日久,没发展的东西渐渐被淘汰,有根基的留下来,在这个大熔炉里,融化、综合、分解、改造成另一种模样,就成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所以北京的地方艺术和各地的地方艺术有点不同。外省地方文艺,多产自本乡本土,北京则集各家之长,又染上自己色彩,变成自己的东西。产于他乡,成于京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京戏。去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二百年前安徽地方戏进京朝贡,在这里落下脚,在此与皮簧、吹腔等融合,接受昆腔、梆子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姓京的大戏。
用这个观点来认定北京地方艺术,路子可谓宽矣,品种可谓广矣。王佩一大臣的铁片大鼓,关学曾的琴书,连魏喜奎的“奉调”也得算北京土著艺术,因为在这些艺术的原产地绝听不到今天这样的东西。
表演艺术如此,别的艺术门类也不例外。毛**曾说北京的建筑艺术特色是四合院,其实四合院是遍采北方民居之长,加以综合改造而形成的,此外玉器雕琢,有京作,苏作,广作之分;烟壶内画,有京派,冀派,粤派之别,过去就连娶亲的饮场,花轿的装扮,出殡的执事,棺罩的花样都有自己的特点。若再扩大到生活文化范围,穿衣有穿衣的学问,如今虽有很大改变,但仍留下不少遗迹,作为民俗文化来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说个笑话当例子,刚进北京不久,我得了几元稿费,买了件纺绸衬衫,是我生来最好的一件衣裳了,平日舍不得穿。正好在伏天时,有位老北京朋友过生日,我正儿八经把衬衫熨平穿了去贺寿,坐下之后,见他们全家都穿着旧夏布小褂,我正为自己的绸衫得意,他母亲过来了,这位大妈平日拿我们当子侄看待,就笑嘻嘻地冲我说:“哟,大侄子,你们革命干部可真艰苦哇,都数三伏了,纺绸还没下身哪。嘴里省一口,也该买件夏布褂子,年轻轻的别叫人笑话……”他儿子就说:“快歇着您的吧,现在哪还这么多讲究哇。”两人说得我莫名其妙,过后打听别人才知道,北京人只在入夏的时候才穿串绸(即纺绸),只要日子过得去,一数伏就该换下来,有钱可以穿罗穿纱,没钱穿夏布也算应节气,再穿纺绸就成老憨了。
外地产的比较原始,比较粗糙的艺术进了北京何以就发展成比较成熟,比较精致了呢?我有个看法,不知是否有点反动,我觉得艺术这玩艺是要吃饱了肚子有闲心时才可以仔细琢磨,精心从事。弄它的人还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北京作为首都,有钱有文化的闲人不多,吃饱了没事干就静下心来钻研雕琢艺术品,这才能精益求精,争奇斗胜。即使是艺人们自己发展创作,在北京也比别的地方更有有利的条件,旧话说“无有君子,不养艺人”,北京这地方有闲钱有欣赏能力的人多,艺人们就容易混饱肚子,北京这地方能见到各地各省甚至番帮海外的艺术精品,也确有扩大眼界,增广见识的机会,这就为艺术家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条件。过去几代京剧艺术家其籍贯虽多系安徽、湖北、江苏等南方诸省,而艺术上的功成名就皆在北京,就是个证明。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地方的,民间的纯朴,健康,乡土气息民间气息浓厚的艺术,一经这些统治阶层的文人大佬加工改造,就带上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色彩和贵族化的艺术趣味。贵族文人常有的富贵气酸腐味一渗入艺术领域,就像把一杓肥油加进了雨前龙井中,玷污了整个优美境界。更何况,统治层中的人有权有钱却没有文化修养的大有人在,为了迎合这一部分人的趣味,更易沾上庸俗繁琐的毛病。这一点在工艺美术中看得最清楚,比如北京的家具制造业,按工艺的技巧说,无疑是到清朝时发展到了极致,鲁班馆的家具今天看来还是叫人惊叹它的精致细巧,但和明式家具比起来显得刺眼的庸俗和繁琐,由此也就有了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倾向,再进一步就有随着统治阶级的衰败灭亡而衰败灭亡的危险了。这一点也许从昆曲身上能看出点眉目来。昆曲的艺术成就应当说是登峰造极的,无论唱念作打,到今天很多剧种还要从它吸取营养,但昆曲本身,从几十年前就已衰落了。说来可叹,我对昆曲的兴趣竟是从看蹭戏培养起来的,我小时家住天津法租界,那时白云生、韩世昌常在“新中央戏院”演出,因为上座极差,每场几乎上不到四成座,以至小学生们进去看蹭戏把门的拦都不拦。就我记忆来说,当年看的戏中,行头比昆曲班再破旧的很少了。解放初期,我认识的那几位昆曲名伶都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团当了基本功教员。白云生的《拾画叫画》、韩世昌先生的《胖姑学舌》都只能在联欢会上露演,许多武生演员,竟改行去耍狮子舞了。新中国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艺术政策才使昆曲从旧统治阶级的艺术牢笼中解放出来,周传瑛等改编演出了《十五贯》,这才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之盛事。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昆曲作为一个剧种才重新活跃在舞台上(前清北京某王爷酷爱昆曲,在他高阳的封地上成立科班,请苏州昆曲艺人教他庄子上的农家子弟唱戏,才有了北昆一支,故北昆虽出自高阳,仍把它算作北京艺术)。
北京艺术比起外省地方艺术来,和统治阶级的关系更紧密,所以时代的发展,阶级地位的变动和艺术兴衰关联,在这里就看得更清楚些。有些艺术品种,明显随着统治阶层的衰败而衰败了,人们可以感叹,可以怅惘,但绝无回天之力。当然也有不受这种影响,始终保持着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品种,那是因为它们与普通人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的有所发展有所改造,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像在这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几位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就是这样。魏喜奎同志我们是老朋友,我亲眼看到她一生拼搏,不断创新的过程,她不断改进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从不墨守成规,今天大受欢迎的曲剧就是她、曹宝禄、关学曾等几位艺术家在老舍先生直接参与下历尽艰辛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例子在其它艺术门类如工艺美术界,民间艺术界,也可举出不少,所以我们在面塑、内画、风筝,景泰蓝等方面都看到新的人材,新的成就。
北京也有纯粹土生土长的艺术,但并不见得高明,而且留传下来有所发展的也有限,有的改头换面以新的样式传下来了。如曲艺中的岔曲、单弦,这倒是北京八旗子弟的创造,两者都发源于军旅,前者创于清朝南征之时,后者是乾隆时期大军远征大小金山时的创造,都是用以慰藉士兵们的思乡情绪的,班师之后带回北京,成了子弟们消遣的艺术,只准演唱,不许收费,故谓之“子弟消遣”,民国后才流入民间。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与当年已大不相同了,当年的“八角鼓场子”是一个完整的晚会,由“鼓、柳、彩”三部分组成,八角鼓开场,中间到牌子戏终场,中间有“哄哏”(相声)、“群曲”、“戏法”、“快书”等多种节目,节目的种类、次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是不许乱来的。大约是太贵族化、规范化了吧,一旦走入民间就打破了它的规范,留下岔曲和牌子曲组成一个曲艺节目,“哄哏”“快书”等各自独立,最后的牌子戏只附属于单弦演员的节目中偶尔作一次演出。前些年顾荣甫、尹福来还可唱牌子戏,也就是“拆唱八角鼓”,尹福来不化装弹弦兼演旦角,顾荣甫歪戴乌纱,身着大红官衣,手执马鞭,边唱边舞一出《小上坟》,演得滑稽突梯,精彩绝伦,此后我就再没看过拆唱的演出了,我想会唱的人即使有,怕也不多,而且多半年事已迈,再过些年怕真要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