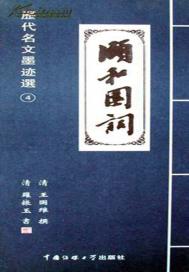还没进院子先听到院中猪嚎鸡叫,人喊狗吠,与往日那冷清沉寂气氛大不相同。进得院来只见有娃子牵着猪,有娃子手中攥着鸡,有娃子在捣米,有娃子在院中又生起一堆火来。多日不见过的红黑脸大黑彝站在屋门口,一言不发地监督着这一切。阿候阿芳和古旺元一进门,他移步来迎,与古旺元握着手说:“我这几天出门办事,没有见面。听阿芳说你的伤养得见好,很高兴。”
他招一下手。牵猪的娃子便把猪牵到他们面前,他发出一声口令,就有娃子提着一根短粗木棒走近,吼了声,猛朝猪的头顶一击,那猪闷叫一声错倒在地。牵猪的人从腰上拔下把尖刀,对准猪胸部连捅几刀,随即有娃子朝那猪身上泼了一瓢冷水,把猪拖到院中火堆上烧了起来。这时拿鸡的娃子便把鸡举得很高,手攥着鸡脖子紧紧一捏,捏得鸡蹬脚展翅,几番挣扎伸腿瞪眼了,也如法炮制,浇了冷水,扔进火堆。大黑彝这才请古旺元随他进屋。
这屋子很大,用半截木板隔成为两块,左边小间里喂着牛、猪。他们在外面火塘边落坐。阿芳领古旺元在正斜对门口处坐下,大黑彝坐在左边,侧面对着门口。娃子从墙边一个布包里抓出青绿色的树叶,把罐放在锅庄上炒了几下,顿时闻到一股焦香味,倒进水在火上烧开,分倒在木碗里,摆在他们面前。
大黑彝不动那茶,却从身旁的陶罐里用木耳杯舀出一杯酒。举起来说:“我们跟古先生相遇,是难得的缘份。我有事在外边忙,小妹不懂事,照顾不到,多多包涵了。”说完把酒一口饮尽,又亲手舀出一杯,敬给古旺元。
古旺元偶而喝两口酒,必须就菜,这么干喝,略有难色。阿芳在一旁偷拉了一下他的衣襟,他会意,闭上眼把酒喝了下去。还好,那酒虽似白干,但比汉族的白干度数要轻得多。
他喝完,亮了一下杯。娃子接了过去又到罐中舀满一杯,双手递给了他。他不知该如何办,阿芳又拉他一下说:“你也要回敬我哥哥一杯嘛!”
古旺元是演戏出身,反映灵活,连忙举起杯对大黑彝说:“我九死一生,全凭支头搭救,才活到今天,我永世不忘你的救命之恩。”说完把酒敬给黑彝。黑彝接过酒也喝了。这时娃子又给舀满。古旺元拿着酒有点发怵,不敢再喝。阿芳在一边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感谢我哥的救命之恩。全没有别人的情份了喽!这些天你都是吃石头喝马尿活过来的?若回到你们自己人那边怕连这个地方都记不得。还讲什么救命之恩,永世难忘。全是鬼话。”
古旺元赶紧向她低了下头说:“我正在想这杯该敬给姑娘。没有你精心照顾,我哪能起死回生!我要忘了你,天地不容!”说着把酒敬给阿芳。并向她深情地看了一眼。
阿芳哈哈笑着接过酒一扬脖就喝得精光。
喝着茶古旺元打量这间屋。古旺元这是第一次进入彝人正房。房子很大却没有一件家具,而且就在隔开的一间中喂养着牲畜,很感惊异。
娃子进来说了句什么,阿候阿芳起身出去了。剩下两个人时,大黑彝笑着向古旺元说:“你对我妹妹说的所有话,她都转告我了,可她对你讲了些什么,一句都没跟我讲。她讲到我些什么?”古旺元摇头说:“她只是问我话,从不允许我问什么,对你的一切都避而不谈。”阿候拉什点点头,说道:“那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叫阿候拉什,是黑彝支头。有些钱,有些地,还有些娃子。是成都军校的毕业生,在中央军里当过副官处副处长。”
古旺元点点头说:“我看出来你是受过教育的人。”
阿候拉什说:“我不是心甘情愿受教育的。父亲是大支头,家又临近西昌,他不送个儿子去上军校,留在他们手里当人质,就没得太平。不受中央的讨伐也要受邓秀廷的欺侮,所以送我去了军校。”
古旺元说:“可以理解。”
阿候拉什说:“结果我们不光没得到太平,反倒陷进了是非漩涡。毕业后给我个少尉肩章,编入部队,平时呆在那里还是等于当人质,我的家支出了事就拿我是问;他们要打别的彝人,又要我带自家的娃子替他们当先锋,打一仗他们发一次财,我就结下一门冤家。军队可以调防,我却不能随军调动,一直留在西昌。哪个军头来了把我编入哪个部队,换一次长官我送一回礼,上一次供,这我也忍了。可是最后他把队伍开进到我自家门口来了,叫我向自己家人开枪……”
说着他示意身后站着的娃子,那娃子赶紧给他和古旺元又满上一杯茶。他痛饮两口,简单讲述了参加八大黑彝,失败后被迫遁居山林,再不复出的经过。古旺元才想起在锁夷河边罗赤中讲的这段故事,也才明白面前这位就是被李家钰派去当督战官,临阵倒戈,宁死不向自己同胞开枪的那位彝族副官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