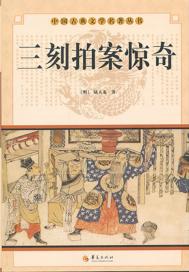古旺元喝了几口水,晕晕乎乎睡着了。等他醒来,已是夜间,从屋顶的木板缝间露进了一线月光,隐约看见门旁蹲着一个彝人,缩在墙边像一条狗。古旺元伸手摸摸头边,木碗还在原处,里边又装满了水,端起来喝了一口,粘乎乎的竟是稀粥,从没尝到过的香甜。一口粥下去勾起了他的食欲,既没有中毒的警惕,也不再绝食求死,是死是活吃饱这顿粥再细想,真没有活路吃饱了再死也来得及。便大口大口,狼吞虎咽把一碗粥全喝了下去,还伸舌头把碗舔个溜净,啧啧嘴,感到余香满口,可就是辨不出是什么粮食做的。
半睡半醒地过了一会,听到鸡叫,狗咬。睁开眼可以看见屋里的陈设。先看到头上的房顶,房顶是用一些不规则的木板搭盖的,板与板之间有好大的缝隙。可以看到澄蓝的天空。屋子并不小,除去身下的荆笆,沿墙堆了些谷草,屋顶吊两串辣椒,别的一无所有。那彝人仍靠在门边墙上睡着,蜷缩在那里像只老狗。
肚子里响动,多少天来头一次要上厕所,便扶着地坐起来,立刻一阵晕眩。他强咬牙站了起来,腿抖得厉害,坚持着往门口挪动,移了两步便跌跌撞撞地冲到墙边用手扶住了墙。那彝人被惊醒了,睁大眼睛看着他,伸开两手作出阻拦的姿势。他颤抖着对彝人说:“我要大便!”那彝人呜呜地叫着向他摆手。他用手摸摸肚子,把手从腰部往下滑动。彝人懂了,点点头,跑出门,回手把门关上。他用手推门却推不动,显然门被从外边拴上了。他急得大喊,喊了好久,外边有了人声,那彝人拉开门,扶他走出去。离门口不远站着个背着枪的彝人。背枪的彝人招招手,带他走到房后。房后是“座小山,山坡左右又有四个背枪的彝人,各据一方,背对背,脸朝外警戒。”
扶他的彝人,朝山坡中间指了指,嘴里又呜呜地叫了两声。古旺元问他:“叫我上哪儿去解手?”那彝人点头。又指指那些背枪的人,作了个射击的手势。古旺元说:“我要跑他们就开枪?”彝人又点点头,转身走回屋子前边去了。
古旺元挪到土坡中间,找草深处蹲下去。重新站起时满脸泪痕,生活秽事证明他自己还活着并且又回到人间。
那四个拿枪的人没回过一次头,没说过一句话。
古旺元蹭回来,走近房子,老彝人就从墙角转身出来,把他扶回屋中,扶他躺下,自己又默默地回到门边,靠墙坐了下去。
古旺元说:“我要喝水,水!”他指指碗。
那彝人走到他身边,拿起木碗转身就走,古旺元拉住他的手问:“我说的话你懂?”
那彝人惊慌地看看门外,点点头,又摇摇头,嘴里啊、啊了两声急忙走出门去,并随手从外边把门拴上了。
门重新打开时,慌慌张张前后进来两个人,老彝人端着一木碗水走在前边,后边跟着年纪只有十六七的小娃子,捧着小木盆,木盆冒着热气,肉香刹时溢满了全屋。老彝人放下水转身对小娃子作了个手势。小娃子把肉放在古旺元的身边,慌张地看看门口,见门关着,就急急地小声对古旺元说:“先生,我也是汉人,你出去把我带走吧,我情愿给你作牛作马。”
小娃子说的汉语!
古旺元狐疑地问:“你也是被人抓来的?”
小娃子结结巴巴地说:“叫人抓到,卖了三家,才卖到这里来的。”
“你是哪里人?”
小娃子说:“我家在陕西,给胡宗南的军队抓来当兵,开到四川吃了败仗,不认得路跑到山里,叫蛮子抓住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巨响,门被人踹开了,老彝人惊惧地拉开小娃子,小娃子刚要跑已经来不及了,迅雷闪电般从门外冲进一个人来。
这人体态轻盈,丰胸细腰,面容娇好,举止傲慢,嘴唇宽厚红润,紧闭中透出怒意;两眼黑中透亮,圆睁时威光逼人。绣了花边的青色帕子,用辫子紧紧缠在头顶;坠着流苏的墨色披衫,以丝绦斜斜挂在肩头。上身穿窄袖短袄,袖口上绣满花边;下身着百褶长裙,裙摆间五色缤纷,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
她在屋中间站住,两眼怒视两个娃子,一言不发。
老娃子扑通跪下,呜呜地叫着,指着那两只木碗,又指指小娃子,再指指自己,捣蒜般磕起头来。
小娃子也跟着跪下,把头磕得咚咚作响。大叫道:“姑奶奶,饶了我,饶了我,我帮他端肉来的,我啥子都没讲……”
“讲彝话!”她用汉语叫道“说彝话!”
小娃子赶紧改口,结结巴巴用彝语求饶。老娃子也急忙用手比划。
她听了一会,眼看着小娃子,手指老彝人,用汉语说:“他也犯过你这样的错,想叫人把他带走,从那就没有舌头了,你没看见吗?没看见吗?”回身对老彝人吼了一声,老彝人泪涟涟地冲小娃子张开了嘴,嘴是个黑乎乎的空洞。
她又用彝语说了句话,小娃子感激地磕了三个头,爬起身来走出门去。
她对老娃子怒吼起来,不断地叫着一个字,那老娃子随着她的叫声,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脸,直到嘴角流血,两腮肿胀。她才停口,老娃子呜呜哭着,磕个头退出屋门去了。
她回过身来,两眼盯着古旺元,一脸杀气。
古旺元是个心慈面软而又有同情心的人,平日看到以强凌弱,以大压小都禁不住打抱不平,看到苦老乞儿,总要周济,连看到手狠的父母打孩子他都掩面而过,哪里受得住这样残暴的场面。躺在那里早已心痛得泪流满面,气愤得浑身发抖。见这女人回过身来,便也怒目而视。刚才一进门时美貌印象,早已被撕碎扯烂了。
他欠起半个身子说:“你这个母老虎,用不着对娃子发威,是我跟小娃子说话的,你冲我来好了……”
姑娘不等他说完,就冲他大声叫道:“你这个坏种,你这鬼怪,应该打你,应该杀了你!”
古旺元不是英雄,但是受了这些天的折磨,见到奴隶的可悲命运,已不存任何侥幸,没什么可贪恋的了。便豁出性命喊道:“要杀要剐由你,别冲我叫喊!我不是你的娃子!”
他一喊她反惊呆了,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盯住他,仿佛看一头从没见过的怪物,露出满脸的困惑。
门口又有了脚步声,她才把眼睛移开。
来了个穿着比较整齐的彝人。见她在此,便默默停在了门口。她什么也不说,径自走出门去,那彝人跟在她后边也走了。
老娃子回来了。用手抚摸被打得通红的脸,吐出了一口血水。眼睛看着古旺元微微地摇摇头,嘴角稍稍向上一提,作了个极丑极苦的微笑样,靠墙坐下来。
这一天再没人来,没人和古旺元说过一句话。天黑后老彝人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烤糊了的土豆。
从此一连数天都这样沉寂刻板地度过,早晨到持枪人包围着的山坡上排便,然后躺在荆笆上养伤。两顿粥,几碗水。中间要小便时去房后山坡,老彝人跟随着,不说话也不抬头,背过脸等他,随后再跟随他回到屋里,仍在那墙根坐下。
老娃子被割去舌头,已经哑了。但通过眼神,手势,他们仍在交流。几天后已经能辨别老娃子在什么场合,用哪种眼神是暗示什么。古旺元发现那肮脏、羸弱、丑陋的形体里藏着个善良灵魂,并感到他的同情与关照。
当初学习社会发展史,老师说“奴隶主把奴隶只看成会说话的工具”,如果他还能活着回去,他想更权威地作点更正:“奴隶确是工具,但并不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