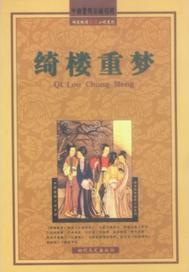西昌和邻近几个县的联络中断了。援兵正往南边赶,在西昌已经能听到清楚的枪声,商店停止营业,街上十分冷清,全城沉闷得令人不安。
接近中午时分,王庭芳正在后院检查备战工作,有人在前院喊了声:“胡大夫,呼延先生来访。”
王庭芳马上迎了出去。一位穿着破旧长袍,留着三绺长髯,仙风道骨的老人正微笑着走进院来,王庭芳已在各族各界代表会上见过他,赶紧叫了声:“呼延先生,你怎么有空驾临哪?”
呼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在下有事求助。”
“咱们屋里谈。”
王庭芳把呼延老先生让到客位上坐下。呼延迫不及待地说:“我想焙茗候教,请您务必赏光。”
王庭芳脑子飞快地转了一转,在这非常时刻,这人决不会只为了应酬交际来请自己,必有要事商谈。便问道:“什么时候?”
呼延说:“越快越好,如能现在起驾,求之不得。”
王庭芳马上答应说:“好,我安排一下随后就到。”
呼延说:“我回去准备,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不必多带人来,我以性命保证您的安全。”
王队长笑道:“瞧您,说到哪儿去了!”
呼延走后,王庭芳把孟先生找来,悄悄说了一声:“我去呼延那里,有人找我就说出去办事了。”说完还是带了秘书陶亚男,走出大门。走到呼延那条街口,叫警卫员到附近茶馆等候,从远处注意着呼延家门口的动静,有事时他以摇手帕为号。
王庭芳叫开门,呼延迎出来,把他们让进上房。
这上房是一明两暗的正房,中间是客厅兼诊室,竹制的桌椅,揩抹得一尘不染。两边耳房门口都挂着竹珠串成的门帘。茶早用盖碗沏好了。王庭芳在客位坐下后,呼延欠身:“请多包涵,没大事我不敢劳驾。山里来了位朋友,有事找我求助。这事非同小可,又与你直接有关,所以我不揣冒昧把您请来。希望您能和我这朋友见一面。”
王庭芳说:“这有何不可?为我介绍位朋友,我还要感谢您呢,这位朋友在哪里?”
呼延往左边的门口走了一步,挑开门帘说:“阿候支头,请出来相见。”
一个高大魁梧的人低头钻出门来,站住后向王庭芳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这人穿着一身旧衣裤,新干部帽下露出几根额发,看来像是乔装的彝人。王庭芳站起让座说:“不要客气,请坐。”
呼延介绍说:“这位支头名叫阿候拉什,跋涉几百里,到此就为见你一面。”
一听阿候两字,罗洪英豪对此人的介绍就涌上脑际。王庭芳忙说:“我们早想请头人来此共商大事,惟恐请不到,既来了怎么不直接找我们,反麻烦呼延先生,是不是太见外了?”
阿候笑笑没说什么。王庭芳又介绍了陶亚男,说这是他的秘书,阿候很礼貌地欠欠身。
呼延说:“队长是中央来的,没有偏向、不存成见。我可以替他解释一下。当前与政府合作的支头中,有人和阿候家有宿怨。他不想公开露面,也不会久留,找您只为核对一件事。”
王庭芳心想这位阿候拉什,跟自己素无瓜葛,有什么事要核对呢?便说:“阿侯支头,政府对所有彝人一视同仁。愿意精诚合作,有事你尽管谈。”
阿候从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个羊皮小包,从小包中掏出一个方方的血污的纸片双手递给王庭芳说:“王队长看看,你可认识这个人?”
王庭芳接过一看,大惊失色。忙问道:“这是我们的同志,掉队失踪好多天了,我们正在找他,你是在哪里捡到这个团员证的?他还活着吗?”
阿候微笑着出了口长气说:“这就好了。确实是你们的人,我就放心了。他活着,不过受伤太重,还不能行动。”
“他现在在哪里?”
阿候说:“前几天我在北边,碰到卖娃子的人,要卖给我新抓到的一个娃子。要的价钱很低。我答应先看看再说。他们把我带到河边山洞前,抬出了这个人,已经十停死了九停。本不想要,后来看到了这个证件,知道他是公家人,我怕他被别人买去,转卖进深山,没有得救的希望,就把他买了下来。现在养在我家里。”
王庭芳焦急地问:“谢谢你,花了多少钱,我们可以照付给你,连同这些天的生活费。”
“不,您太小看我了。”阿候笑道:“我的身家虽然不大,但还不在乎这点银子。为了这点钱我也不会冒险下山。山里不少地方出现了暴动武装。我进城若被他们发现,有杀身之祸。我来就是要说明一件事!”
王庭芳急问:“什么事,你说!”
“第一,是告诉您这人在我手中。我既收留政府的人,就不会参加暴乱,请对我放心。”
王庭芳对这彝人的用心有点同情。诚恳地说:“我相信你。”
阿候说:“第二,他现在不能动,我无法把他送回。求您也给我个凭证,叫他相信我确实见到了你,你也同意他在我那里养伤。我已求呼延先生给弄了药,回去给他治伤。”
王庭芳说:“这不成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给他再带点西药去。”
阿候说:“带着洋药,碰上暴动的人我无法解释。呼延先生的药彝区通行,他们见了也不会怀疑。”
王庭芳见他头脑冷静,有条有理,极为动情地说:“阿候支头,我代表政府,代表我们全团谢谢你。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并且欢迎你下山来共商国事,一块建立咱们新中国,新凉山。”
阿候苦笑一下说:“那就不必了,我发过誓不问政事。你只要明白,我不是你们的亲信,也不与你们为敌,这就够了。”
王庭芳说:“我尊重你的立场。来日方长,现在请和呼延先生一块到我那边坐坐,一起吃顿晚饭,痛快谈谈。”
阿候说:“外边情形很紧张,今天不走只怕明天就进不了山了。我是昨天天黑进城的,躲进呼延先生家时谁也没见,除去你们也不想再见任何人。您留个信物给我,咱们后会有期吧。”
王庭芳觉得这个人虽然心灵中有死角没打开,但可以信得过。他在身上摸摸,没带多余东西,只在随身带着古旺元的那支手枪,他斟酌片刻,解了下来说:“我高兴得到你这个朋友,这支枪送你留作纪念吧,我那个同志认识它。看到它就相信你跟我见过面。”
阿候感到意外,重复地问:“你说把枪送给我,你这么相信我?”
王庭芳说:“我这辈子还没看错过人。我相信这支枪在你手中,枪口永远对着仇敌,不会对着朋友。”
阿候深鞠一躬,双手把枪接过。从身后取下自己的佩刀说:“我也把保护性命的东西送给你。如果我阿候枪口转向朋友,叫我死在这把刀下。”
王庭芳也郑重地双手接过。问阿候:“要不要我再写儿个字带给他?”
阿候摇头说:“我所以只要信物,不提带信,就是汉字写的东西我带着不安全。”
这时陶亚男红涨着脸,突然从她的手提包中抽出来一张纸,拿给王庭芳说:“这上边没有字,带去总可以吧。”阿候凑过来一看,见是一张铅笔画的画儿,画着光着膀子,摇着扇子,坐在大街边上乘凉的人。
阿候说:“这倒可以带,被人看见也泄露不了什么,可它有什么意思呢?”
陶亚男一笑说:“没什么意思,可他看了会安心。他认识这幅画。”
阿候说:“好,我一定带到。”
王庭芳告别时,问他还有什么要帮忙的事。阿候说:“我白天出城不便,你能不能帮我说个情,天黑之后放我出城。但不要说我是谁。”
王庭芳答应说:“一定办到”匆匆回去,马上向军管会领导作了汇报。军管会主任也觉得阿候虽倔强倒也义气,更觉罗洪英豪对他的评价带有个人感情,今后若能化解他两人的矛盾,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当晚王庭芳与军管会主任一到,以备战工作为名,来到城西门。等呼延陪阿候来到,请到守卫室中,按彝族规矩,热情地招待他干喝了几盅酒,这才握手告别,悄悄叫把城门打开一条缝,放阿候出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