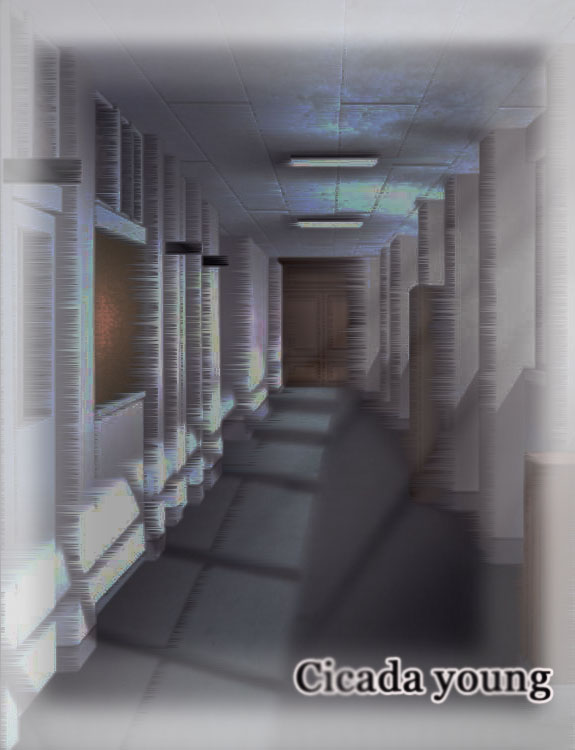若不是姬伽的催促,桑落与妘缨还在一旁继续看戏。
面前的你侬我侬,可比说话本的老叟生动许多。
姬伽谑笑,故意当着众人的面,道:“王上如此欢喜少年炙热的爱恋,可曾是想到少时,非臣抱怀为枕的难眠之事了?”
众人闻讯纷纷前去姬伽身旁,等着他继续。
妘缨连忙起身捂住姬伽的嘴,道:“快走快走,子时过了,莫要等着那二人也过了宫门。”
少时的妘缨,颇为贪恋姬伽身上的味道,以至于一度只能在姬伽怀中止住哭闹,安然而眠。为此,宋仁公特地将姬伽封为公子伴读,常留宫中陪伴在妘均与妘缨的身旁。
思尔,本就是姬伽为妘缨取的小字,却被同是妘均挚友的商温捷足先登,献给宋仁公。
妘缨自小与姬伽一同长大,识得他的笔迹,便从一众小字中,选择了思尔。
属于姬伽与妘缨的缘分从此阴差阳错的断开了,与商温的孽缘,也是从此刻开始的。
这些前尘往事桑落与霍繁香自是不知,妘暖亦是从各处听来,勉强拼凑,貅离与他讲一些,简祭酒与他说一些,还有夜雨,铃铛和夜玦。他想着若伽伯为当事人,或许能从他的口中套出些独家来,待回到临酉,与简祭酒和夜雨姑姑她们也有的饭后谈余。
在一行人趁着夜黑风高,穿梭在安阳街巷,前往死城时,妘暖故意走在距离姬伽很近的地方,起先用闲话家常与他拉近距离,随后便从他口中套话,问他与宋公是如何相识的。
姬伽自小颠沛流离,几度曾在生死徘徊,凭他的城府,如何听不出妘暖在套他的话。
“按照辈分,你应当称我一声叔公。”姬伽道。
妘暖是大公子妘均的遗腹子,妘均还得称呼姬伽为小叔叔。
妘暖恭顺地唤了一声“叔公”。
姬伽满意地点了点头,不再言语。
妘暖诧异满面,不禁又道:“我叫这一声叔公,都不能消除你的芥蒂,便是与我说一说和父亲和姑母的往事,都不成了?”
姬伽满面笑意,道:“说倒不是不可以,你既认了妘均为父亲,便要接替妘均的责任,对宋国的责任。”
“若你始终逃避,我也有理由拒绝,有理由与你一样,选择避而不见。”
妘缨走在二人的后面,在听闻姬伽的这番言辞时,亦是会心一笑。
待妘暖轻哼了一声,转身直追前方的霍繁香与桑落后,妘缨稳步上前,细声道:“平时见你对他不以为然,这回怎想着履行作为长辈的责任了?”
“我又不是为他。”姬伽回道。
妘缨戏谑:“难不成是为我?”
姬伽沉默半晌,随后轻轻“嗯”了一声。
“若他接替妘均继位宋国,你便能随我回广灵隐世。”
“就像我父亲和母亲一样。”
“似稀世之珍,藏之珍之,再不让你受半点侵害。”
妘缨美目流转,莞尔一笑:“不必非要隐世,你现已在我身旁。”
“更何况,我亦非吉光片羽,哪那么容易遭人惦记。”
“妘暖与我兄长一样,天真又炽热真诚,这样的人,不适合为君者。”
“兄长已经死去,因为权利的争斗而死去。”
“我不忍他再步兄长后尘,被亲近的人,被信任的兄弟坑骗而惨死。”
“若这条路黑暗冗长,荆棘满路,我不希望他来走,但凡还有我在,他便能自由自在地去追求他的热爱。”
妘均的暴毙,皆来自对于妘卿的信任。或许他到死都不会相信,那个凡事以大哥为重的弟弟,竟能受姬洛禅的蛊惑,为了国君之位,亲自下手毒杀了他。
“有时候,我在想,若我是长姐就好了,若我是长姐,由我继承君位,兄长如你一般,做个闲散郡伯,远离权利中心的争斗,而后安稳一生。”
二人还沉浸在往事的情绪之中,妘缨腰间的白虹剑忽生异动,倏然出鞘向远处飞去。
妘缨忙道:“速速隐蔽。”
姬伽即刻飞身上前,扯着桑落与妘暖往相反的方向藏身。
在霍繁香被妘缨拖拽着前行的时候,她还有些懵,直至看见眼前的人时,她才反应过来。
妫翼接过白虹剑,同百余甲兵对峙。
霍繁香定睛望去,见率兵之人,乃是罗绮与澹台成蹊。
那妫翼的身后也站着二人,一个是君绫,另一个是鬓发散乱,泣下沾襟的韩尤妙。
“陈侯可知非王诏令,随意入王城的后果?”罗绮厉声道。
“劳烦罗小臣挂念,我已自请卸去国君之位,陈情书早已送入宫中,如今我不过一节流民,与这安阳城的百姓一样,失所于大疫之中。”妫翼退位的陈情书已经在君绫的安排下送入安阳王宫。
陈情书已覆周王玺印,只是以安阳目前这种情况,暂未能宣召于九州。
“安阳王城不受流民而入,尔等自行离去。”因妫翼曾将澹台不言的腿打断,澹台成蹊对妫翼充满敌意。
妫翼稳如松柏,一动不动。
“若你执意不走,休怪我下手无情。”澹台成蹊的怒气随着他的利刃出鞘,直冲妫翼杀来。
妫翼不忙不慌,直至澹台成蹊的龙渊直逼面门,才挑剑抵御。
两方剑气相撞,荡开层层厉风,令众人不觉身形趔趄。
在面对如影随形的白虹,澹台成蹊的龙渊应付的颇为吃力。他的每一个招式,妫翼似是都能提前预料,她出剑迅速,却又不伤及他体肤。
然而妫翼的退让,并没有使澹台成蹊放下执念,他愈加气急败坏,招式凶狠又凌厉。
妫翼不愿再和他耗下去,挽剑打掉了他手中的龙渊。
龙渊脱离澹台成蹊的掌控,飞至罗绮身前,斜插入泥土。
“趁我还未动杀心,快些离开。”妫翼剑指澹台成蹊眉间。
澹台成蹊怒气未脱,双拳紧握,怒视妫翼。
“你与乱臣贼子为伍,天下人必诛之。”澹台成蹊道。
君绫冷哼一声,缓缓上前,柔媚地笑道:“将军郎把话说清楚,谁是乱臣,谁是贼子?”
“你这妖妇明知故问。”罗绮道。
“孤不过是继位燕国新君,这才远道而来安阳奏禀,更何况昭明太子为孤自家兄长,世间大疫横行,孤不过是担忧他的安康,故而将他保护在王宫之中。”君绫道。
“倒是尔等,夜半不各自归家安寝,违抗禁令,对这少女穷追不舍。”在君绫囚禁了昭明太子后,颁布宵禁令,子时燕军巡城后,一直到巳时,城中各处不允许士、卿、兵、将聚集,违者绞刑示众。
“收起你那自己以为正义的姿态吧。”罗绮冷笑道。
“就在你离开安阳的这段时日,霍将军已经率军北上,如今正在宫中大肆清剿燕国叛军,待天亮,一切尘埃落定,绞刑示众的是你这妖妇。”
君绫如嗜杀的野兽瞥见猎物落单一般,黑耀耀的目光中闪着兴奋。
她笑得花枝乱颤,妖冶地模样如石缝中的浮花浪蕊,只凭观望,但凡摘取必摔下深渊,粉身碎骨。
这笑声在黑夜之中令人毛骨悚然。
妫翼心中暗道一声不妙,随即挥舞白虹,接二连三地将罗绮与澹台成蹊一众刺伤。
剑锋划过众人的尺骨,一众兵刃随即砰砰啪啪地落在地上。
偏生有怨者钟意撞南墙,一直未动的罗绮拔出面前的龙渊剑,笔直地向君绫刺去。
君绫笑的美艳,并没有躲闪。
妘缨见妫翼未动,随即掷出白虹剑的剑鞘。
剑鞘重击在罗绮的额间,他身形一顿,龙渊脱手后,仰面瘫坐在地上,额角迅速渗血而出。
“罗小臣话说的太满,孤瞧燕君风姿媚骨,与乱臣的贼鼠之相相差甚远。”妘缨推搡着霍繁香自角落之中走出。
躲在君绫身后的韩尤妙见到霍繁香,雾水般的双眸倏然变得透亮。
她抬起脚便要向霍繁香飞奔,却被君绫扯住青丝扥了回来。
韩尤妙半跪在地上,凄惨地喊了一声“痛”。
霍繁香听得韩尤妙叫这一声疼痛,登时也红了眼,发狂似地向君绫奔去。
妘缨眼疾手快,勾住她的宫绦,将她扯了回来。
君绫冷笑一声:“怎会有如此的机缘巧合,故人旧识,竟都在此处聚全了。”
君绫如丝的眉眼,轻瞟妫翼一眼。
这一眼是在向妫翼说明,她将白虹剑故意留在圣安,借此为妘缨留信的举措,君绫已经心知肚明。
妘缨注意到了君绫的眼神,故而道:“并非巧合,孤是得绥绥的点拨,特地前来寻燕君的。”
“哦?”君绫挑眉,等着妘缨的下文。
“想必燕君也知孤与昭明太子势如水火,尤甚在今年逐除,孤险些被他算计,死在周地。”妘缨道。
“如今,他落魄,最不愿见到的便是对头洋洋得意之相。”
“当然,除了给他添堵,孤更想与燕君结盟,共商大周继位人选。”
君绫昂着头,上下打量着妘缨。
她一身红衣如夜火,绚烂多姿,眉宇间透露着淡淡英气,使原本温柔的脸庞,透露着清冷和高不可攀。
可她,又颇为谦逊,不失亲和。
“若公与孤结盟,手中的人,可是投诚的献贡?”君绫问道。
妘缨点了点头,故意将霍繁香猛推在韩尤妙的身前。
“如今王宫被霍将军所控制,燕国又临靠郑郡,这灵川郡主既是霍将军的亲女,亦是掌管郑郡莘奴将军的义女,控制了她,便捏住这二人的命门。”妘缨道。
君绫不屑,道:“何须她,仅凭孤,千军万马也不过如一群蝼蚁般拿捏。”
“孤知燕君深藏不露,可毕竟死人太多,对燕君所新立九州共主的名声不好,更何况若众人死绝,燕君手上无所掌控,这游戏便玩不下去了。”妘缨几近权利旋涡涉险,心中深知各怀心思的诡谲,欲望与恐惧相互角逐,会将人的初心掩埋。
就好比君绫的初心,是复仇,是灭世。
可现在,她更想站在权力之巅,如神邸一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她想掌控一切,人之生死,世之兴衰。
君绫垂下眼睑,细细地想了想,她抓着韩尤妙青丝的手缓缓松了开。
“你想得到什么,如此费尽心机,不会只为了羞辱昭明太子吧?”君绫试探道。
妘缨淡淡笑意,坦然而语:“宋国掌管蔡郡许久,所求不过名正言顺,若燕君能将蔡郡划入宋国,孤将鼎力支持燕君任何决意。”
妘缨缓缓上前,靠近君绫耳边,又细声道:“若他死了,孤就不用担惊受怕了,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若他哪日见孤不顺,发兵宋国,孤难以自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