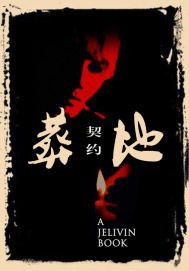孋姣于临盆前几日,在府上的水榭闲逛散心,刚巧遇到了回家省亲的孋婰。
孋婰自小便嫉妒孋姣性格柔顺,得人喜爱。
她见不得孋姣好,孋家人越是保护着孋姣,她越是讨厌孋姣。
她看到孋姣大腹便便地模样,想她是快要临盆了,便不怀好意地将木家的事情告诉了孋姣。孋姣在得知木家被诛,木二哥车裂于开瑾门后,急火攻心,随即难产。
折腾了一天一夜后,孩子是平安的生了下来,可是孋姣却血崩而亡。
孋上卿为此怒不可遏地将孋婰打出了孋家,并怒斥让她此生再也不许回孋家来。
此举不但得罪了孋婰,也开罪了楚王。
楚王罢了孋老丈的上卿官位,赐了他上饶之地,命他即刻前往上饶,告老种桑麻。
孋老丈的告老,不但使孋家大房和小姑姑所在的二房分了家,还使木丝言有了能逃出东楚的机会。
姑丈为楚国少府,另立别府时,因需避人耳目,便将木二哥的遗腹子交给孋老丈一并带去上饶,且为了保命,这个孩子自出生起,便要跟随母族姓氏。
木丝言为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灵筠。
逐除过后,孋老丈带着木丝言和灵筠便启程离开了东楚。
而就在他们才离开了东楚,白尧便被楚王封为了楚国的丞相,掌有金印紫绶,迎娶了姚家三女姚绾为妻。
这些事情,是木丝言护送孋老丈和灵筠到上饶之后,雅光公主派阿月来告知她的。
雅光公主仍旧被困在章华台,没有办法为木丝言送行,这才派遣阿月避人耳目,晚于木丝言几日离开东楚,到了上饶才与木丝言碰面。
白家如今已是东楚显赫,哪里还会能想得到罪奴木家。
不仅仅是白尧,自白素于伏水之战,一战成名后,被九州兵家奉为战神,被楚王封安邦将军,掌管楚国兖州所有军队,包括东楚的都城令。
所以,将雅光公主困在章华台的并不是楚王,而是白素。
楚王自继位之后,便在巴陵山下建了一座行宫,行宫的名为绣衣阁。
在外人开来,这行宫是楚王冬猎时才小住的宫殿,可实际上,却是楚国训练细作的场所,这些细作被称为绣衣使。
绣衣阁由白素和白尧兄弟二人监管,从亡国的俘虏中挑选可用之人,进行各种特殊与非人的残酷训练,经由三重考核后,成为绣衣使,渗入各国,为楚国利刃。
老蔡侯的死,便是白素派去蔡国的第一批绣衣使所致。
这些绣衣使潜伏在大公子叔怀的身边,诱惑他,怂恿他,亲手杀死了老蔡侯。
阿月告诉木丝言,自从白素得知雅光公主心悦于叔怀后,便致力于毁掉他们之间所有的情愫,破坏他们之间仅存的情谊。
他还威胁雅光公主,他掌控着绣衣使,监视着叔怀的一举一动,如若雅光公主想平平安安地出嫁,不想蔡宫之中再有暴病而亡的人出现,便安安稳稳地呆在她的章华台。
阿月将雅光公主送给木丝言的细软转交给她,与她道:“白素对雅光公主愈加放肆,甚有不轨之意,我需快些赶回章华台去,得了空再来看你。”
阿月转身上马后,木丝言叫住了她:“阿月,保重。”
阿月朝着木丝言点了点头,便调转马头往东楚奔去。
木丝言将雅光公主给她的细软自留了一小部分,将剩下的大部分留给了孋老丈,便一人浪荡于天地去了
她从隆冬里走到了春夏,又从悲秋中走到了初雪。
她一路风餐露宿,却从没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罪孽。
她走过孤寂幽静的山谷,落入过冰冷刺骨的洞庭,睡在寒露凝重的曼珠沙华丛中,最后倒在了广阔无垠的雪地里。
她浑身发抖,连心窝都开始变的冰冷。
她想若是她死了,便再也没有人能画出攻山之器的图纸,这天下便也不会再有那么多枉死的冤魂。
抱着这个想法,她望着灰蒙蒙的天,渐渐地睡了过去。
朦胧之中,她听到好似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一声接着一声,起初听着像华容郡主,后来又像二嫂嫂。
她浑浑噩噩,头痛欲裂。忽而,身上的寒冷逐渐被外来的温暖驱散,嘴中涌入一阵甘甜,她努力地汲取这甘甜,不知为何,竟然有些不那么想死了。
她这一生,从未做过错事,却被人利用,已经是家破人亡,为何还要搭上自己的一条命去?
她在梦里哭着,喊着,抱怨着,将所有的委屈一并发泄。
醒过来时,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吴桥县的姨母家。
将她从冰天雪地之中救回来,日日为她擦身,尽心喂她喝药的人,竟然是姨母的女儿,她的阿姐,时娴。
那日初雪,雪停了后,时娴要去雪地之中采冬青,炮制药材。见到雪地之中躺了一个人,便上前去一探究竟。
这一看,便认出了是木丝言。
时娴连忙找到附近的农户,并借了牛车,将她带回了家。
回到时家后,木丝言足足昏睡了十五日。
这十五日,都是由时娴一人衣不解带地照顾着她,也承蒙姨丈和姨母不弃,让她暂时有了容身之所。
历经家中变故使木丝言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坐在小院儿的藤椅上一座便是一天。
时娴见到她愁苦地模样,于心不忍,便与木丝言讲起自己在山中采药时,偶尔会遇到山兽的事情来。她笑着问木丝言可否愿意保护她,陪着她一同出门采药去。
木丝言盲目地点了点头,当真以为时娴采草药的地方真的有山兽,还在随行放置草药的背篓里装了一把镰刀备用。
哪知时娴不过是想让木丝言少困坐于家中,趁着林木苍翠之时,出来走一走,调整一下心情。
时娴采草药的深林中,最凶猛的山兽便是斑鹿,并且还在木丝言摘野果时,偷吃了好些个。
于林中休息的时候,木丝言恍惚之间想到早年前巴陵山的冬日,那个眉目清澈的少年,陪着她在林中的时日。
时娴看到她又发起了呆,将洗好了的野果放在她的手中道:“吴桥的野果可比东楚的甜,你快尝一尝。”
木丝言回过神,缓缓地笑了笑,拿着野果吃了起来。
“阿姐去过东楚吗?”木丝言问道。
时娴摇了摇头:“母亲说东楚是是非之地,想要一生平安顺遂,便不要出了华容郡。”
“不过,我倒是挺想去看一看东楚的,听说那里车水马龙,月夕节时的月神祭特别好玩,长街的市集要彻夜开着呢。”时娴的眼光发亮,那种对未来憧憬的眼神,木丝言也曾经拥有过。
木丝言笑了笑,没有说话,大口地啃起了野果,缓解心中的苦涩。
东楚的月夕节是很好玩,长街的莲花灯,月神庙的祭月舞,花鼓台的牵丝戏,百香楼的珍馐宴,还有景行阁的翠竹液。
东楚的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木丝言却永远都不想再回去。
时娴见木丝言又不说话了,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可是我说错了什么,又惹了你的伤心事了?”
木丝言将嘴中的野果吞进了肚子,立即摇了摇头道:“不是,就是想起来些以前的人和事。”
“阿言,你莫要总沉浸在以前的回忆中,人都是要往前走的,即使是闭起了眼睛,也是要往前走的,既然都活下来了,那便要好好活着,别总想着死,别再辜负每一个对你好的人。”时娴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道。
木丝言不知道时娴是从哪里得知这么多的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对于她来说,还是挺受用的,尤其是在劫后余生,什么都失去了的情况之下。
她逐渐地放开心扉,变得勇敢,将心里的伤长成了盔甲,保护着自己继续前行。
时娴的上面还有一位兄长,名叫时见燊。早年前曾在云梦城的公学学艺,回到吴桥后,在其父吴桥县伊的帮助下,设立了县公学,并在公学内授业。
他这些日子,瞧见了木丝言将时娴早前弄坏的炮制草药的工具,都重新修好,便问她会不会修一些桌案之类的物件。
木丝言并没有拍胸脯地去与他保证,先说看看是什么样式的案,她可以尝试着去修理。
翌日一早,她便被时见燊拉去了县公学。
放眼望去,县公学的外观虽然看上去挺不错,可内部的设施却很陈旧,连习字的竹简都要公学里的师尊亲自晾晒。
县公学的兴办基本都是由吴桥县伊,也就是木丝言的姨丈自掏钱袋的,姨丈一年的俸禄本就没多少,自己家中也需要开支,更何况还要支撑公学师尊的俸禄。
这也难怪时娴阿姐还要亲自采药,亲自炮制之后拿去医馆换钱。
木丝言在学堂之中转了转,仔细地观察了几个残破的桌案,而后便去了院子里,寻了一些能用的上的工具,开始了捶捶打打。
在公学授课的时候,木丝言见到来听学的都是些总角小童,有些连笔都不会拿,更何况要他们刻篆。
木丝言望着院子里面晒的竹简,无奈地摇了摇头。
休息时,她听时见燊对她说,现在正是农忙之时,吴桥县内但凡人家中有青壮年的,都是在田间干着农活,没有人愿意来公学听学。
可农忙时,又无暇照顾家中的幼童,便都送来公学这里了。
于是,县公学就成了吴桥的托童院。
木丝言有些好奇,便问时见燊,为何执着于兴办公学,要知道所有人都去做士族的门客,便没有人耕田了。
时见燊看着她温和地笑道:“你以为,我的教学都是如何让人成为士族的门客吗?”
“难道不是吗?”木丝言反问,“前去云梦城听学的,不都是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士族的门客,便不愁今后的吃穿了吗?”
时见燊歪着头,漆黑的眸子转了转,笑道:“你这么说,倒也是没错的,不过我办的这个公学,可与云梦城的不同。”
“有何不同?”木丝言想要快些知道答案。
时见燊朝她神秘一笑:“若想知道,你也来听学,就当是抵了修桌案的钱可好?”
木丝言撇了撇嘴,心想着她修桌案的费用可是很贵呢。
虽然嘴上说不愿意,可木丝言的身体却很诚实。
每天一早时见燊出门去县公学时,木丝言都乖巧地跟在他身后。
她坐在学堂的廊下旁听,除了听时见燊教教书习字之外,还有一位老者专门教农事的学识。比如何时种桑,何时收麻,何时犁地,何时除草,遇到虫害时要怎么做等等。
虽然这些都是最初级的农事知识,可木丝言与那些总角小童一样,都是只食过粟米却不知它是如何长成的家养米虫,因而听的津津有味。
她从没想过,原来农耕也是一门极为难学的课业,甚至还要会观星、观云、观雪、观雷,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
时间一久,她倒是成了县公学的常驻学生。
为了抵消时见燊的学费,她又将学堂内的桌案重新修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