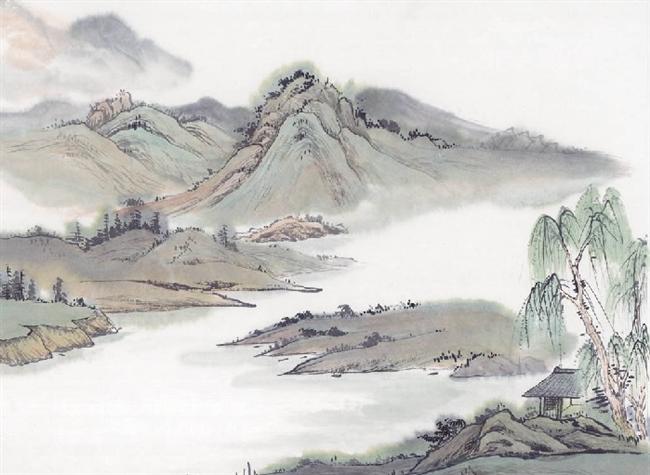“明日,我想同公主一起去。”她拉着我的衣袂,双眸渴望。
“留在圣安等我回来不好吗?”我拉过她的手,继续在黑夜之中行进。
“不,我不要留在原地等,我要与公主同去同归。”她声色哽咽,似是这话里勾起了她的伤心之事。
我不再执着与她是留还是与我同去,却开口道:“若是同归,今年的初雪,你依旧陪我去终首山祭奠师父可好?”
她双眸晶莹,缓缓地笑道:“好。”
临行前,我提笔一封帛书,让芊芊送去了绿婺宫。
我此去唯一不放心的便是妫燎,他为我身负重伤,可我却没能亲自去探望他一眼。
而绿婺宫的素素,自妫燎重伤之后,整日坐立不安,可为了不与我平添麻烦,竟是暗暗忍着忧心,不来我跟前求一次出宫探望。
我知二人的惺惺相惜不易,便亲自写了一封赐婚书让芊芊交给素素。素素是瞽者,看不见帛书上的字迹。于是我告诉芊芊在送帛书时一定要告知素素,请将这封帛书待妫燎醒来后,入宫见她时,呈上于他。他一见帛书的内容,定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启程时,小白藏于我的车马之内,芊芊隐于随行的婢女之中,只有我同百里肆二人在浩浩汤汤的队伍拥簇之中,高调地出了城门。
我掀开帘子回头望了一眼高大耸峨的圣安城墙,眼前不知怎地就浮现了第一次入尔雅时,见到尔雅城墙上满墙的芙蓉花来。
我想等战事平定,也移栽芙蓉花来,可转而又想陈国的天气似是不太容易使芙蓉花存活。
回到马车上时,便有些伤脑筋,暗自在脑中搜寻着哪些花可以装饰陈国的城墙,又能挨过陈国冬日的冰天雪地。
小白见我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还以为我是担忧路上的艰难险阻,拉过我的手便道:“不如我同你走水路,信北君和你的芊芊姑娘走陆路?”
我好奇地盯着他,心想着他这是讲的什么话。
他却淡淡一笑:“你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酸枣一般,扭曲的可怕。”
我连忙抽出双手,抚平脸上因凝思而凝聚的褶皱,解释道:“我在想,圣安的城墙要爬一些什么花而已。”
听闻我说此话,小白忽然收起了笑容,神情变的冰冷起来。
他的眼中掩藏着恨意,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
我吓了一跳,以为戳到他心中不堪的过往,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拉住了他冰冷的手指。
他回过神,缓缓地笑道:“想来蔡国的芙蓉花在陈国不易存活,不如栽一些朝颜花来。”
我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这倒是不错的想法,朝颜花本就容易存活,且生存力极强,移栽几株,转年后便能开出一大片来。
我一直在想着圣安城墙上朝颜花开放时的秀色,却忽略了小白神情再次变得冷若冰霜。
五日后,抵达银波镇。我同小白浓情蜜意地告白时,百里肆也转身上马,似是没有要同我走水路的意思。
我好奇地仰着头看他,却听他冰冷地说道:“臣不能安心将陈国的命运交于他人之手,想来公主决定以身为饵,便做好了万全的打算,少了臣的保护,也断然不会被楚人掳了去。”
他这是不放心小白手持兵符前去星谷关,才会舍了我,紧跟着小白。
我想他既然有这个担忧,倒不如让他跟着小白,总比一路跟着我,为我担惊受怕要好。
我离开小白的怀抱,朝着百里肆便是一拜:“我日后还要仰仗信北君,此去请务必要注意安危。”
“公主如是。”他目光灼灼,字句响遏行云。
他虽然嘴硬说不担忧我的安危,并毫无顾忌地跟着小白走了,可却将他身边最得力的护卫宏叔留在了我的身旁。
宏叔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旁,倒是让芊芊寻到了打趣我的话来。
我们一行人于银波城码头登了官船,缓缓地往星谷关的方向驶去。
妫水自银波城开始,便要经过九道峡湾,过了定陶之后便是一马平川。
父亲曾与我说过,早在他祖父颖侯时,这里的水盗十分猖獗,过往宋陈两国的商船和官船皆惨遭毒手,更甚的是连往来渡河的国人也不放过。
颖侯亲下旨意派人来此剿匪,在水盗隐患解除后,这里便逐渐繁荣了起来。
再后来父亲的父亲平侯将峡湾边上国人所安的住所修葺了一番,更在峡湾的每道停歇处设驿站,酒肆,歌台等供往来船只休息。
每到春夏两季丰水期时,河流丰盈,妫水澎湃,鱼虾肥硕,亦是船游妫水的好时节。九州上曾有一位的歌者在船游妫水之后,曾唱遍天下“天接云涛连云雾,长河已转千帆舞。”
如今正是深秋之时,妫水上早已不似春夏那般热闹,碧绿的江面之上,唯有我们这一只官船乘风前行。
自昨日一早登船,我便随时保持着警觉,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身探看。由此,昨夜整晚我几乎没怎么入睡。
芊芊觉着我紧张过度,早饭过后便催我去榻上休息。
她告诉我,宏叔早就派了护卫伪装成打渔的渔民先行探路,如若前方有何不妥,必会来报。
我再这般紧张不安,星谷关还没到,我便把自己累死了。
我听闻之后,便安了心,怀抱着装着玉盘的木匣倚在榻上,翘着腿闭目养神。
忽地前方传来一阵粗犷又悲情的歌来,我睁开眼,坐起了身,细细地听着歌中的诗句。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坐于我对面的芊芊也听到了歌声,她猛地起身将开着的舷窗重重地关了上,捧着棋盘来问我可否陪她下棋。
我苦涩地笑了笑,沮丧地趴在案上问道:“他们是在怨我掀起了征战?”
“他们只是不知这场征战并非公主所愿罢了。”芊芊安慰道。
“我在他们眼中早已是引起战争的红颜祸水了吧。”楚国攻来陈国的缘由便是想得我入楚国,或许在国人心中,我同孟姜一样,皆为祸国红颜。
想来也是,我什么都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们又凭什么为我而战呢?
“这同公主有何干系。”芊芊冷笑道:“不过是窃钩者为贼,窃国者为侯罢了。”
“倘若如今是陈强楚弱,可见他们还能有这番说辞?”
“说不准,那时的他们恨不得为公主鞍前马后,只为求得军功,论功行赏呢?”
我瞧她维护我地模样,倒像极了百里肆。然而一想到百里肆,我便更加忧心忡忡了起来。也不知他们现在行于何处,是否安然无恙。
芊芊见我垂眸凝思,也便不再多言,她将棋盘布好后,自娱自乐起来。
我越是忧心过重便越觉得无所期盼,索性不再乱想,转身去瞧芊芊下棋。
她的棋艺甚佳,许多我看着明明是死路的棋局,却被她一子落后,尤有余生。
我歪着头,有些好奇,便与她聊起了她的东楚旧事。
翌日一早,才用过早饭,宏叔便神情紧张地入房来报,说前去探路的护卫在靠近什方镇处瞧见有黑衣人在峡岸旁设埋。
听闻此消息,我内心担惊又欣喜。
欣喜的是楚人的围堵来的如此之快,便有可能是认定了兵符在我的手上,这样小白和百里肆便能安然无恙。
担惊的是,若是楚人认定了兵符在我手上,怕是埋伏不只是什方一波。
我回过身,连忙令芊芊将我的戎装银甲拿来,如今我要做的便是为百里肆拖延更多的时间。
芊芊并没有为我命令所动,她笑着看着我,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隽永深刻。
而后,我脖颈间忽然一痛,便没了知觉。
“再见了,我的公主。”我耳边传来一声淡淡的叹息。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然渐暗,宏叔正跪坐于我身旁,我坐起身发现仍旧在船上,环顾四周却不见了芊芊的踪影。
“她背着木匣代替公主下了船,引开了那些藏于峡岸边的埋伏。”宏叔将怀中的裹着锦布的玉盘递给我道。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宏叔手中的玉盘,胸口沉闷,仿若有巨石压着喘不过气。
“我们可否过了什方镇?”我即刻调整情绪,开口问宏叔。
“刚刚行过,并且先前看到埋伏于此处的黑衣人都不见了踪影。”宏叔道。
我喉咙泛酸,忽地觉着一阵恶心。
宏叔见状连忙问道:“公主若是不适,便叫随行医官来瞧一瞧。”
我连忙摆摆手道:“不必,许是整日困于船,有些积食了,过了什方便是楴川,此处峡岸多林,善于藏身,还劳烦宏叔多加留意。”
宏叔俯身朝我一拜,便转身出去了。
我颓废地坐在塌边,看着芊芊曾布过的棋局,终于忍不住地细声哭了起来。
她同我一样,都想挣脱开命运的桎梏,可最终却不得不再回到原点成为囚徒。
这一夜,我靠在凭几上几乎没怎么入睡,待破晓时分,宏叔突然传入房间之中,拉着朝外跑去。
官船的两旁停着两艘小船,宏叔带着上了小船后,继续在水上的浓雾之中穿行。
冰冷的秋凉拂面而过,我虽清醒了不少,可身上却发起了抖。
宏叔见此,卸下了身上的斗篷披在了我身上。
此时的水面浓雾缭绕,压根看不清前路,只能缓行。宏叔警觉地吩咐两艘小船并进,注意四周。
少顷,我的身后忽然现出一片火光,虽隔着浓雾看不清,但瞧方向也知是方才我乘坐的那艘官船起火了。
随着巨大的火光,还有阵阵求饶声。
我惊恐地看着宏叔,想来他方才就知道我们的官船被人盯上了,这才拉着我乘坐小船逃命。
我后怕地摸着怀中的玉盘,如若不是宏叔想来我早已经死在船上了。
宏叔低声命人加快船速,可才刚刚行驶的快一些,便从迎面的浓雾之中刺来几十余支羽箭。
宏叔将我护在身后,抽出长刀抵御刺来的羽箭。
“靠岸。”宏叔低声喊道。
接连而来的羽箭将船逼靠到了岸边,宏叔为了护我,肩膀上挨了一箭。
他将羽箭砍断,待船停靠于岸边之时,拉着我一同往岸边上去。
如今的天色已然大亮,我回身望去,却见我们方才行船的地方飘着三两只轻舟,那些迎面而来的羽箭,便是从这几艘轻舟之上放出的。
宏叔吩咐剩下的护卫将围在中心,然后快速往前奔走。
行至江畔的一处八角亭,宏叔突然停了下来。
我随即仰头望去,透过已是枯黄的枝桠,见正有一人坐在亭中,悠闲的煮茶。
深秋风凉,尤其在这人迹罕至的山野之间,没有人会兴致高昂到来此吹凉风煮茶。
宏叔摆了摆手,示意朝旁路走去。
我没有动,直直地盯着亭内的人。
想来在什方时,他们就已经抓住了芊芊,知道她身上的匣子是空的,便又在此处再次设局,既然已经让我逃掉了一次,这第二次便不会那般轻易地再让我逃了。
“既然公主不逃了,不如上来与我共饮一杯如何?”那人一席绀青衣袍,两鬓的青丝在脑后盘成一个节,发丝随风而起,萦绕周身。
宏叔认为我被吓傻,无法前行,便行至我身前,突然拉着我奋命往前跑去。
我惊的说不出话,却见林间暗影簌簌而过,忽然四周冒出来许多手持着画戟和璎枪的黑衣人。
“是你们自己上来,还是要这些人请你们上来,兵刃可不长眼,别怪我没提醒公主。”那人笑道。
我稍稍地安抚了宏叔,并用眼神确认我无事,而后仰起头与那人道:“想要与本公主共饮的人多了,阁下不亲自来请,便显得毫无诚意,如此的待客之道,还当真不敢恭维,想来也是,楚王收服诸多蛮族部落,却大都习惯掠夺而忘记教化,久而久之楚人也大都同化于蛮人,礼节崩塌。”
那人冷笑了两声,忽地从亭内踏枝而来:“如此,那我便亲自来请公主。”
我这才认出亭内之人是白素。
可是他如今不是应当在息国驻守吗?
“若是等一下拼起命来,公主定要躲在我的背后,可记住了?”宏叔在我耳边细声说道。
我暗暗地拉住宏叔的手臂道:“保持警惕,等我暗号。”
白素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有些奇怪,他的武功已是万夫莫敌,按照他平日嚣张的作为,应当是直接劈过来杀掉宏叔,将我擒了。
我心底暗暗留了心思,便开口道:“将军入我陈国是得了谁的通行令牌,还带着这么多兵卫,怎地我这个陈国公主怎么全然不知呢?”
“大概是余陵郡守的通行令牌吧,他没来得及跑,也不肯屈服于楚国,所以我便将他一家都屠尽了。”他从腰间结下一枚猩红色的令牌,这令牌的颜色显然是被血迹浸泡过的。
我心里一抽搐,眼前本能地又浮现恶梦中余陵的那场大火 。
我放开宏叔的手臂,轻轻地道:“就现在,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