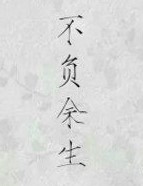肇淑丽对克珏,如果说没有半点感情,那肯定是假的。
因为克珏,是她生命中第一个能让她真切地感受到依赖感和安全感的人。自从认识了克珏以来,每当她遇到困境、或是遇到突如其来的心悸,她貌似再也不曾感到过绝望,就好像她的心中,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个“底”。
她一直期盼着她的“白马王子”,但真正的“王子”到底是什么?她思索过,她反省过,一个爱人的什么最值得去爱?如果仅仅是所谓的容貌、荷尔蒙,亦或是所谓的异性吸引力,那她已经尝试过了,并且不止一次地接触到了异性最肮脏、最令人作呕的部分,无论是丑陋的面目还是兽性的心灵,她已经,再也不敢去幻想“白马王子”的存在了。
异性对她的伤害,从身体发肤伤入心肝脑髓,她濒临死亡。她一天天看着每一处即将痊愈的伤痕不断被再一次败坏,并最终结下丑陋的痂。
直到有一天,她在消毒水的气味中醒来,看见那个趴在病床旁睡着的白衣“少年”,一个将她带离苦海、宁愿为她附上全身伤痕的,还是,一个拉拉。
而她,曾被她的这层身份吓呆过,更是在知道她对自己的炽热感情后本能地排斥过她。可这个人,一个这么好的人,却为她做着一件件“白马王子”分内的事情。
想起她的一切,肇淑丽的心忽然变得温热,这是她对她的感情,她告诉自己没有必要回避自己的心意。或许,接受这份感情,对自己、对克珏,都是好事。
她接受了,她给了克珏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刻。
此刻,她正将脑袋歪歪地靠在克珏的肩头,闭上眼装睡,时不时偷偷眯起眼睛瞄向克珏,她喜欢看她打着哈欠却仍要拱拱眉头硬撑不睡的模样、喜欢看她低头专注地玩着手机时被荧光映亮的侧面、更喜欢看她挠着头发想事儿时一脸纠结的表情。她爱她的单纯,因为这能让她多少沾染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年轻气息。
火车站的一号候车厅偌大而拥挤,夜晚高峰期来此候车的人,运气好些的,能抢到恰好够塞屁股的小块座位;运气背些的,也能挤进座椅周围的地儿坐下,将厚重的旅行箱当作座垫;运气差的,也好歹能向蹭得到中央空调的位置挪步。
而她们,正坐在这间候车厅的一排铁质长椅上,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对中年男性有了心理阴影,淑丽选择躲进克珏的怀里小憩。
此行,是她俩的蜜月之旅,但主要是为了送炘宏回帝都。
发车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现在就剩二十分钟了,加上还要排队检票,克珏担心炘宏再不出现恐怕会迟到,她再次给他打电话,然而刚“嘟”了两声,竟然被挂了。
“玉哥,晚上好,”克珏的肩膀被拍了两下,她抬起头,看见是炘宏,咧起嘴傻笑,炘宏望了一眼睡着的淑丽,又看看周围的狼藉,捂住鼻子,“别怪我踩点,这种地方能少待一秒是一秒。”
排队检完票,三人带着各自的行李,跟着人群下了坡,穿过了地下通道,找到了这趟车的站台标识,刚踏上一半楼梯,站台的风就直接灌了下来。
炘宏走到靠近黄线的地方止步,呼啸的风拨乱了他额前的中分,但他依旧装作惬意地扫视着下方与远处那浸在一片黑暗中的火车轨道,他什么也看不见,但看不见,或许会比回过头目视着蹲在一起你侬我侬的克珏与淑丽、然后还不得不努力挤出祝福的笑容要让他好受些。
“周围人都盯着她俩看呢,真是不害臊,我应该避避嫌。”他这样告诉自己,仿佛这是他可以装作不认识她俩的理由。
“红姐,你带了啥吃的没?要不咱们分一下?”然而克珏却没这心眼。
“啊咦西......”他此时巴不得跳进铁轨,“上车再说!你急什么?”
车票三张,是炘宏统一订的,然而他实在没能抢到三个连着的卧铺,其中两个倒是上下铺,但另一个,却在另一节车厢,并且和那俩之间,隔了八节车厢。
“红姐,谢谢你啊~”她帮着炘宏一起把大箱子抬上了高高的货架,“你放心,我等会儿去那节车厢帮淑丽安置好了行李,就过来陪你聊天。”
“那还是不必了,”他的语气异常冷漠,“我看你倒挺困的,过去就早点儿睡吧,等你走回去淑丽都等急了。别忘了,明早五点半就到了,我看看...好了现在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了。”他看了看手机时间。
“没事儿!我不困!我还得帮淑丽守夜班儿呢哈哈哈。”
“嗯。”他理包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双眸无神,声音极细地吐出了这一个字。
“好啦!”克珏拍了拍炘宏的肩膀,声音挺响,“好好休息,可别怕黑哦~不过玉哥放心,咱们红姐可不是一般的淑女,没人敢欺负,对吧?”
她话音刚落,车厢里的灯突然就灭了,时候太晚了,乘客们都还要睡觉,只是炘宏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她一个苦笑。
炘宏趁着黑转过头正视了她一眼,虽然看不清五官和表情,但不远处车厢中段洗漱间的白灯光却依稀将她面庞的轮廓勾画出来,他看着她仿佛在笑,又仿佛在迟疑些什么,然后察觉到自己的肩头又被她拍了两下,他感到有点疼,却又能依稀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他突然希望这种痛感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他莫名害怕自己会失去她的温度,然而,这温度并不属于他,所以到底还是没有了。
他慌了,他不知道自己对克珏的友情怎么会就这样变了味,他更不知道这是种什么情感,这迫使他不断回忆起自己的每一个朋友,努力在寻找一个类似的案例,他自我催眠式地将它扯到了友情的层面,他和鸣祐、以及另外一个发小,在面对分别的时候或许也会像现在这样吧,心头空落落的、身体也软绵绵的,在浓烈的困意中却仍然能怅然若失到辗转难眠的地步。
车身不断颠簸着,正如他的此起彼伏的心绪,他觉得像这样啥也不干地摊在床上就是在浪费时间,索性翻过身,匍匐着爬向窗口,然后微微拉开了蓝色的列车窗帘,打算看看外头的风景。
可惜他睡在车厢中铺,在这种俯视的角度下他只能看到漆黑一片的地面,他想看窗外的夜景,并且可以顺便,等等克珏。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但他心里,还是很希望她来陪自己的,他也知道有淑丽在,克珏过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愿意相信“奇迹”,他可不想还躺在床上就被克珏叫起来,这样可不优雅。
他坐在靠窗的翻板凳上,给手机充着电,撩起窗帘看向比漆黑的车厢明亮很多的林间景象,他看见近处快速闪过的一棵棵树木、看见黛色的夜幕上一群密集的星子、看见不远处转瞬即逝的城市霓虹。
都不过是些寻常的景物,但是空间的快速移动却为它们附上了几分生动的空灵感,炘宏喜欢这种感觉,可是这却让他不合时宜地记起幼时曾听过的几个关于列车的灵异事件,并且出自一个女同学在铁路上当列车员的母亲之口。
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仿佛一回头就会真撞见鬼,这让他愈发期盼克珏能快点出现。
人,一旦想得太多,就会自讨苦吃,就像此时不断冒着冷汗的炘宏,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一群鬼魂围了起来,他再次泛起反胃的感觉。
渐渐地,他看见起床的人多了起来,有一对估计已经在车上睡了很久的老夫妻坐在炘宏不远处的边座上,因为翻板凳的朝向,使得他们只能侧面对着侧面坐着聊天,活像清朝娘娘们的唠嗑坐法。
他看了看手机,也才刚到凌晨两点半,不过在列车上,本身就不分什么昼夜。
附近的人气儿这么旺,他自然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便拿起正在充电的发烫手机,点看QQ空间看了看自己刚出发时发的动态,一共有三十个人点赞,下头鸣祐还评论了一句:“你的自拍呢?真反常。”
是啊,真反常,他怎么会忘记在临行前拍张照呢?是因为什么影响了他吗?
他看着自己随手拍的高糊车站,毫无美感可言,尤其忘记用美颜滤镜,很敷衍地就发了一条说说,这真是不符合他的处女座性格。
他边喝汽水边看着手机里的小说,还花流量看了几个短视频,时间一晃,就到四点了,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他的玉哥,却还是没有来。
他垫脚从货架上扯下装有钱包的单肩包,挂在肩上,走向车厢的另一头,他打算去找克珏,因为天色已经亮了,他的胆子也跟着肥了。
等到他终于来到了克珏的那节车厢时,他仿佛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累得满头是汗。好不容易找着了克珏的中铺,却发现没人,一低头,却看见她与他,正抱在一起挤在下铺,克珏睡得很沉,打着呼噜,淑丽倒是安静得很。
他呆视了良久,看见了克珏脸颊上粘着奇怪的东西,凑近看才发现是散掉了一头的创可贴,她脸上的伤口已经结巴了,但还是有些红肿。
他知道,常年在外“厮杀”的克珏负点伤自然也是常事,而且,她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或许真的可以豁出性命,炘宏却心疼,他觉得自己现在纯属只是把自己当成克珏的妈了,这么神经大条的幼稚鬼,如果没有心细的人照顾那可怎么办。
他瞄向淑丽,这也是个让他心疼的人,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为之揪心。他脑海中不断浮过一句“她会照顾好克珏的。”然而双手却还是伸进了单肩包里。
而淑丽,她是醒着的,她微微眯着眼看着炘宏,看着他将包里的芦荟膏掏出,蹲下身子,然后挤在手指上,轻轻地用食指和中指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克珏的伤口处,替她将创可贴的另一头贴好,最后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她猜测,他也许会独自离开,但她还是没有叫醒克珏,因为,她被他的举动吓到了,她怕起他来了,哪怕,她心知肚明,那次在宾馆是他救下了她与克珏,他本应是她的恩人。
车一到站,炘宏早已整装待发了,他在克珏打来的电话里告诉她自己要先走,并且祝她们好好玩。克珏,第一次生炘宏的气了,她挂了电话,时候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怒点。
五点三十一分,炘宏拖着行李箱,绕过人群,面向站台尽头那愈来愈亮的地平线,天色青的好看,但原本预示着万物苏醒、昭示着希望的日出,却成了炘宏眼中告别的标志。
他走进荒凉的地下通道,他对着微信录音向新男朋友哀伤地求着安慰,他看着石沉大海的语音消息,他想起新男朋友答应来接他时那温柔而仿佛近在耳边的语气,他后悔自己本应让父母送自己来帝都,他体会到自己无边的孤独,他听见路过的老大爷手中收音机里放出的凄厉悲惨的京剧唱腔,他看着自己的影子。他止步,鼻尖一酸,仿佛喘不过气一般地啜泣起来,他像个委屈的孩子。
他第一次不顾周围路人的眼神,放肆地哭泣,他的身上一阵冷一阵热,他感觉自己即将死去。
有些人、有些事,如果无法继续面对、但也不忍割舍,那便最好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