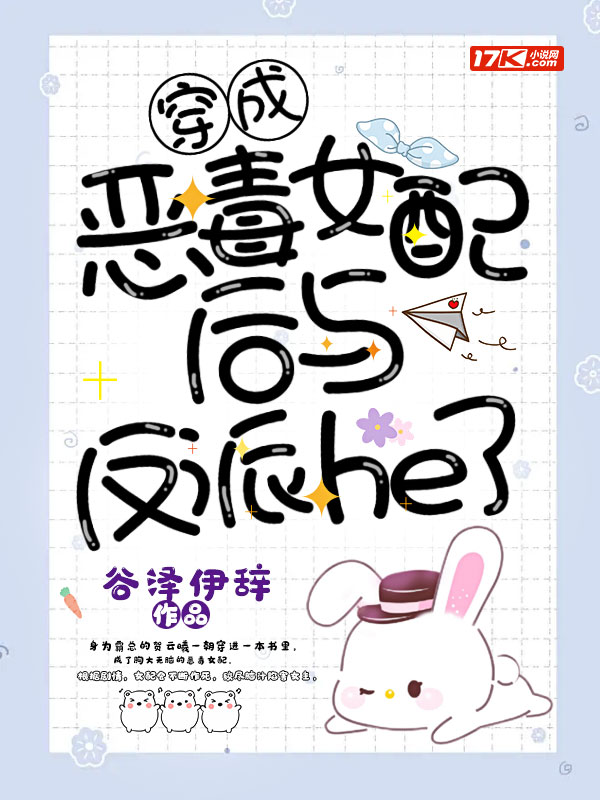惴惴不安,绝对是人世间最折腾的病毒之一,它总能携带着使人不断自我矛盾的情愫,刺激大脑皮层,进而引发反胃、头昏等不良症状,并且无药可治。
炘宏憎恨这种感觉,更憎恨这种人类天生的情绪设定。
他幼稚地将负面情绪喻作各式各样的病毒,无非是想为自身因素开脱,好把所有的不幸与不悦,都归咎于某些客观因素——都怪它们,害得我这么生不如死,真想把它们从脑子里抽出来。
然而,现实告诉他,它们住在人心与脑海的深处,抽出来?不要命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幻想着一个不会紧张、恐惧、悲伤的完美自己,一头看着车窗外的世界,一头思索着思维内的天空。
他极力分心,他极力放空,他不想被自责与不安吞噬,他不想自己的灵魂被多愁善感的思绪所累死。
他还是想起了昨天,在微信上和那个聋人少年用英文交谈时,自己激动而龌龊的心情,以及自己是如何如履薄冰、满是套路地组织着语言,一点一点将天聊热、又一步一步地将他的性格大致摸清并且最终把他约了出来。
炘宏先是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然而这人居然没有“girlfriend”的概念,十分疑惑地表示不解,而这种白纸一样的单纯更是勾起了炘宏的“欲 火”,他非常想见到他,因为说不准,最后兴许还能发生些什么。
炘宏的脑中进行了一场斗争,良心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人,而不良的心却安慰他,这种行为对那人根本造不成伤害,甚至可以说是在帮他。
他心动了,打着见面一起运动的幌子向他提出了邀请。
他发了一个定位给炘宏,那是他时常跑步的小公园......
此时,炘宏正煎熬地坐在开往公园的大巴上,心跳得仿佛比车身的颤动得还快。
大巴停在了一个炘宏很熟悉的站台,他微微伸长脖子,隔着车厢前部门侧的透明窗,向外望去,只见一干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人头,密集而汹涌,和往日里一样,在这一站上车的人总是能排遍整个站台,并且,还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这个站台附近是这座城市的“老人区”,因为五十年前的这里,是一座电厂,附近全是为电厂员工配备的公寓楼,在当时,这些房屋尚且前卫先进,无数居民看着眼红,风光一时,然而时过境迁,这些五十年前的年轻员工,全都步入了老年时代,而这些半旧不新的楼房,也全都成为了楼盘开发商最头疼的“眼中钉”。
炘宏的外祖父母,就住在这一带。
他眯起眼睛左顾右盼,本抱着点儿好奇心打算看看这些老人里头有没有熟悉的面孔,谁知他唯一熟悉的身影,竟是他的外婆。
他突然开始直冒冷汗,这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愈发浓烈。
他看着她坐在橘黄色的“老弱病残孕专用座”上,扭过头看着车窗外。
安静而文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婆的背影,不禁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一个光头驼背的老头被人潮挤到了炘宏的旁边,炘宏稍微往里靠了点儿,因为不想碰到老头满是汗渍的白色衬衫,然而他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老头不但颤抖着的双腿,他呆视了片刻,便索性站了起来,绕过老头,并且轻轻用手推了推他,示意让他坐下。
老头僵硬而费力地微微转身对着炘宏笑了笑,然后比了个大拇指,脑袋一直发颤,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仅仅在冲他点头而已。
前后座的年轻人见此景也纷纷都坐不住了,陆续拉过周围站着的老人,给他们让座。
一个大嗓门的大妈边喊着“谢谢”,边在那儿叨逼叨叨逼叨地和其他老人说个没完,什么“咱们这一代是都老了”、“这车厢也太小了点儿”、“现在的小孩都挺懂事的,又都生的漂亮,我那小孙子......”
尤其是接下来突然冒出的一句“这小伙子就很好,长得白白净净,还头一个让位,真懂事。”更是把离神很久的炘宏突然刺醒,炘宏尴尬地冲着大妈笑了笑,欲言又止,然而余光发现外婆正在扭头看向这边,他立马侧过身,往人群中挤了挤。
车厢没过多久又空了,炘宏便挑了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弓着背让前排的椅子挡住自己,以免被外婆看见。
他此时并不想面对外婆,或许因为外婆在他的心中,是个温暖、光明、理智并且清流一般的化身,而自己现在却是何等丑陋、龌龊、肮脏的一副面孔。
他一直学不来在这种苟且的心情下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起码在最亲最爱的人面前,他永远也做不到。他希望能在这些亲人的心中留下最完美最正常的形象,希望他们永远爱着自己,因为他害怕失去这种原本最坚固的感情。
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玻璃,随着车身的行驶而移动着,印在并扫过外婆微卷的染后后发、外婆稍有细纹的后颈、还有外婆那单薄的肩背。
因为瘦,外婆脸上的皮肤早已松弛褶皱了,因此看起来并没有比自己本身的年龄年轻,但背影却是如此的纤细,没有其他老年大妈发福后的臃肿,而是娇小玲珑,愈发显得年轻。
重要的是,炘宏多多少少能在她的举止、神态中,看到妈妈的影子,然而在这之前,炘宏从来没有发觉妈妈和外婆的相像。
他想起外婆和外公站在一起的身影,那时候,外公那细长的腿还是健壮有力的,他俩每天早晨天刚亮,便会一起出门,手拉着手,从这座城市走到一座城镇,赶一趟农村的早市把一整天的食材都买好。
那时的街道还没有很多路人和行车,天地间便只有两人携手并进的背影,这是何等浪漫的画面,炘宏甚至都不相信这会属于这样一对老夫老妻。
后来,外公的腿脚不好了,还时常犯困、犯懒,不爱出门、不爱走路,外婆便只能自己一个人,每天照常赶着早市、照常在晚饭后到附近的小公园散步。
他就这样,窥视着外婆的背影,神游了好一会儿。待他回过神来想起自己即将要做的事、要见的人,他突然不知所措了,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无数或近或远的亲戚,他并不缺爱,他并不缺陪伴。那么,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单纯满足一时的“色心”?但这又是一件多严重的事情,他虽不相信“公序良俗”、他甚至不怕“丧尽天良”,只是何必呢?何必要为了一件也许并不利己的小事而将自己置于水深火热的自我煎熬里呢?
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有些憧憬男女之间的爱情,然而他片刻便收回了这种想法。
车停了,他赶在外婆之前先跑下了车,躲在车站广告板的后面,目送外婆走进公园的大门,长舒一口气,掏出手机,毅然决然地给“LOVE”发了一句:
“I’m so sorry,I can’t go to there,I don’t have 520yd.com you next time!”他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这段“孽缘”。
他望了望四周,突然感觉有些眼熟,看到不远处的小别墅才霎时间回想起来——侯克珏的家。
“喂,玉哥。”他尽量发出最热情地声调。
“啊,红姐啊,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呀?怎么了?”一听是他,克珏不禁咧起嘴微笑,扶着腰“老态龙钟”地走到了卧室窗台前——她的腰还是闪了。
“我这恰好路过你家这边,我......”他就是很想找人倾诉,而克珏,在给他一种可以很亲近的感觉,毕竟他俩之间,有那么多“相反相成”的地方,这是鸣祐在那次漫展上扯出来的恭维话。
“你想来玩吗?...啊对了!”克珏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然而炘宏却没有想着接过话茬,因此......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我正好有件事想告诉你!”
他俩,居然异口同声了,两人都被彼此间的默契震惊到了。
他们对着手机呵呵傻笑了一会儿,然后炘宏便在克珏的指示下找着了克珏的家门。
炘宏让克珏先说,于是那些有关肇淑丽的一切“奇妙”的事,她统统都分享给了炘宏。
炘宏呆了好一会儿,仿佛看完一个意犹未尽的灾难片或者是惊悚片,总之,他瞬间觉得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了倾诉的必要,况且,光顾着张口闭口一个“淑丽”的克珏,也全然忘记了炘宏也有话要说。
......
轻缓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淑丽把手中的电视遥控器扔在一边,从柔软的席梦思上跳起,她知道是宾馆打扫卫生的来了,便喊着“来了来了”走向房门。
可当她打开门的一刻,她仿佛看到了鬼一样,试图立马将门关上,并且发出低沉的哭腔:“怎么是你...给我走开...出去...出去啊!”
“淑丽,”龙哥用力顶住门,故作暧昧地说道:“你可真难找啊,宝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