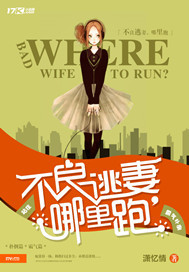那是她二十五年人生至今做过的依旧存留在记忆中的最美好的一个梦了。
天空是湛蓝的透澈的,阳光是和煦的明亮的,脚下的草是鲜嫩的温软的,就连妈妈,从来都是内敛淑雅喜素喜静的妈妈也穿上了她从未见过的热烈鲜艳的红色裙子。一双白皙的玉足赤裸着轻踏在蓝天下,及腰长发在身后不住摆荡,她时不时回头看向身后的自己不断催促的模样,可脚下却未停——
“快看啊初阳,爸爸就住前边树林的木屋里呢,咱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她看得出来,妈妈那是真得开心,就连唇角的笑都是开怀又轻快的,是即将见到心上人的迫切与激动。不是少女,仿若少女。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初阳快跑啊,咱们去找爸爸,去找爸爸啊初阳!”
她跑得极快,小小的自己却是无论如何都追不上。
“初阳!”
又是一遍初阳,又是一声叫喊,可它却不是宠溺轻盈的,它很急切,它很凄厉,似是来自骨血,带着绝望。
这凄楚无望的声音对于正常睡梦中的人来说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惊悚可怕了,但奇怪的,她只是不带任何心情地机械般地睁开了眼——
一头巨型的灰白色怪兽袭击了妈妈的后脑。
那头乌黑的秀发散落开来,混着粘稠温热的液体,粘在了她的脸上、脖子上。它们是魔鬼,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将她囚禁。自此,她的世界将只剩黑色和血色,茫茫无尽,只剩折磨……
江初阳猛地睁开了双眼,眼前没有什么蓝天绿草,红裙骄阳,更没有怪兽鲜血,乱发囚牢,有的只是安静发光的床头灯,和因咬合得过于用力而隐隐作痛的牙床。
她躺在那没动,一吸一呼地喘着气,许久之后才压下了心头的恐慌。她张了张嘴,发现嗓子干涩而压抑。
“活该。”
几丝平淡,无尽嘲讽。
江初阳起床开了大灯,一瞬间亮如白昼。
她慢慢踱着步,最终停在了镜子前。
镜子里的人面色苍白,满头是汗,平日里透软顺直的长发此刻也乱蓬蓬的,粘湿在额头、脸侧和脖颈,狼狈得很。
她眼神无波平静异常,随后咧了咧唇,离开原地,两分钟后再原路返回,没有什么不同,只除了手中一把剪刀。
————
宋翊殊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稍微重点的声音都能将他吵着。
如同此刻,他便怀疑自己听到了摔门的声音,但醒不透脑神经只是稍微打了个转,随后就继续寻梦去了,因而床上的人也就只是翻了个身,阖了阖本就没睁开的眼皮,再次自顾自地熟睡了。
夜色深重,空气清冽,道路空荡荡。
江初阳再次见识了A市的凌晨夜景。美则美矣,倍显空旷。
她车开得像龟爬,像个游街乱逛的,不紧不慢。好在大半夜的,也不会因为有人不爽于她这样的速度影响秩序而将喇叭按得震天响。
她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按下了车窗。
空气多冷啊,轻轻吸上那么一口,都好像要将鼻子给冻通透了,然后再直达肺腑,让整具身体都得抖上两抖,一刹那间,甚至眼中都能盈满泪花。
江初阳微微激动着,这次要成功了吗?
她甚至都舍不得眨眼,生怕将眼底那点晶莹被眨没了。她使劲瞪着双眼,就想以此来证明些什么。
冷风轻轻吹,纤白的手指手指摸了摸眼角。
“嗤!”终归是妄想。
微微一动,窗子又缓缓升了上去。隔绝了冷风,身体又开始重归温暖。
被虐是别无他法,自虐却是不可饶恕。
她踩下油门,车子疾驰起来。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孤独。
本是毫无目标,纯属闲逛,但江初阳看见了“拾色”。寂寂寒夜里,唯它灯火辉煌,一片喧嚣。
她勾了勾唇角停下车:“倒是好去处!”
“凭什么!我不就是没钱吗!呜呜呜……笑笑,我不就是没她有钱嘛!一栋房子啊,他妈的就一栋房子啊!呕……呕……我郑佳八年青春八年爱情他妈就抵不过一个三室两厅……”
“笑笑,我错看他了!错看他了……”
江初阳顺着两个女孩离开的方向看去,心下一阵恍惚。这看似繁华的大都市里,哀痛的人却满地都是。
她伸出手使劲裹了裹羽绒服,将脸往围巾里深深埋去,就留一双冷静又清淡的双眼。
这天,可真冷啊!
她进门了,进入了一个与门外完全不同的,温暖的、热闹的、充满人气的世界 。
她痛快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好了那么几分。压了压帽檐,直奔着吧台去了。
“一杯Mojito,一杯温水。”
她动作言语十分自如,但过分严实的打扮还是让调酒师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怎么?”
江初阳是一个敏锐的人,察觉到了对方“多看的那两眼”,她微微抬头眯着眼睛看过去。
调酒师猛地一震,突然回过神来,几乎要失手打翻手中的器皿:“马上就好,您稍等!”
他转身开始忙活起来,心中却仍是带着些许挥之不去的震颤。那双眼睛在帽子的遮掩下显得愈发漆黑深邃了,刚刚他一眼看去,平淡之下竟尽是清寒,因此瞬间就失神了——
同样也是失礼。
江初阳随意勾了勾唇,把目光重新放回了人群之中。
低吟浅唱的,亲密耳语的,甚至肢体碰触的,人虽远不如周末时候来得多,但倒都不寂寞,没见到单独一个人瞎逛或是格格不入的……
“轻慢用。”
江初阳回头,用手支着下巴,轻轻笑着懒懒出声:“你这双手倒是好看。”
调酒师是个纯情的年轻小男生,听到这话就红了脸,耳朵上也蹿上了一股热意,下意识顺着对方的目光低头看去。
骨节分明,白净修长,好像确实是挺好看的。
他抿着唇又悄悄打量了下眼前人。她的围巾已经摘下来了,脖颈白皙细嫩的刺眼,只是帽檐压得太低了,看不清全貌,但他直觉,对方应是极好看的。
“偷偷摸摸有什么意思,大大方方看就是了啊!”她仰头咽下一口水,将帽檐转到了脑后,“我又不收你钱!”
调酒师吞咽了下口水,怀疑自己是酒香醉人,不然为什么会觉得对方笑得像个会喝人血的妖精呢!
江初阳的唇角再次翘起,但稍后又将那上翘的弧度压了下去,她想着自己这天凌晨笑的次数是太多了,不然为什么会觉得嘴角有股不自在的僵硬呢?
她深一下浅一下地轻啄着杯中的水,直到它几乎凉透。
“再来……”
“妹妹,一起喝个酒呗!”
江初阳的眉梢都挑了起来,侧头看去。
妹妹?
有意思!
她晃了晃见底的白水,手指都带了几分轻快的欢愉。
“咚!”她将玻璃杯放回了桌面,笑眯眯的,“好说好说!”
“哈哈爽快人!”男人笑得猖狂又粗俗,“给这位妹妹来一……”
“别急啊!”那人未说完的话被江初阳给打断了。她抬了抬下巴,将视线放到了调酒师的身后,素手纤纤一指,“就那个酒,再拿一个杯子过来!”
调酒师对这个面容姣好又调侃过自己的美女印象挺好的,他看着她手指下的目标,对她微微摇了摇头——不合适。
江初阳笑笑,俏皮地眨了眨眼,以示无妨。
调酒师无法,只得把东西递了过去。
江初阳侧了侧身子,正面对着这个在她眼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猥琐的男人:“想搭讪,总得拿出点诚意来不是?”
“想要什么诚意?”男人顺势靠近了些,满脸都写着“不怀好意”几个字。
“这瓶酒……”江初阳早在他往前凑之前就闪到一边去了,心中很是不爽,这油腻腻的,用来做菜?“你付钱,你喝——干净,如何?”
男人也不是个外行:“格兰菲迪26年,700ml装,你消遣我?”
江初阳低头笑笑没说话,只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桌面,示意调酒小哥先把温水给她续上,这才似笑非笑不紧不慢地答了句:“才发现呀!”
“砰!”男人好似这才回忆起她自始至终嘴角的嘲意,不甘而愤怒地将自己的酒杯砸在了桌子上,“敬酒不吃吃罚酒!”
江初阳整个人都趴伏在桌面上,一副笑得要直不起腰欠揍模样,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脸蛋、耳朵甚至微微露出一点的脖颈,很明显是肾上腺素分泌得多了:“我这人可是不喜吃酒的!”
男人突然向江初阳逼近伸手,也不知这一动作究竟是为揍人还是揩油——
“你们拾色,什么时候竟然缺了看家的?!”
江初阳虽不是个正经练家子,但收拾普通流氓还是绰绰有余的。就在对方心怀不轨出手之时,她就趁其不备将其胳膊扭到了身后。身法挺快下手狠辣,不同于那嗷嗷求饶声及骂骂咧咧声的嚎叫,她的声音低低柔柔的,语气里却是带了点漫不经心的质问。
调酒师从头到脚哆嗦了下,尚未开口,就见对方转过了头,似乎是并不在意答案如何。
被钳制的人疼到不行,最初的不服气已经消失不见,就剩些“有眼无珠”“再也不敢”“饶了他吧”……
“嗤!”江初阳将人推了出去,“没意思!”
得了自由,那人连句狠话也没放,只留了个恶意的眼神就踉跄着跑掉了。
调酒师又重新开始擦手上的高脚杯,慢慢压下了心底的好奇,随意地问了句:“您不怕那人报复啊?”
江初阳扬扬眉,拿起围巾套在脖子上,将帽檐重新转回:“不会的。”那人一看就是不是个硬气的。
“保安不是故意不出手的——”调酒师本想解释,一时间却没能找出合适的措辞。
“懂!”江初阳又拿起杯子最后轻抿了一口水,“小打小闹不需要,是吧?”
“……”美女这么明白还问个什么劲儿?
已经往外走的人不知想到了什么竟又反身折了回来。
江初阳拿起了那杯Mojito,在调酒师眼前轻轻旋转了一下,又重新放回原位。对方不明所以。
“薄荷叶太多,冰太碎。”
“……”
“太丑!”
“……”
“所以您才一口不动吗?”年轻的调酒师在最后一刻道出了自己的疑问。
江初阳低了低头,似笑非笑:“不,我只是不喝酒。”
调酒师一愣过后,却见对方已经大步离开了。他摩挲着手上的用具,深感对方的所思所想着实无法参透。
夜风静静,江初阳不知道,其他人更不知道,刚刚搭讪的男人确实还贼心不死想着扳回一局来着,只是看见她开的车后,思忖一番后便偃旗息鼓了——
那拉风的车牌号,可不是简单人物能用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