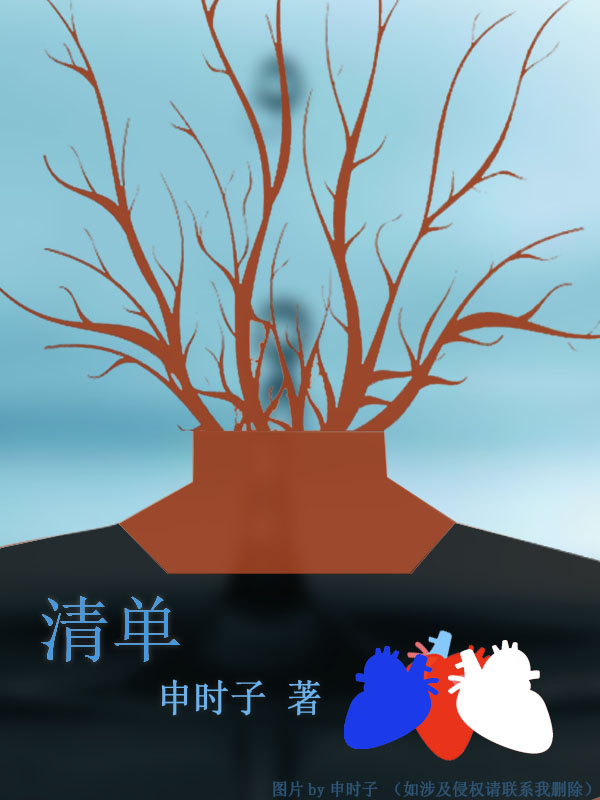对于危险气息的感觉,我向来没出过差错。这次也不例外。我相信那既是一种天赋,更与当年在荒原上的生存环境有关。
我成年之前一个人在荒原上晃荡,基本没遭遇过生命危险,比如摔伤,中毒,蛇咬或猛兽袭击,全都没有进入过我的记忆。起初我以为是种幸运,后来才渐渐发现,我似乎生来就具备一种避险本能。自从落地学走路开始,凭着一种奇异的感觉指引,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绕过或避开野地里大大小小的危险。
少年时代我还没接触过人群,记忆空间里储存最多的东西,是气息,各种各样的气息。我说的这种“气息”,并不仅仅限于鼻子闻到、或耳朵听到的异样,甚至也不局限于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我指的是一种综合感觉。直到现在,我仍然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表达这种理性之外的东西,只能笼统地通称为“气息”。
比如,一片死寂的草丛,忽然有其中一片叶子或一根杂草无端晃动,不管是耳朵听到还是眼睛看到,那就是一种异样气息,你立马就得知道此处可能有毒蛇滑过,或者有某种毒虫埋伏。不需要更多的判断,在气息的冲击或指引下,远远地绕过那一片地带。
后来随着年龄见长,我的天赋锤炼得更为敏锐。那时娘已死去多年。我每天面对最多的是恶狼,却从来没有给它们袭击我的机会。因为我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逃生或反击的最佳场所。这个过程,我并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或评估。大多数时候,甚至在恶狼尚未出现攻击的苗头或念想之前,我便已经抢先一步掌握了主动地位。至少在地形的选择上天衣无缝,从来没出过差错,否则便活不到今天。
所以,许多年下来,群狼与我在荒原上和平共处,并非它们对我特别仁慈,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事实上,它们应该也从我身上感觉到更为危险的气息。它们也有这种本能。而且并不比我差。许多年里,我们双方靠着本能保护,有意无意地避开对方。
后来我与群狼发生了惟一的一次冲突,立即使自己踏入死亡陷阱,那并非我的天赋消褪,或感觉出了问题,而是在饥饿的折磨之下孤注一掷。当然了,那一次我没死,就真的纯属幸运,关键时刻,诸葛神甫出现了。他救了我并成为我的师父。而这次与群狼的冲突,也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整整持续了两年,直到师父在那座山顶上被群狼啃得血肉模糊。
我随后被群狼推下悬崖,又一次没死,仍然是幸运。那已经是我生命里第二次幸运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三次。
假如我的生命里存在第三次幸运,是否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刻?
因为这一刻,任谁看来我们都是必死无疑。
我得说,在今天,虽然我对这一刻危险的气息有所感觉,但一直模糊不清,更无法采取相应的行动,很明显是因为那种感觉比以前迟钝了许多。不知是受伤在先,以致感觉麻木呢,还是与人群接触多了,当初的天赋慢慢在退化。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我一路上惴惴不安,极尽抬扛之能事,最终还是跟着归无情与李开心走进了一个死亡圈套。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无法像当初荒原上一样,迅速准确地避开即将到来的风险。
火光在我身后五十步左右猛然点亮。我们三个在火光中本能地转过头,但来不及转身,所谓“头转身不转,狼顾之相”,但我们此时的反应比狼差远了,仅仅保持着“狼顾”样子而发怔,也可以说是犯傻。
火光来得太过突然。也太过强烈。
当然我们的发怔并未持续太久,否则在第一回合便已全部死亡。
让我们立即死亡,这应该是对方的目的。这显然是个蓄谋已久、计算精准的圈套:先在离悬崖边五十多步的地方,铺上引火之物。旁边埋伏弓箭手,全部引箭在弦。一旦我们就位,先点火导致我们视觉错乱,与此同时,弓箭齐发。在我们于火光中尚未反应之机,全部中箭倒地。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点火,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
听起来黑暗中放冷箭更具杀伤力,实际上那只是针对一般江湖庸手。而暗算像李开心这一流的人物,黑夜放箭并非最优办法。因为冷箭无论有多快多强,在寂静的黑暗中还是会有破空之声。大批量的弓箭同时射出,更是相当于一阵狂风扑面而来。所有的绝顶高手,比如李开心,甚或归无情,对于空气中细微震动的感觉,都有异于常人的敏锐。虽然行走于黑暗中,但此时内心的防卫意识却最为澄明,一旦感觉到了风声,凭他们的修为,就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躲避措施。
如此一来,只要第一轮攻击失败,想要再进行第二轮,恐怕连弓箭手都找到不对手的位置。
而在放箭之前先放火,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火光由远及近传播的速度最快,人眼最先受到刺激,那会在瞬间将原本敏锐的其它感觉击得粉碎,于是,无论多么顶尖的高手,也会在那一刻忽略、或者压根就感觉不到弓箭的破空之声。等他反应过来,全身已被强弩穿透了。躲避早已成了虚话。
这个攻击圈套,是专门针对我们三个精心设计的。设计者是梦遗大师,或者是无厘道长。更有可能是两人互相商讨、取长补短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两人无论武功还是心思,都让人感到害怕。
我对于危险气息的感觉,根本上是源于对梦遗大师和无厘道长的恐惧。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周围的一切太寂静了,寂静有时是凶险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我被李开心扔进屋内之后,双方就开始在黑暗中对弈一盘生死残局。
归无情一现身,梦遗和无厘就会想到,肯定有一条不为人知的暗道,然后一定会找到悬崖边。他们没有割断绳子,是故意留一个缺口让我们逃生。这点我们想到了,我们还想到了他们召来南宫玄是为了截断我们的前路。而他们抄我们的后路。
我们的应对之法是将计就计,决定走一步险棋。
很不幸,对方第一步棋——召南宫玄为后援,只是个假象。于是,我方连一步将计就计的险棋都没法落子。
归无情黑暗中一去一回,很可能根本没逃过少林&武当的耳目。他们伏兵不动,是因为杀掉归无情轻而易举,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我和李开心产生决绝的意志,死守黑屋子,他们要攻进来,必须牺牲大部分的徒众。他们不愿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一句话,他们是故意让归无情回来向我报信,故意让我得知,南宫玄正从那条暗道赶来消灭我。
然后,无论是梦遗大师,还是无厘道长,都能猜到,我们三人会有一番商讨。他们也可以猜到,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冒险攀下悬崖,割断树藤崖孤注一掷。于是,他们提前想好了一步棋,在悬崖上等着我们。这是一步针对我们三个高手的绝杀棋。点火的同时又射箭。谁都逃不掉。悬崖必然成为我们的葬身之地。
一切都按照梦遗大师和无厘道长的计划发展。我们顺利地钻进了他们的圈套中。只不过结果稍稍有点不同。这点不同是因为我的感觉引发的。
我们第一回合并没有死。得益于我那残留的一点点对于危险气息的感觉。
首先,那股不安的感觉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虽然在火光突起的前一刻,我依旧没搞清那股不安源自何处。其次,归无情与李开心当时都在黑暗中面对悬崖,惟独我是侧身站在崖边,而且位处他们两人中间,离李开心一步,距归无情两步。
情况就是,火光一起,我因为侧着身子,左眼角最先受到刺激,换句话说,我比他们更早看到了火光。至少是,我少了一个完整转头的动作。我只需转半圈,而他们两个必须转一圈。虽然这个先后时间差极其短暂,但因为心中的不安感一直存在,所以,在这一瞬间,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我。
严格来说,我并没有发怔。火光只不过是让我眨了一下眼。
再次睁开眼皮时,我身形暴起,抬脚踹在李开心腰间。将其踹倒在草丛里,借此一踹的反弹之力,我上半身撞向归无情的肩膀。两人同时跌落在树干底下。
第一排强弩就这样从我头皮上擦过。一部分钉在树干上,更多的射进了悬崖下面无边的黑暗中。
火光更亮了。真正的天地通透,其实就是发生在第一排强弩过后。
悬崖上杂草不深,而且只有一棵长在崖边石头缝里的大树,因此火光通天之后,我们三人根本无处藏身。
然而对方并没有冲过来。
依现在惊魂未定的形势,梦遗大师和无厘道长再带几个弟子,与我们三短兵相接,击败、乃至杀掉我们的可能性较大,最不济也可以将我们逼下悬崖。但他们没这么做。要么就是他们对第一排弓箭的成功信心太大,没有准备好下一着;要么就是,他们仍然成竹在胸,不愿冒一点点风险。毕竟近身肉搏,很难保证他们自己不受损伤。
我相信是后者。一击不成,他们不太可能没有后手。那不符合梦遗大师的智商,也不像是无厘道长的风格。
没听到人声,火光之外也没见到人影。第二波弩箭适时而来。
第二波弩箭的凶险程度,远远比不上第一波,原因是我们眼睛已经适应了火光,而且都有了心理准备。这多少给了我们三个一点点喘息的机会。我与归无情滚到了树干之后,当然了,树干不够粗,遮挡不住我们两人,充其量只能各自隐藏三分之一的身子;李开心也身子一翻,将头部埋在一块石头之后。
第二波弩箭呼啸而过。我们都没受伤,但也无法动弹。因为第三波和第四波弩箭接踵而来。在对方弓箭完全消耗之前,还会有无数波攻击。我们只能依靠身体闪避或长剑格挡,难免不出意外,一旦意外发生,哪怕再微小,要么丧命,要么重伤,要么就是摔下悬崖成为肉饼。
对我们而言,这不是长久之计。无论多么消极的抵抗或闪避,也都要耗费体力。而体力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宝贵的东西,尤其是我。我白天受伤昏迷,醒过来之后体力原本就只恢复六七成,随便再消磨一段时间,最先支持不住的肯定是我。
刚才走出屋子时,我拿了柄长剑在手。现在右手稍用力挥剑,格档了几枝箭之后,背上的伤口又开始火辣辣生痛。胳膊也越来越不灵便。重伤之下,不但体力消失得更快,精力也更容易崩溃。
火光中,树干上归无情不知什么时候系的那个树藤还在,就像一条巨大的蟒蛇,弯弯曲曲地伸向黑不见底的深渊。如果说我们还能逃生,这根如蛇般的树藤,大概就是我们惟一的活路。这是一条艰难而希望渺小之路,尤如一个垂死的老人,气若游丝。
假如让归无情和李开心抵挡少林&武当的人,我凭借残存的体力,抓着树藤往下攀援,或许能活着到达崖底。但归无情和李开心很可能就会丧命于崖上,这种事我干不出来,况且万一有一枝箭恰巧射中树干上的藤结,我同样会掉下悬崖摔成肉饼。另外,即便安全到崖底,凭我一个人,也万万对付不了前头截路的南宫玄。
梦遗老秃驴和无厘牛鼻子老道,一定早就想到,我们凭借这条树藤逃生的可能性,他们或许正在某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三个一起攀下悬崖,他们随便派个武功低劣的弟子,冲过来在树藤上砍一刀,我们立马烟消云散。
假如我们中一个或两个攀下去,他们也只需加紧攻势,估计上面两个早已身亡,下面那位还没到崖底。而且,前头还有南宫玄处理后事。
总之,我们三人一起沿着树藤逃生的可能性不存在,一人或两人逃生的可能性则很小。
又一波箭雨像飞蝗般掠过,我右手忍痛再挥剑,惊险避过。然后我转头很没出息地朝归无情问道:
“现在怎么办?有没有别的路?”
归无情这次答得简单干脆:“没别的路了。”
不远处的李开心低声喊道:“王兄弟你先下去。”
我也回答得很干脆:“不行。我不下去。”
我一个人下去没用,只不过死得更晚一些而已。李开心和归无情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一问一答之后,没人再说话。
形势很明显,我们三个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射死在崖上,要么摔死在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