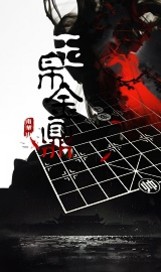我蓦然吓了一跳,转身看到归无情依旧面对墙壁而立,连动都没动一下。他双手抱肩,背影看起来既冷漠又单薄,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也许是我的错觉,他的话语里还有一股悲伤气息。既然想到了脱困的办法,说出口却如此的不自信,听起来就像马上要去赴死一样悲凉。这家伙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与李开心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什么办法?”
归无情这时才缓缓转身,还是那张死鱼脸,一点表情都没有,不知道他是喜是悲,仿佛刚才说话的人压根就不是他。这有点不正常,我感觉他在强装冷酷与镇定。因为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恰好面对着火光,我看到他眼角闪着浅浅的潮湿意味。那表明他在面对墙壁沉默的时间里,作了一个什么决定,而且此前还有过悲伤的挣扎。
也许是,他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道的往事?可是,有什么往事值得这个如此冷酷的家伙眼眶潮湿,而且还是目前这个场合?
管他呢,且听听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归无情答:“将计就计。”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话过于简洁,或者故意只说一小部分,其它大部分要靠猜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最沉不住气。这次也一样。特别是说话的人,恰好又是我比较讨厌的归无情,我更无法忍受他的故作高深。
我厌烦道:“把话说清楚一点。你知不知道,关键时候装酷,容易招人烦。”
归无情的回答仍然很简短:“我们三人仍然从悬崖攀着藤条下去,在崖下截住南宫玄及其手下。”
我一时大怒:“这就是你的办法?他带人来截我们,我们也迎头去截他。那他妈的不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是不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
李开心比我冷静多了,嘴上不说话,还伸手示意让我别打岔。
归无情:“我们先理一理少林&武当的具体计划。他们留着悬崖边的缺口,是有意让我们从那里逃生。如果我们中计,前面会被南宫玄截住,后面少林&武当跟着从悬崖攀下来,抄我们的后路。两方前后夹击,我们三人便有死无生。”
我还是没管住嘴:“这不是废话吗?”
归无情:“据我估计,南宫玄及其手下,还有半柱香的时间才能到达崖下。我们现在立即出发,攀下悬崖后,再把藤条割断,先去除后顾之忧,然后迎头将南宫玄杀个措手不及,或许有点胜算。”
我问:“即便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三个对付南宫玄及其手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实际上,那七个剑客是我师父调教出来的,摆成一个剑阵,足以困住我们三人。况且,少林&武当的人还可以绕路增援。”
归无情:“我几天前就堪察过了,此处要绕路到达崖下与南宫玄会合,至少一个半时辰的脚程,那时接近天亮,而我们与南宫玄,早就胜负已分,甚至还休息了足够长的时间,完全有精力调头应付他们,或者逃离战场。”
我不罢休:“你还没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制住、或者战胜南宫玄及其手下。”
归无情:“首先,这一次铁了心要你命的,是少林&武当的人。……”
我打断他的话:“等等,少林&武当要杀的是我们三个人,不仅仅是我一个。”
归无情:“无论如何,南宫玄此行的目的,与少林&武当不一样,并非刻意要我们的命,而是别有所图。”
我若有所悟,仍然顺嘴问道:“他图什么?”
归无情:“你自己曾经说过,南宫玄这次搞出如此大的江湖风波,却又放弃向少林方丈复仇,是因为他想要得到的是财富和权力。所以,他此行所图的东西,在你身上,具体一点,在你的包裹里。”
我沉吟:“你的意思是,他想要我包裹里的聚鹰帮军队令牌?可他拿到了也毫无用处。”
归无情:“军队令牌必须与帮主信物合用才有效果,这是聚鹰帮内部的机密,他南宫玄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在追逐这个东西。”
我冷静下来说:“南宫玄目前应该还不知道令牌在我身上。此事整个江湖也没几个人知道。”
这回接话的是李开心。我与归无情争辩,他在旁边观望良久。
李开心:“南宫玄知道令牌在你身上。要知道,白天你当着众人之面,不但给了归无情两块令牌,还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这一次少林&武当向南宫玄报信,一定会刻意提起令牌之事。因为他们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各取所需:南宫玄要聚鹰帮的财富和权力,而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保住江湖名声。南宫玄若不是得知令牌在你身上,他是不会甘心接受少林&武当差遣的。所以,归无情说得对,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杀我们,而是要你身上的东西。”
我转向归无情:“知道了他的主要目的,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战胜他。更不能说我们可以借此脱身。他没有得偿所愿,想杀我们之心,估计比少林&武当更强烈。”
归无情:“他既有所图,我们就如他所愿。让他得意忘形之际忽略我们的性命。”
我冷笑:“南宫玄不是一般人,怎么可能得意忘形?你太小看他了。”
归无情:“只要他稍稍放松警惕,我们就有机会。”
我说:“要他放松警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
归无情:“南宫玄知道我是诸神教的卧底,但并不清楚我在诸神教内部是什么身份,更不清楚我与你师父诸葛神甫有什么关系。一会我们攀下悬崖后,分头行动,找个杂草丛生的地段,你们两人趁黑夜伏于路边,我带着所有的令牌等南宫玄。他到达之后,我立即出示令牌,并且毫无保留地送给他。”
我说:“我们三人趁他查看令牌的时机袭击他?如果他不让你靠近、只叫手下来传递东西呢?而且,以他的身份和个性,很大可能这么做。他不可能对你一点都不提防。”
归无情:“见机行事。若此刻的袭击机会没有出现,或者一闪即逝,他一定会问我意欲何为。我可以说是专门来投奔他,偷来的令牌,就是晋见之礼,以此换取教内一个比较高的身份。此话对他而言可信度较高,因为聚鹰帮上官飞鹰已死,而诸神教的诸葛神甫消失已久,我实际上无处可去。如果他相信我的话,我可以进一步劝告他,既然拿到令牌,此行的目的已达成,那么,就没必要帮助少林&武当将你们两人消灭,毕竟此举要损伤不少人命。让少林&武当独自处理此事,诸神教作壁上观,就算要加入战团,也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省时省力又收效明显。”
我还是冷笑:“你觉得,整个废话的过程,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制住他?”
归无情:“即便他完全不信任我,但令牌是真的,他肯定会犹疑不决。也许他全程严防我突袭他,但绝对想不到你们两个就埋伏在路边。以李大侠的武功,整个过程中,要找个空隙袭击甚至制住他,并不太难。帮主你虽然有伤在身,但武力应该也恢复了好几成,从旁相助,此举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大概是我自从见到归无情以来,他说话最多的一次。话语逻辑不够简洁严密,条理也不是算太清晰,但对于自己观点的表达,称得上巨细无遗,面面俱到。而且为了说服我,有问必答、不厌其烦的精神,与他平常的个性大相径庭。
但是,我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或者哪里不太对劲。我刚要再次找理由反驳,李开心及时插话打断了我。
李开心:“归无情的计划不算太严密,但应该可行。”
归无情:“现在差不多已过子时,而且天空阴云密布,如墨之夜是我们悄悄溜走的最好掩护,赶紧出发吧。”
李开心:“我们没更多时间把计划讨论得密不透风。否则失去的机会更多。”
归无情拿起墙上的火把,率先往门外走。我脚步犹豫地跟在他五步之后,李开心紧跟着我,离我只两步之遥。走出地下室,归无情回头看着我们,下巴点了点,手在空中猛然一甩,火把立时熄灭,眼前伸手不见五指。
我心中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呼吸似乎有点不顺畅,必须张大嘴巴配合鼻子一同往胸腔吸进空气。我努力控制喘气声,希望不要让他们听出,我王大侠在黑暗中是如此的没出息。但我抑制不住心跳越来越快。简直就要蹦出胸膛。
我一边凭感觉往前走,一边嘀咕:归无情真的值得信任吗?把一个出了差错可能丧命的计划,完全交给此人,是不是有点太轻率了?说起来,我王大侠既是诸神教教主,又是聚鹰帮帮主,可现在说话作主的,却是前面黑暗中那位底细不明的人。
还有后面的李开心,他似乎更没什么理由轻信归无情。但他没提一句反对之语。他是故意装傻呢,还是真认为归无情的计划切实可行?看上去装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感觉,李开心有一种强烈的想见到南宫玄的欲望。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南宫玄的内心,埋藏着当年李开心师父之死的真相。
风险太大。很可能大到我无法想象。这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脚步走出屋子,我心中这股阴影越来越浓,差不多跟身外的夜色一样黑暗无比。
我没有别的选择。
天空仍然没有一丝星光。我们就像掉进一个墨水桶里,黑水浓淡不一,使得我们眼前只有深浅不同的黑色。
归无情选择的路,其实原本不是路。那是屋后的一片荒僻之地,杂草丛生,时或高过头顶,藏身其中不言不动,谁也不会发现。但若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会吃饱了撑得躲在这么个不是人呆的地方,蚊子和苍蝇多如沙子,叫声一刻不停,在身边各个方向环绕,假如眼睛能明察秋毫,估计还能见到更多乱七八糟的虫子。
另外,地上不知有没有毒蛇。这个季节它们还没有进入冬眠。要是不小心踩中一条,只能躲在野草丛中等死。
计划凶险,走的路也凶险。所幸的是,少林&武当真的没在此处设置耳目或障碍,当然,根据我们之前的猜测,他们是故意留下这么一个缺口让我们溜走。更幸运的是,一路上并没有踩中毒蛇,连无毒的变色龙都没碰上一条。只有苍蝇的搔扰,搞得我更加心烦意乱,而蚊子将我暴露在外的皮肤啃了个遍,还有几只可恶的蚊子钻进了我的鼻子,吸进了胸腔里。
我恶心欲吐。想大力将蚊子咳出来,又硬生生忍住了。声音太大,很可能惊醒少林&武当的人,即便他们不敢冲过来,远远地射一轮弓箭,也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悬崖边。
我并非凭视觉知道已到达悬崖边,而是听到前面归无情的脚步已经停了下来。他似乎还转了个身。我与李开心也立即止住脚步。
我感觉三人应该是站在一棵大树下。只因此处的夜色更浓。除了站在树荫下面,没别的更好的解释。
我此时灵光一现,蓦然想到了刚才一直隐约觉得不切实际的疑问。
我转身向李开心低声说:“计划第一步就行不通。”
李开心立即低声问:“怎么行不通?”
我继续压低嗓门说:“我们三人一起下去,谁在上面割断树藤,阻止少林&武当的人抄我们后路?如果留一个人在上面处理树藤,他随后又怎么下去?岂不是会被随后赶来的少林&武当高手剁成肉泥?即便这人愿意献身,随后崖下的计划,两人也没法很好地执行啊。”
这是个无解难题。李开心没有答话。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眼神看向什么地方。凭声响知道,他不言不动,没什么激烈的反应。难道他胸有成竹?
胸有成竹的不是李开心,而是归无情。我话暗刚落不久,归无情像个幽灵似的,在我左侧两步处接口说话了。他同样压低了声音。
归无情:“你们两个先下去,我在上面割断树藤,随后下来。”
我冷笑:“割断树藤了你还怎么下去?像鸟一样飞下去?下面离实地少说也有几十丈,把你摔成肉饼算是轻的。”
归无情:“我白天来去过几回,悬崖的很多细节位置比较清楚。”
我还是冷笑:“那又如何?细节再清楚,也改变不了你不会飞翔的事实。”
归无情:“你们下去后,会发现两边各有一棵树。一会我将树藤割断,你们两人捡起树藤各执一端,爬上树梢,抓紧、拉直。我从崖壁上滑下来,中间有几处突出的岩角,可以帮助缓冲下跌之势,如果我运气好,最终可以凭感觉摔在你们两个拉直的树藤上。依靠树藤的弹力再次缓冲,可能会受点轻伤,但性命没有大碍。”
我叹道:“既要靠运气,还得凭感觉。你这个计划也太不靠谱了。”
归无情:“帮主不必太过担心,我说过自己攀援的本事,比常人强一点。”
我心想,我才不担心你这个死鱼脸会摔成什么样子,我是怕计划中途流产,一旦下去就没有退路,到时被人瓮中捉鳖,黑暗中死得糊里糊涂,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下辈子还是个孤魂野鬼。
此时李开心接口道:“王兄弟,对他投入点信心吧。再说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赌一把,一味抬扛于事无补。无论什么完美的计划,都有赌博的成份。”
我不再说话,但内心那种不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归无情走近树干,双手摸索不定,大概在寻找他口中提到过的树藤。但他的手尚未停止动作,蓦然间天地通透明亮,照得我们三个人纤毫毕现。
饶是我们三人历险无数,一时之间也不知怎么反应,全部怔在当场。
与此同时,一轮箭雨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