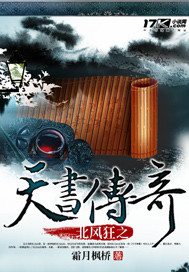芥展的回书到了北境,时近黄昏,北境在下雪。
厚王仁玑在寝殿用晚饭,跟随他近百年的老奴默山有些拿不准,该不该把回书送上去。他接过姜黄织布包裹的书信,封口处压了火漆,钤着西镜的徽饰,生了翅膀的虎。
织布冻得梆硬,带着户外的寒气。默山往珠帘里望了望,厚王坐在方桌前,看上去情绪平静。珠帘用的是东境贡入的珍珠,柔白圆硕,这道门足有寻常门户四扇大,银针松华光耀映下,绵长的珠帘很华丽。
默山收了回书,挥手叫递信的奴人退下。他在坏了厚王的信致,与耽误部落的大事之间选择良久,还是整了整衣冠,悄悄揭帘入室。
珠帘沥沥轻响,厚王也许知道是他进来,仍坐着不动。他的侧脸流畅而俊美,墨黑的头发利落束成顶髻,黑色深衣编进南境贡入的朱枳线,微微一动,便有隐隐红光。
方桌上架着红泥小炉,小山熬炖肉汤捞饭的泥炉,跳跃的火苗拱着只淡紫陶盆,袅袅水汽伴着鲜香扑鼻充盈于室。
除了泥炉陶盆,桌上的碗箸盘碟都是银制,是西境品色最好的软银。器具讲究,边沿压着一圈花纹,并非花卉,仿佛是仙人驾着鹤鸟高车,伴了祥云遨游。
默山走到桌前,娶银壶往银杯里兑了蜜酪,又悄然搁好。厚王理了理袍袖,伸出两根手指捏住银杯。他的手指节修长,风骨清俊,肤如凝脂,保养的极好。
“南境的珍珠米吃完了吗?”厚王饮一口蜜酪,搁了杯问。默山恭敬道:“最后一斛昨日已用尽了。”厚王嗯一声,娶绢帕抹了抹嘴,便听银铃轻响,有小娘子送上银盆,盛着温度适宜的水。
厚王探尽指尖,像是试试水温,接着浸了手掌,旋即提裳出水,指尖轻弹。另有小娘子送上绢帕,厚王皱眉道:“说了绢帕磨手,要用棉帕!”
小娘子吓得一抖,通得跪了下去。默山小声道:“此事是老奴的错!织品库里的棉帕都不干净了……”厚王冷冷一笑:“姬芥展总不会这样小气,棉布也不肯送了?”
默山喃喃无言,斗胆摸出袖中藏着的西境回书,高举过顶,跪下道:“王上,这是刚刚加急递到的。”厚王瞧了眼文书,道:“打开。”
默山道:“是。”他撕去火漆,展开书信,匆匆一览,抬眼看了看厚王。这微小动作没逃过仁玑的眼睛,自从默山拿出书信,他的神经已经崩紧了,只是不想表露出来。
“说的不中听吗?”仁玑问。默山低声道:“用词很讲究。”仁玑道:“芥展向来讲究用心。他最讲究的地方,是诸事都是别人想做的,他永远置身事外。”
他笑一笑问:“这次总不能又用她作借口。”默山道:“这次却是换了借口。”仁玑一时好奇:“换了借口?他还能有什么借口。”默山道:“西境的姬女芳冉。”仁玑只有一刹的迷惑,瞬时便懂得了,他忍不住滑稽,哈哈笑了出来。
“有趣,有趣,”他笑着起身:“想不到淳齐如此有福,南境认定了他,西境也动了心思。”他笑而起身,越想越是好笑,又问:“南境的奚止怎么办?”默山道:“回书里只说,大殿下与芳冉在东境共经生死,暗生情愫,大殿下开的口,求裕王应允,许他纳芳冉为正妃。”
仁玑的笑容冻在脸上,仍是春风满脸,静了静方说:“他纳谁做正妃,总要我点头。难道眼下规矩变了,王子纳妃不必部落王允准了?”默山不敢多话,只说:“是。”
仁玑指回书道:“说说重点。”默山道:“裕王说大殿下另有隐情,请北境召集星主会盟。”仁玑冷哼一声,哗得一撩珠帘,转身出去了。
珠帘便似迸碎的光,咻咻闪个不住。默山定了定神,蹑足跟上。
仁玑转过一扇磨得半透明的冰塑屏风,踱进暖阁。里头沿窗堆着诸怀目,各堆相距不过一臂,屋里布着大设,银针松的雪亮夺了诸怀赤红,地上铺着孔雀绿的织毯,色泽鲜翠又沉静,像一汪碧绿的湖。
仁玑立在冰塑的书柜前,仰望良久,伸手取下书匣,取一卷展开,扫了两眼,捧着缓缓回身,坐进铺了雪狼王皮的榻椅里,屈膝半倚在暗金织花软枕上。他注目书卷,并不理默山,翻了良久,合了顺手一丢,道:“王后在做什么?”
默山道:“老奴不知,这就去安排打听。”他转身要走,仁玑却唤住了,道:“我去看看。”默山微惊,却问:“可要通报了再去?”仁玑道:“不必!”说罢了就走。
北境的王殿是真正的水晶宫。亭台楼阁皆冰砌,七座主殿间有冰棚相连。仁玑出了主殿,触目飞雪漫天,雪片只落在冰棚上,却沾不得身。
他立在冰棚之上,放眼瞧了瞧琉璃世界。说实话这风景太单调了,这座水晶王宫住的也闷气。他此时不知为什么,忽然想一个不愿想起的人,淳齐的母亲芥菱。芥菱从南境回来,兴奋得像她带回来的金丝鸟儿,备述南境种种,听来风光如画,仁玑嘴上不说,心中很是向往。
他有时候想,他的命不大好,不该生在北境,该生在南境,只是这话他从不说罢了。芥菱事发之前,他的所有辛苦都为了有一天,他能随心所欲的行止四境,冷极了就去东境,热得无聊便能回来,萧凉了自南境的繁华等着,若是浮华扰心,仁玑设想着,唇边浮出一抹笑意,他并不介意大漠西风,让他也换个新鲜心境。
芥菱毁了他的随心所欲。
他厌弃着看一眼飞雪下粉妆玉琢的世界,迈步向萤几寝殿走去。
也许没料着他要来,萤几的寝殿黑乌乌的。王妃侧妃乃至有位份的妾从,供应银针松都有份例,因而萤几早早收拾了光亮,只留着下榻处的两处大设。黑暗里,值夜的奴人袖手躬身立着,低头缩颈像在瞌睡。
仁玑到了近前,默山微咳一声,奴人猛然惊觉,通得跪下,抖了身子却说不出话。自从淳于出生,厚王进这殿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了王子,王上宿在王后殿中的时日不再苛刻,厚王自有说辞,只推公事繁忙。
默山问:“王后歇了吗?”奴人抖了声音道:“还,还不曾。”默山道:“还跪在这里做什么,速速去禀报了!”仁玑却和悦道:“不必,我进去就是了。”他往里走,边走边向默山道:“当值时睡觉当个什么罪?”默山只得说:“削去双耳,放出浮玉关,永世不得入关。”
仁玑点头道:“照办罢。”他这话说毕,奴人哇得哭出来,叫道:“王上饶一饶小的,小的并没有睡觉,实在是太冷,因而低了低头!”仁玑便似听不见,直往里去了。奴人的惨叫声配着飞雪,映着琉璃宫殿,更显得北境冰冷。
也许奴人的哭叫惊动了萤几,里头慌张着迎出女奴,提着冰刻琉璃灯,又有小娘子急步而出,跪拜道:“见过王上。”仁玑便似看不见,跨过她身畔直走过去,萤几已忙忙迎了出来。
她要行礼,他摆手道:“不必了。”萤几听了,跪下去的身子又拔了起来,他却刻意绕过她,走去榻前坐好。
这里比起他的正殿,仿佛两个世界。此处认真是个雪屋,除了一张榻几,和两只搁在地上的大设,别无长物。
仁玑多待,开门见山笑道:“今天淳于没进来吗?”萤几便道:“天黑前来过,坐了坐就走了。”仁玑想了想说:“眼看着也到了婚娶的时候,你这个做母亲的,就没替他谋划谋划。”萤几恭敬道:“此事但凭王上做主。”
仁玑失笑道:“由我做主?这话听来让我感动,眼下不必我做主的事多的很。”萤几听他这样说,摸不准出了什么事,也不敢看默山,只低头不言语。
仁玑瞧她不接话,长吁一口气道:“既是叫我做主,那么我看着,菁莲很好。”萤几仿佛吃惊,抬头看他道:“菁莲?”仁玑笑道:“怎么啦,菁莲究竟是西境王女,难道你嫌弃吗?”
萤几忙道:“不,不是嫌弃,只是,只是……”她嗫嚅不出,仁玑笑道:“难道你认定了南境的奚止,别的都看不入眼?”萤几道:“王上,南境的奚止定给了淳齐,我和淳于都不存此心。只是菁莲,菁莲……”
仁玑蹙眉道:“她有哪样不好,你说来听听罢。”萤几道:“别的都罢了。东境的事是我亲身经历,淳齐里外奔走,身冒奇险救了我母子出来,无论是特意还是顺带,总也算是救了菁莲。可菁莲到了北境,言谈间却是颠倒黑白……”
仁玑微微抬掌,打断她说下去,挂了笑道:“你被关在夜牢里,淳齐为何与泯尘约定,为何上了且留岛,这些事你并不清楚。”萤几语塞,默然不语。仁玑道:“反是菁莲陪了纯王上流波岛,亲眼见着淳齐跳上鲸船,跟着泯尘回了且留岛。她也说的清楚,若非当时她与淳齐锁在一桩石柱上,陵鱼是不会救她的。”
萤几舔了舔唇,仁玑道:“我只问你,淳齐用什么事与泯尘约定,能换了纯王上流波岛一见?”萤几无话可说,看了看坐在榻上的人,若是不知情的,见他与淳齐站在一处,只当是兄弟,再料不到是父子。
她眼前一花,想到涤尘馆里肃立阶下的淳齐。淳齐虽是丰神俊秀,比起他王父,还是少了些俊美倜傥。“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淳齐,”萤几想:“看着眉目模样,淳齐分明是他亲生的。”
仁玑扶膝而起,道:“此事就这么定了。你明日见见菁莲,问问她的想法。她若答允……”他回顾默山:“找个不忙的时辰,带她来见我。”默山道:“是。”
仁玑说罢了就走了,仿佛这屋里藏了怪兽,走的慢了要被吞了。
他一口气穿过冰棚,正殿在望方才缓下步子,回顾默山道:“她殿里的气味真难闻。”默山一惊,却不敢答。仁玑冰冷道:“明日叫工匠进来,把墙上多凿些窗子,叫屋子通通气。”
默山只得答应,伴着他入了寝殿。仁玑直入卧房,有小娘子迎出来替他宽了深衣,换上丝袍,又放下束发。屋里人来人往,各司其职,添香的添香,递水的递水,铺床的铺床,只是无人说话,静得不闻人声。
良久,仁玑依着铺了雪狼皮毛的软榻躺下,叹了叹说:“什么时辰了?”默山道:“ 时未至。”仁玑从榻上坐起,自走到几前坐下,一会儿说:“去催一催,怎么还不来。”默山道:“是。”
默山退下了,仁玑便伏在几前看书。殿里悬着东境贡入的夜明珠,加了银针松助威,亮如白昼。几脚放了只西境新送入的黄铜鼎,喷出的暖香却是南境使君王后亲手调制的白芷清露,雅淡宁神。
他慢慢放了烦恼,渐入书中之境,也不知过了多久,却不妨着眼上覆了片冰凉,却是有人伸手遮了他的眼睛。仁玑一愣,随即微笑,抚着那只冰凉的手,温声说:“今天好兴致。”
含光一笑松手,仁玑却不许他抽开手,握在掌中笑道:“怎么这样凉,诸怀目不够用吗?”含光偎在他身边坐下,也笑道:“并非诸怀目不够,乃是被人气得!”仁玑搓着他的手皱眉笑道:“北境还有谁胆敢气你,且说来我听听。”
含光饮一口他银杯中的蜜酪,瞧着杯子微笑道:“这人莫说是我,你听来也是头痛的。上辅大人芥隐,你惹不惹的起?”
仁玑笑而摇头:“惹不起。但凡沾着个西字的,哪咱们都惹不起。”含光三根手指捏着杯口,冷笑不答。仁玑瞧他偏身坐着,眉目如画,那张棱角分明的薄唇,带了些清疏不屑,华丽羽衣掩着的胸脯微微起伏着。
他拨开含光衣襟,抚着他隐现的锁骨,喃喃道:“芥隐烦着你什么了?”含光盯他:“你不知道吗?”不等仁玑回应,他皱眉笑道:“东境陷于泯尘之手,这消息炸翻并境,人人皆知开战在即。各星骑每日辰时、午时、酉时点卯,严令星骑将军不得回府,厉兵秣马,只等着王上令下,便要挥师东进呢。”
仁玑笑问:“此事与芥隐何干?”含光道:“紧要之时,王上按兵不动,不说别人,连宰洛奕王上也是个不见。这便罢了,以偷调星骑出境为由,落平常、司蒙、泥鸿于冰牢,这可是有的?”
仁玑微笑:“是,是有的。”含光又道:“同一日,明诏下达,墨曜将军索鸾于东境护主有功,赏银绶将军,粮十斗。墨曜骑没于东境者,尽数擢拔甲等护卫,以慰英灵。”他击掌叹道:“如此这般,你想想,芥隐哪里能坐的住。”
仁玑道:“难怪他每日请见,原是坐不住了。”含光嬉笑道:“王上莫要装傻,你不肯见他,他只来烦我,天天必到府中,叫我烦不胜烦。”仁玑笑道:“我不肯见他,找你有什么用?”含光握住了他的手,似笑非笑盯他道:“找我没用吗?”
他攥着他的手,像把他的呼吸也一把攥了,仁玑急促道:“有用的很。你若是烦他,就允他见我罢。”含光摇了摇头,眼里的笑化作了寒光:“王上如此好说话吗,为君者一诺千金,他若拿不出一千个金子,怎能轻易见他?”
仁玑哧得一笑,指了指几上芥展书信,道:“何止一千个金子,西境这次下了狠劲,要用全境来换啦。”含光哦一声,抖展书信看了,未了笑道:“内兄这两字终于用得厌烦,改了岳丈。”
他轻声道:“南境已灭,娶不娶奚止算不得大事。只是这星主会盟嘛……”
他推了仁玑道:“喂,你坐坐好,商量此事要紧啊。”仁玑原本倚在他身上,听了这话懒懒坐正,问:“你可知为何要用个盟字?”含光搁了书信,道:“这有何难处。凡行此会,事必涉部落难决的大事。与会星主入了场,与部落王不再是上下隶属,乃是平起平坐,能直舒胸臆,详发议论。”
仁玑呸一声,笑道:“都是些空话。设这条款,不过叫部落里勤王的一派,与存心自大的一派,有个地方交手罢了。”含光笑一笑:“可惜在北境,向来只有勤王的,并没有胆敢存心自大的。”
仁玑听了这话,又凑上前去,拨开含光的羽衣问:“你热不热。”含光低笑道:“王上,外面下雪呢。”仁玑贴着他的唇,轻声说:“越是飞雪的时光,我越是想念你。”含光笑着向后躲躲,低声道:“王上的大事都商议妥了?”
仁玑摇摇头:“我的大事,自有你去安顿,不需我费心。”含光被他推挤着,含混道:“那么,那么这星主会盟,你是答允还是不答允。”仁玑扑他在榻上,撑了身子笑道:“我若不答允,西边都把太阳拘了,不叫它从东边升起来,你信不信。”
含光被他逗得笑了,问道:“你就这样顺遂着他。依着我说,嫁进来的人是芥菱,你娶了的心可是芥展罢?”仁玑哎一声,埋怨道:“如此杀风景的话,说来做什么。”含光立时转口,讨好了贴紧他笑问:“接下要我做什么。”
仁玑笑道:“北境七位星主,淳齐涉事其中,余下六位。我自不必说,萤窗淳于也不必担心,芥隐那老东西是必定站淳齐的,那么还有两个人。”含光接口道:“上宰洛奕,你弟弟仁玺。”
含光笑道:“这么算来不必担心,即便这两个站了淳齐,那么是三票对三票。”仁玑笑道:“六人之中,须得四人认定淳齐有错,方能行此事。芥展要星主会盟,就给他个面子,这会盟的结果却要万无一失。”
含光哦一声:“你是说,剩下的两人必要有一个人听咱们的。”仁玑点头笑道:“这事就交给你啦。”含光笑道:“这简单的很,你弟弟我拿不准,洛奕总是听你的。”仁玑微笑道:“你说芥展是不是蠢?”
含光还要再说,仁玑已吻住了他。飞雪连天,屋里春暖袭人,良久,含光呻/吟道:“你为何如此厌恨淳齐?”仁玑微喘道:“谁让他同西字沾亲。谁叫我不能痛快,我便叫谁不能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