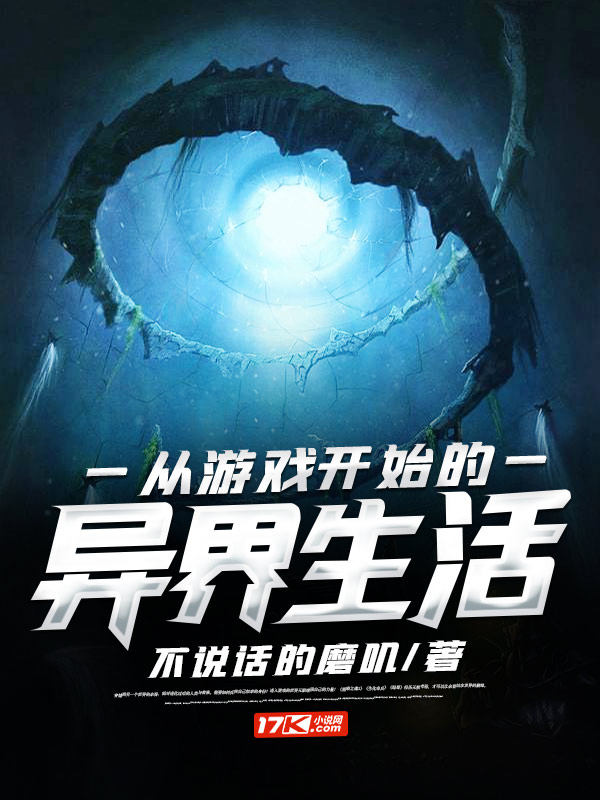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小山轻声唤道:“奚止,奚止。”
雪狼王振作精神,起身去开门。小山捧了只袋子笑道:“心远殿下送金子来了,就放在奚止这吧。明日用不了这么多。”雪狼王接过袋子,心想小山看着莽撞,其实心细,知道不占银钱上的便宜。
小山走了,雪狼王把袋子搁在几上,又去石榻上坐好。奚止却道:“我今天累了,想早些歇息。”雪狼王顺从道:“明天还要去逛市集,早些歇了也好。”想一想又问:“要我陪你去吗?”
奚止仿佛并不期盼,懒懒道:“你没有事吗?”雪狼王还有诸多事要面见裕王,比如商量星主盟会,还有聘订芳冉也是繁复。他却说:“我没有事,能陪你呢。”奚止随口道:“那就同去罢。”说罢了起身下榻,向楼上去了。
雪狼王在楼下耽留,让奚止从容换衣梳妆。他吃了东西,只是食不知味,也不知吃的是什么,又饮尽陶壶里的清水,听听上面没了动静,便提袍上楼。
灯烛调得极暗,火苗小的瞧不见,奚止缩在床榻里睡下了,她的黑发直铺在榻上,像闪着光的瀑布。
雪狼王取水净面洗手,脱了外袍躺下,大睁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石顶。未来是没尽头的黑暗,黑森森的,不知会有什么。
好在有奚止在,无论经历什么,他们总是在一处的。他怕吵醒了奚止,不敢摸她的手,指间绕着她的长发,安然闭上眼睛。
他知道她累了,并不想烦扰她。
雪狼王慢慢朦胧,分不清睡了还是醒着,脑子仍想着事,人却不在场似的。奚止动了动,雪狼王猛得醒了,没等他怎样,她翻身偎了上来。
他还没开口,便被她吻住了。雪狼王闭上眼睛,回应她的纠缠。奚止抽开他的衣带,褪去他的中衣,他嗓子里低哼着,心跳得砰砰响。奚止终于放开他,娇喘微吁。他翻身压住她,胡乱剥下衣裳,吻她耳朵说:“以为你累了。”
奚止低声唤他:“淳齐……”他答应了,她又不吱声了,只是缠得紧。他支了身子要下床,奚止惊道:“干什么!”雪狼王知她多心,赶紧附身回来,吻她说:“灯不够亮。”
奚止红着脸,却搂着他不放。他也顾不上灯了,半明半晦里,只觉得她比往日狂放。她的大胆是赤诚的大胆,带着略微造作的妩媚,可这对雪狼王足够了。他努力讨好她,只怕她不开心,有那么一瞬他有了错觉,仿佛奚止是女王,他才是王后。
其实他愿意的,雪狼王想,他真的是愿意的。
奚止抚着他的背,摸着一层水,是他出的汗。她张开掌心喃喃道:“秀要泉里是第一次。”雪狼王委屈着说:“我也是第一次呢。”奚止笑道:“我不信!”雪狼王道:“雪屋里除了泥鸿他们,那就是太黄啦,啊,是了,还有诸怀。”
奚止问:“不是有小娘子吗?”雪狼王道:“小娘子只到关内,谁会去浮玉之湖。”想了想搂紧她说:“忘了,你会去。”奚止轻声哼着,雪狼王咬牙道:“你那条绿裙子,真是,真是,穿来就是叫人剥掉的。”奚止婉转的嗓子像在唱歌:“你那时候就不怀好意。”雪狼王道:“我的床是谁都能睡的?若是怀着好意,怎能叫你睡上去。”
他拉她起来,奚止伏在他肩上低低道:“可你选了流月。”她自己喘着,却不肯放过他,仍是说:“她的衣服破啦,是你撕的罢。她明明在哭,可你只穿着睡袍。”她总是勾着他乱想,让他在这时候也逃不掉。雪狼王投降说:“都是你的好不好?”奚止推他仰倒在榻上,咬着他的唇说:“我不信呢。”
好容易歇一歇,奚止仍伏在他身上,舔他肩上的伤。雪狼王摸她头发说:“我咬了你,也该你咬回来。”奚止摇摇头,一会又问:“若我不是奚止,你认真爱上了碧姬,那可怎么办?”雪狼王叹道:“这问题简直做一次问一次,我可说了几遍了?只要是你就好,碧姬也罢,奚止也罢,我都认了。”
奚止不高兴,修长的腿跨过他的腰,说:“若我问十遍,你可做十次吗?”雪狼王无奈看她,无奈道:“奚止殿下,小的是个人,不是布偶木傀啊。”奚止爬在他身上,撒娇说:“我不管。”
她不管了,他还能怎么办。
石屋的窗细窄,压住了满天星光。这屋里像个洞,闪着幽微的篝火。到最后一次时,雪狼王说:“明天我下不了榻,去不了市集,那可是你的错。”奚止的声音甜到发腻:“日后就是这样了,叫你没力气下榻,没力气理会芳冉。”
雪狼王被她说的性起,一把翻她过去,奚止啊得叫出来,回了头看他,眼睛能拧出水来,只是说不出话。他看她娇滴滴的,急凑着吻她,用力吻着,恨不能吞她入腹。
也许星星都睡了,屋里才静下来。雪狼王是真累了,横在床上睡着了。奚止躺了很久,她坐起来,附身看了看雪狼王。
他真好看。长发乱拂着,丝丝缕缕挡着脸,奚止的指尖顺着他的眉心,走过他的鼻子,划过他的唇,落在下巴的玲珑沟里。她不敢落实了,怕他醒来。
她按着她的决心,溜下床穿好衣裳,坐在几边。四极的笔,最好用的是北境,最艰难的就是西境了。也许是织布的布角料裹作的笔头,软而塌。奚止还是认真的,一笔一划写下去:
我走了,淳齐就死掉了。我留下来,奚止就死掉了。
我不想委屈自己,成全你活着。
我不知去哪,他们亦不知我去哪,不要为难夕生,不要为难心远。欺哄我的话,可说与芳冉。
她搁了笔,亭亭起身下楼。楼下的几上放着口袋,是小山送来的金子。奚止打开取了几块掖在腰里,饮尽陶壶里的清水。
她拉开门走进院子,昂首向屋檐打个唿哨。电光一闪,九瞬直冲进她怀里。为了怕它对付雪狼王,奚止不敢让九瞬进屋。
星足楼沉浸在美梦中,明日的憧憬还没有东升,沙漠的星海无边无际,像一条银河,接应奚止踏出驿馆,走向无人的市集。
******
雪狼王醒来时,几上的烛已燃到了头,余下青烟一袅。
他含糊唤着:“奚止。”没有人答应他。雪狼王勉力坐起,看着狼藉的床榻,才知道昨晚辛苦。他夸张着扶腰下榻,楼下已传来小山的敲门声:“奚止,奚止,你起了吗?”
小山爽朗透亮的声音,让雪狼王觉得这日子美好,他微笑了扬声说:“你进来吧。”又自语道:“没去找小山吗,她又跑去哪里了。”
他扶着腰走到几边,看见了奚止的留书。
小山推门进屋,叫道:“奚止,快下来吧,时辰不早啦!蝗石盒子要被人抢光啦。”六义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答她。小山想上楼,又怕雪狼王在上面不方便,于是攀着石墙向上张望。
她刚要张口再叫,便见雪狼王从楼上下来。
也不知为什么,小山忽然觉得冷,好比有人拉开冷库的门,劈面的寒气滚滚而下。她原本踏上石阶的脚不自主的收回来,怔怔看着沿阶而下的雪狼王。他应该是笑着的,可那笑容充满了骄傲和不屑,让小山不敢开口。
他擦过她身边,走到楼下的石榻前坐下,低头研究手指甲。小山皱了眉想,他这样子很像一个人,像谁呢。
没等她想出来,雪狼王冰冷问:“夕生呢?”小山一怔,道:“他,他在三和馆。”雪狼王点头:“叫他来,我要见他。”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是命令,而非请小山帮忙。小山小声说:“好。”她向门口走去,想了想还是站下了,问雪狼王:“殿下,奚止去哪了?”
雪狼王没有抬头,仍看着手指甲,慢悠悠道:“她回南境了。”小山一惊:“她回南境为什么不告诉我?”雪狼王不打算回答,小山等了又等,屋里只有沉默。
她在沉默里尴尬着站了会,转身出了六义馆,向三和馆走去。路上,她终于想起来雪狼王像谁了,也不是像谁,只是他仿佛回到了银针松林,是银袍雪氅,喜怒无常的雪狼王。
六义馆的悄静保持到夕生叩门入内。雪狼王仍用小山走时的姿势坐着,一动不动。夕生受小山警告,说雪狼王“很怪”。他于是小心上前,试探着唤道:“殿下?”
雪狼王问:“这几天你在忙什么?”夕生不敢提《神玉论典》,那里头的话纵是奚止替他译了出来,他也是似懂非懂。他于是说:“也是无事可做。”雪狼王听了起身,道:“既是无事,随我走一趟吧。”
夕生只得答应。两人走到门口,雪狼王指一指几上的口袋:“带上金子。”夕生道:“是。”织布口袋沉甸甸的,夕生往里看看,指头粗的金块,一块块摞着。夕生不由问:“去哪里啊,用的了这么多吗?”
雪狼王已出门去了。
市集依旧热闹,色彩斑斓的织布像旗帜,飞扬在大漠的蓝天下。雪狼王信步走着,一时吩咐夕生:“问问哪里有买卖奴人的。”夕生只好寻着路人问,路人说:“走到头再往右转,有怀仁池,是买卖奴人的地方。”
他们依着指点直走右转,有个广场样的空地,中间用石头砌起圆形旱池,里头或蹲或坐,或站或走动,大约圈了数十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七八个牙人立在圈外,手握长杆,若是买主看定了,那长杆便探进圈去,勾了奴人叫他出来。
雪狼王负手看了一圈,停在三点钟方向。却说今天司掌奴人买卖的头子唤做胜好,他远远坐在卖织布的摊下,借着挂出来的织布乘荫凉。人群之中,雪狼王自然是出众的,胜好心想:“这位不知是何来历,西境贵人里没有我不识得的,他却是眼生。”
他眼见跟着的夕生捧着个袋子,仿佛沉甸甸很有货。袋子是白织布的,钤着淡蓝圆章,里头画只飞虎。胜好心中一动,暗道:“这袋子上的表记是诸王子才用得。难道是王室的贵客。”
他忙于巴结,慌张站起来,三步赶到雪狼王身边,点头笑道:“大人,可是要买人?”雪狼王瞧他一眼,只说:“是。”胜好夸耀道:“怀仁池的奴人是远近最好的,大人是贵客,要买需得在这里,切莫被外头的路数给骗了。”
雪狼王并不多问,笑一笑道:“要身体强壮的,要能干的。”胜好听了,忙指挥了牙人勾过四五个奴人,笑道:“大人瞧瞧这几个可好?”夕生见其中有个老者,高材极高大,却弯腰驼背,满脸胡须,只是不肯抬眼看人。
他不由指了问:“这位大爷多少岁了?”胜好呵斥道:“白象,问你呢!”老者白象听了,仍是不抬头,匆匆说:“九十三了。”夕生大吃一惊:“九十三了?我瞧着您仿佛只有六十出头。”
夕生认着生来平等,脱口说个“您”字。白象听了,抬目盯了他一眼,就这一瞬,雪狼王见他眼中精光隐泛,绝非寻常奴人。他沉吟了道:“留民的寿数过了六十便是高了,这位是仙民吗?”
胜好笑道:“大人好眼力,正是仙民。因在东边犯了事,不敢在东境待了,混在我们这里给人做活计。他很能干的,磨铁造屋,织梭染布,伺候牲口,那是没有他不会的。”
雪狼王点了点头,道:“既是如此,那就跟着我吧。”胜好高兴,连连称谢,转而又悄声问:“大人,要不要小娘子?”雪狼王还未答应,夕生奇道:“这里头哪有小娘子,没见着啊。”
胜好笑道:“大人若有意,请那边坐坐。”夕生瞧雪狼王呆呆立在太阳下,只看着脚下不说话。夕生凑近低唤:“殿下?”雪狼王恍然回神,勉强一笑,若无其事说:“有小娘子更好了。”
胜好大喜,领着雪狼王钻进一处织布连成的帐篷。雪狼王进去便觉得香,脂粉的浓香。他们刚进去,里面便有银铃轻响,挤着七八个小娘子,都穿着鲜艳纱裙。
其中有个着鲜绿色的,雪狼王猛得见了,心头便像被狠捅一刀,痛得翻江倒海,再也拿不住平稳劲。胜好恰巧递过石墩,雪狼王坐了,手指直抠进石缝里,想着她留下的话,暗道:“我说的每句都是真心,你不肯信,却说我欺哄你。”
夕生附耳道:“殿下,这几个的姿容比流月差远了,咱们别花冤枉钱罢,缺人伺候还是买女奴,划算呢。”雪狼王冷笑道:“谁说的,我看漂亮的很。这屋里有几个人?”胜好忙道:“共是七个。”
雪狼王道:“给钱,我全要了。”他说着起身,低头便出了帐篷。夕生无法,只得算清了钱,叮嘱胜好把一众人都送到星足楼,交给个叫“周泉”的。胜好做了大生意,点头哈腰跟出来,夕生已顾不上理他,直追着雪狼王去了。
雪狼王在市集乱走,夕生也只能跟着。两人走了一日,夕生袋中的金子用去了四分之一,雪狼王简直恨不能买下市集。直走到太阳西下,把市集左右前后逛了个遍,雪狼王仍是不想回去。
雪狼王忽然站住了。夕生抬眼一瞧,路尽头是个石头屋子,门前围着石篱,悬着面杏黄织布旗子,上头弯曲曲绘了字,夕生不认得,那是个医字。
夕阳西下,石头房子前站着个人,如弱柳扶风,娇花照水,却是芳冉。
雪狼王不向前,芳冉也不迎来,隔着十来步,两人就那么站着。夕生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总觉得有些古怪。半晌,雪狼王低低道:“回去!”
他说罢了转身便走,夕生只能踉跄跟上。等到了星足楼,天微微擦了黑,月亮起了。穿过星足楼的大院,到了六义馆前,雪狼王忽然站住了。
他看着月亮问:“昨晚月亮是圆的吧?”夕生哪在意这些风花雪月,愣了愣搪塞道:“是,是圆的。”
雪狼王嗯一声,很久很久,他说:“再不会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