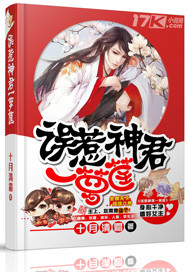“这孩子,不会又跑去她姐姐倩凝那儿去了吧!”乜飞不由推测道。
“我已经让永浩的两位叔叔去看了,只是他俩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到底在不在她那儿!”
“还没回来……那这般,我现在就挨家挨户地去说一说,叫大家都帮你找找。——对了长风,你现在回去把这事给你爹说一声,还有彩苓,你也回去给你爹说一声,叫帮忙找找,我就不亲自去通知他俩了。”乜飞当下便做了决定,还未等长风三人应答,便先动步出院去了。
长风与彩苓既得乜飞吩咐,当下便三言两语道了别,各自回家去了……
未几已是天黑,却听得乐天村犹响着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永浩——永浩——”
却始终无人应答。
夜色浓重,透过细细的门缝,看得见长风家的堂屋里亮着烛光,又听得里面人声嚷嚷,竟有几分热闹。
——原来是长风与远志、青云以及李氏正围着一桌,就他此次乡试中榜一事正聊得火热。
忽然间,却听得堂屋的门响了。三人忙移目一看,却见是殳鹤回来了。
“爹!”三兄弟连忙呼了声。
“怎么样,找着永浩了吗?”长风当下问。
但见殳鹤手提一灯笼,低头面色一副淡然,待跨进屋内方回身将门带过去了,一句话也没说,便朝桌旁行来。
“爹您坐!”青云方忙从座位上起身,一面示意殳鹤坐下,一面接过他手中的灯笼。
殳鹤既行至座上坐下,方轻叹一声道:“没找着啊……”
“没找着,怎么会呢!”长风疑中带焦,“那他两个叔叔回来了吗?”
“回来了。”
“那他们俩也没找到永浩?”长风又问。
“对。两人去永浩舅舅家找了,又去倩凝那儿问了,都没找到他影子。”
“奇怪,他究竟去哪儿了……”长风不禁伤透了脑筋。
“永浩这小子也是,”李氏带着半分嘲意,“遇到一点事就离家出走。上次他不是和他嫂嫂吵了一架吗,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弄得全村人这儿找,那儿找,最后还是在他姐姐那儿找到。你说,都这般大个人了,能不能让人省心一点啊!”
长风听了,不禁觉得李氏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即辩道:“哎呀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永浩他嫂嫂是个什么心肠的人。莫说是永浩了,就算换着是我,也未必会受得了的。况且永浩这人本来就性格内向,遇见什么事总喜欢藏于心里,不对外人说。这般时间一长,心中得积压多少的苦闷啊!”
李氏“哼”的一声道:“苦闷?他好歹也是大男子汉一个,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呀。再怎么说,他嫂嫂也是一妇人家,力气大不过他,身板强不过他。她要吵就等她吵,她要闹就等她闹,难不成她还敢动手?这就算要动手,也干不过啊!”
“你懂什么啊!”殳鹤这时也生起些不耐烦,当下对李氏一句微斥,又问:“饭菜都弄好了吗?”
“弄好了——,就等着你这位老爷回来吃呢!”李氏目色上斜,几分不屑,说罢方撑桌而起,朝厨房而去。
“娘,我帮你端饭菜。”青云说着,亦忙跟了上去。
这时远志亦发话了:“到处寻都寻不到,那该如何是好?”
“还能怎么办?只有明天接着找喽!”殳鹤透着几分无奈。
“爹明天还要去帮着找?”远志问。
“我还去干嘛。”殳鹤一句否道,“今天和村长他们找了那般久,先是将整个村子找了个遍,后又去邻村、山上找了,哪还有处可去?再说了,这是别人家的事,他自己会知道想办法,我一外人瞎操什么心啊。只能说,能帮忙便尽量帮忙,帮不了的也就算了。”
“也是……”
……
话说,第二日天还未亮,黄氏便又早早出了门,去四处找寻了一番,没有结果。后又只得命永浩的两位叔叔去县城里等较远的地方去找寻,这般又花去了一整日,却仍是一无所获。不由心灰意冷,悲痛欲绝,却已是再无他法。
※∽※∽※∽※
因为一个忙于官务,一个忙于差务,故远志和青云亦不能在家里久待,第二日便要返回县衙去。
这日一早,一家人用了早食,长风便送两兄离去,待将两人送至了离家不远的村间小道上方止。既目送二人离了去,自己亦转身回家去了。
行了几步,却忽地听见背后传来一熟悉的呼喊:“贤弟!”忙止步扭头一看,却见是曾宏宇奔着来了。
“曾兄!”长风忙呼了一声,又喜着道,“好久不见你了啊!”
曾宏宇片刻方至了长风跟前,却是满面喜色地拱了拱手道:“贤弟!恭喜恭喜啊!昨日没来得及来找你,今日说声恭喜不算晚吧?”
“不晚,不晚。”长风笑了笑,又摊开一只手示意道,“不如到我家里坐坐?”
在此以前,曾宏宇只来过长风家一次,即他制服盗贼李二那次,却也纯属巧合偶然。当时两人并不怎么熟识,仅仅聊了三两句,且主要是相互打了打招呼,并未像如今这般想畅谈便能畅谈。而后来尽管结为口头上的兄弟,也单只长风隔三差五地去曾宏宇家,曾宏宇却从没来过他家。
未曾想到曾宏宇一见邀请,便爽快答应了:“好啊!”
“走!”长风一喜,这便忙领着曾宏宇朝自家而去了。
至了屋前,却见殳鹤正在院坝中勾身锯着木头。长风方呼了声:“爹!”
殳鹤扭过头来,却见是长风携曾宏宇来了,方忙放下手中事务,前来喜色迎着曾宏宇:“曾贤侄!快进来坐!”便一面以手示着意,一面将曾宏宇往屋里领。
“鹤大叔在锯东西呢?”曾宏宇一面随殳鹤进屋,一面随口说了一句。
“这不闲着无事嘛,锯锯柴。”殳鹤笑道,又问,“对了,你今日怎么突然想起来我家做客了呢?”
“这不长风贤弟刚刚中了解元郎吗?我来与你们道道贺啊!出门走得匆忙,什么也没带,鹤大叔莫要怪罪啊!”曾宏宇说着,已行至堂屋里的桌旁,于一方条凳上坐下了。
“哪里哪里!”殳鹤摆手客气道,“昨日你爹来,不是送了贺礼了吗?再送啊,我都不好意思了。”说着亦于桌旁另一方坐下了。
方一话毕,却见李氏这方亦从房间里出了来,见了曾宏宇,竟觉几分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只携着几分疑惑问:“他爹,这位是?”
因李氏乃一妇人,平时少于出门,不像殳鹤与长风那般,时而还要去曾铸家,故而没机会见到曾宏宇,与他不熟识。
“这位是曾贤侄,曾经多次与你提过的。”殳鹤介绍着道。
曾宏宇听得殳鹤为自己介绍,亦忙起身向李氏施了施礼,“晚生曾宏宇,曾铸之子。”
李氏一听这话,瞬间就反应过来了:“哦——!想起来了,就是曾经在我家门前帮村长捉盗的那个。你瞧我这记性!”又朝曾宏宇压了压手示意着道:“坐吧坐吧!”
“还不快去沏茶!”殳鹤当即吩咐了一句。
“是。”李氏得命,当即扭身便朝厨房而去了。
三人相继于桌旁坐下了。
曾宏宇这方道:“说来贤弟可是真厉害啊,竟然一考便考了个解元,实在不简单呢!想科举本就是一厮杀的战场,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既有人过,便有人过不了,而能过的人自然在少数,其难度可想而知。有的人读书读了几十年,方才上了一个榜,便莫说什么解元郎了。所以说啊,像贤弟这般能一考便取得甲位的,着实甚为罕见,可谓是几十年难得一见。这般看来,贤弟来年的春闱是大有希望啊!”
“希望自然是有的。”长风带着几分谦逊,“只是啊,我这次能取得解元,多多少少也有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平时我在书院,见比我努力的大有人在,然而一到了院试乃至如今的乡试,许多人便是不行了。而这些人中,有好些连院试都没通过。虽说我这次倒是一马平川,但也骄傲不得,亦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啊,来年定要栽了跟头。”
说话间,李氏已从厨房里端了茶水和杯子来,依次为曾宏宇、殳鹤及长风倒上了一杯。这便静静立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三人的谈话来。
“贤弟能这般想自然是好。”曾宏宇一句赞叹,又忽地问,“对了,那乜永浩与你不是同学吗?听说他前日失踪了,现在可找到了?”说着又看了看殳鹤。
“没有啊!”殳鹤丧气地摇了摇头,“现在他家里人连个他的消息都没有。”
“听说他是因为考试没考好,所以才不见了踪影的?”曾宏宇又问。
“不知道啊!”长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这次不是第四次参加乡试吗,结果又是和往几次一样,连榜都没上,换着谁能不心伤?而他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平时万般的努力,在书院整天都待在座位上埋头看书,连学室门都少得出,可是呢,这结果偏偏就不如人意。”
“听你这么说,我算是看清楚了!”曾宏宇瞬间一悟,“这读书啊,不仅得看你努不努力,还得看你有没有那天赋。若是你没那天赋,即便是再努力,未必就能取得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