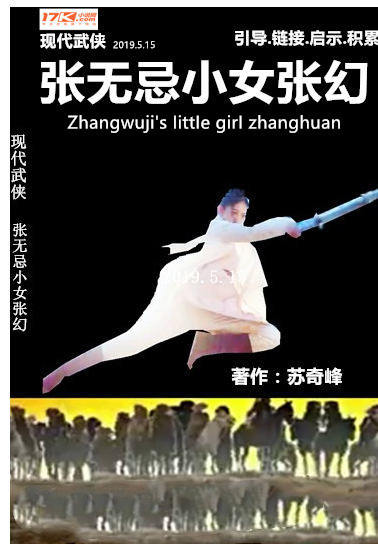正准备睡觉之时,林塘来到了大家的卧室,大家都很吃惊,因为师父平时很少到这里来。林塘笑眯眯地道:“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休息了。请大家到议事厅一聚,有要事相商。”
不一会儿,桑山弟子全都在议事厅了,当然,除了还被关押着的杨坠。
林塘朗声说道:“我刚才仔细想过了,杨坠虽有嫌疑,但他说的话也不能全然不信。因此我觉得,应该给杨坠一天时间,让他去找到传他武功的那位武林高人,那人虽不愿旁人知晓他的事情,但为了救杨坠的性命,想来也会出面的。杨坠此人,最重信诺,他必不会趁机逃跑。此事事关桑山派荣誉,因此要与众位商议,大家觉得此法妥不妥?”
闵阐第一个叫道:“极妥,师父,我赞成!”
接下来赞成之声响成一片。
突然一人喊道:“大家安静一下!”大家的声音瞬间息了。大家齐向那人看去,见是于继尊,只听他说道:“大师哥极重信诺自是人尽皆知,但此番乃是生死关头,怎可保证他不逃走?依我看,还是找个人跟着他为是。”
林塘道:“此节我也曾想到,但那位武林高人不让杨坠泄露此事,自是不欲见外人。若让人跟着,恐怕便找不到那位高人了。”
——————————
第二天一大早,林塘来到关押杨坠之处,正欲将事情给他说,却见他满脸发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是病了,林塘伸手摸他额头,感觉滚烫,原来真是病了,他自己颇通医术,忙去熬药。
听说大师哥病了,许多人都来看他,闵阐见到大师哥的病容,心想:“大师哥定是气病的,唉,真是可怜哪!”
从师弟师妹们的口中,杨坠得知了师父的决定,他显然十分激动,只盼自己的病快些好了,好动身去寻吕全务。
喝了师父熬的药,杨坠恢复很多,但仍觉全身无力,心想自己的生死全系于能不能找到吕全务了,但愿他千万别出门啊,想到这里,杨坠觉得,白天去找他可能找不着,但若晚上去找多半能寻到,晚上人们会睡觉,自会在家里待着,到时候只要去找吕全务教自己武功的地方附近的房子就行了。
于是他再也等不及了,此时已是傍晚,病虽未痊愈,但走几里路自是不在话下,当下禀明师父,说给自己一晚上时间,若还找不到传自己武功那人,便回桑山自杀。
杨坠走的时候,闵阐在他身后默默地看着他。杨坠的身影越来越远,闵阐终于看他不见,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忽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向声音来处看去,原来是姬信泛。他心中掠过一丝不安。
姬信泛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身前,说:“闵师哥,终于找到你了!”闵阐问道:“姬师弟,找我什么事?”姬信泛说:“桎梏找你下棋!”
闵阐心中一动,说:“桎梏?她找我下棋?”姬信泛道:“是啊,你快来吧!”
闵阐想:“天这么晚了,桎梏还找我下棋,这可真有点奇怪。不过,她既然找我,那我是求之不得啊!”马上跟着姬信泛去了。
二人来到桎梏的家里,桎梏显得很吃惊,她说:“闵阐你还真来了!”闵阐说:“当然了,你是我的朋友,你找我下棋,我当然要来。”
闵阐和桎梏在棋盘的两边坐好,闵阐见姬信泛还站在一旁,便对他说:“姬师弟,真是麻烦你了,天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姬信泛笑道:“闵师哥,这里是人家桎梏的家,人家主人还没赶我走,你怎么能赶我呢?”
桎梏朝姬信泛一笑,说:“你爱留下看我俩儿下棋便留下吧。”姬信泛说:“多谢桎梏姑娘,我正想瞧瞧闵师哥的棋艺最近又长进多少呢。”说着便坐下了。
闵阐也不再说什么了。二人在灯下便对弈起来。闵阐感觉到桎梏的棋艺并不高,因此便手下留情。桎梏也渐渐感到自己棋力远不如对方,刚开始每一步都认真思索,到后来却很急躁,下着下着就方寸大乱了。
桎梏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闵阐问:“桎梏,你困了么?”桎梏点点头:“嗯,是挺困。”闵阐于是说:“要不咱们明天再下吧?”桎梏还没回答,姬信泛抢着道:“围棋不仅是对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毅力的考验,能在很困的情况下集中精神下棋的人才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桎梏,我觉得你这一步下在这里会更好。”说着拿起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桎梏仔细看了看,拍手道:“果然很妙!”
就这样,桎梏一边下,姬信泛一边在旁边给她出主意,可时间一久,桎梏就厌烦了,她说:“姬兄,要不你和闵阐下吧。”姬信泛说:“那可不行,今天是你找闵师哥下棋,我怎么敢和你抢?还有你别忘了呀,是你说只要我把闵师哥找来,你就会和他下一晚上棋的。”
桎梏伸了个懒腰,说:“可我现在真的困得连眼都睁不开了。”闵阐见她连打哈欠,确实是困得厉害了,便说:“桎梏,你去睡吧,下棋再重要也没有睡觉重要。”姬信泛却说:“做人不能食言呀。”闵阐替桎梏辩解道:“她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困……”桎梏道:“就是,再说,下一晚上棋也不是我先说的,是你让我说的。”
闵阐心中一动,是姬信泛让桎梏说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桎梏想和我下一晚围棋,而是姬信泛让她这么做的。闵阐看着姬信泛,说:“姬师弟,你为什么想让桎梏和我下棋呢?”姬信泛显得有点紧张,说:“我……我就是想在旁边看着,这样也能长进不少。”
闵阐对姬信泛一笑,他已经想到,可能是姬师弟看出来我喜欢桎梏了,想帮我创造接近桎梏的机会,姬师弟真是我的好兄弟呀。
闵阐对姬信泛道:“桎梏毕竟太困了,让她睡吧,我和你下到天明。”
于是,接下来就是闵阐和姬信泛二人的切磋了。
——————————
沉醉在棋局间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闵阐不经意间一抬头,发现天已大亮了,这时姬信泛说了声:“我输了。”闵阐说:“承让。”站起身来,看见桎梏还在睡着,就不向她辞行了,他对姬信泛说:“我们回去吧,大师哥应该已经找到那位高人了。”姬信泛满脸笑容,说:“是啊,这样大师哥就能洗刷掉自己的冤屈了。”
二人并肩而行,走到离住处不远处时,看见前边聚了一大群人,闵阐感到奇怪,快步向前,人群中的屈浊兴看见他,叫道:“阐哥,快来!”闵阐挤进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那人的脸变成了蓝色,而那人赫然便是杨坠!
他大吃一惊,万料不到杨坠竟会中了和伍丰适同样的毒,旁边的林塘对两名弟子说道:“你们把你们大师哥的尸首抬去伍丰适墓边埋了吧。”
闵阐叫道:“慢着!”蹲下来对杨坠的尸首进行了一番查看。林塘说:“闵阐,还有什么问题么?他中的是和伍丰适一样的毒,他用这种毒自杀就是承认他就是杀害伍丰适的凶手!”
闵阐说:“看起来确实是同一种毒药。”站起身来走了。耳朵中传来同门的议论声:“伍丰适的事情今天终于了结了。”“没想到大师哥还真是凶手,我本来还相信真有那么一位高人呢,想想自己真是傻,居然相信大师哥的胡言乱语。”“以后不准叫他大师哥,他已经被逐出师门了!”最后这个是师父的声音。
这日上午,闵阐把屈浊兴、冯劝层和花尘叫到一个隐秘的所在,对他们说道:“我们得给大师哥报仇!”那三人俱吃了一惊,一齐说道:“什么?!”
闵阐向他们解释:“大师哥是给人害死的。”屈浊兴说:“他不是自杀的么?”闵阐又道:“不是,他的裤脚有些磨损,显是被人拖了一段路程。”冯劝层道:“什么?你是说他不是在发现他尸体的地方死的么?”闵阐说:“对,而且他衣衫不整,也是一个证据。我发现他胸口的衣服上有些许泥土,应该是被人踹了一脚。”
花尘说:“踹了一脚?大师哥是被人踹死的?”
闵阐说:“这一脚不是致命伤,但也很严重,因为大师哥重病未愈,身子还很弱。真正致他死命的是那能让脸变蓝的毒药。”冯劝层说道:“阐哥,你还真聪明,可是到底是谁杀死了大师哥?”
“我已想到了一人。”闵阐说。
“谁?”三人不约而同说道。
“姬信泛。前天我看见他去伍丰适坟前献酒,还磕头,我就已经很怀疑他了,昨天晚上他带我去桎梏家中下围棋,一整晚我们三个都在一起,我觉得他这是欲盖弥彰。”
屈浊兴问:“何以见得?”
“他献酒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也看见我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怀疑他,所以故意一晚上都和我在一起,为的就是让我知道,大师哥不是他杀的,因为他没有时间,但他要在晚上杀大师哥也很容易办的,只要指使另一个人去办就好了。”
屈、冯、花三人思索半天,终于明白了闵阐的意思。屈浊兴说:“那你为什么不和师父说,而要和我们说?”
闵阐说:“我刚才不是说了么?姬信泛知道我在怀疑他,我不能打草惊蛇。再说了,我只是怀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凶手,因此才来找你们帮忙。”
花尘说:“找我们帮什么忙?”冯劝层说:“阐哥,你说吧,是什么忙?虽然我不喜欢大师哥已经很久了,但我也不能眼看着大师哥死了还被人冤枉,我愿意尽我所能,让大师哥的名声恢复清白。”屈浊兴很激动,说:“小层,说的好!”
闵阐说:“老屈,小层,你们俩暗中盯着姬信泛,要是他有什么异常举动,老屈继续盯着,小层来告诉我和花尘。”屈浊兴拍拍闵阐的肩膀,说:“放心吧。”
——————————
这日晚间,闵阐正在补觉,冯劝层急急忙忙地赶到,花尘赶忙叫醒闵阐,冯劝层对他俩说:“姬信泛偷偷地下山了。”闵阐和花尘赶忙跟着冯劝层前去追踪。
他们一路下山,按屈浊兴留下的记号找到了屈浊兴,四人一起跟踪姬信泛。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姬信泛来到一间小屋前,闵阐对他的三个同伴说:“你们在草丛里躲着,我上前瞧瞧。”三人自然知道闵阐是怕人太多被姬信泛发现了,都听闵阐的话伏在了草丛里。
姬信泛走进了小屋,闵阐站在窗边朝里张望,大吃一惊,原来屋子里的地面上躺着一个老头,他的身上流了一大摊血,已经干了,显然死去很久了。
闵阐又去看姬信泛,见他的表情也很吃惊,闵阐想:“他不知道我在旁边瞧着,自不会装作吃惊给我看,那这说明,莫非这人不是他杀的?”
姬信泛的表情随即变得很镇定,他抱起那老头的尸体,走出了屋子,刚走几步,又把那老头放在了地上,回到屋内,拿了一把锄头,抱起尸体又走,选了一处地方,用锄头挖了个坑,把老头埋了。这一切闵阐都看在眼里。
姬信泛埋完老头后便走了,闵阐正要与三名伙伴商议,突然看见有一个人从桑山的方向走来,闵阐赶紧隐蔽,等那人走近,看清他是于继尊,闵阐心中纳闷:“于师弟来干吗?”
只见于继尊径直走进那间屋子,闵阐还是从窗口张望,只听于继尊脱口而出:“该死,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