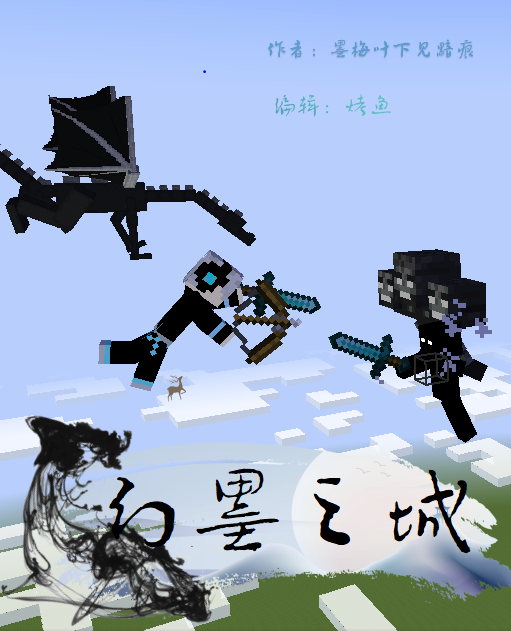猴哥说他的花果山目前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借咱家的推土机用一用。俺寻思他的花果山那么大,咱家的推土机只不过是用来解决小坡小坑的,估计没什么用。猴哥说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咱又不是白用你的,事后油费人工费照样付给你。
高老庄去花果山得好几百里路,如果照猴哥所说那样的话,得先用汽车将推土机运过去才行,这样的话又得增加成本。俺问猴哥为什么不就近叫一辆,猴哥说人家嫌他的活儿太少,都不愿接手,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俺老猪的。
在往花果山运推土机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小小的麻烦:交警看到车上装着那么大个家伙,就说比较近的那条公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得从新修的二级公路上过去。新修的二级公路与原来咱们打算的那条公路基本上属于往两个方向的,如果要去花果山的话还得在半路上绕道另外一条外省的公路才能勉强达到。这样一来无疑是大费周章。
俺问猴哥这样的话还要不要拉过去,猴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花再多的钱都得拉,不然的话山头上那些事儿都得暂停,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
虽然绕过来绕过去绕得俺头都晕,但到底还是到花果山了。原来猴哥的水帘洞仍然还在对外开放,只不过做的是那种愿者上钩的生意。不过说老实话,以俺老猪的审美观点来看的话,水帘洞的水流虽然不如从前汹涌、气势磅礴,但周围的山山水水仍然值得欣赏,特别是花果山。猴哥的漂流河道是搞过一阵子,但后来因龙王饱饿状态下的吐水分量不同,所以就搁浅了。那些漂流用的皮划艇都还搁在水帘潭的边儿上,不知道猴哥是打算把它们当做一个景点呢还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忆。
猴哥打算在花果山向阳和背风的地方分别栽种柑橘、苹果、桃、李、杏、梨等等,这些刚好都是他擅长的。俺跟猴哥说,果子大多都集中在那几个月,过了那几个月基本上就空闲着了,跟咱家的农田一样;不过咱家的农田还可以种些别的经济作物,而你这花果山的果树并不是一两天就能生长得出来的,如果那样的话无疑没能做到资源的最大利用。
猴哥说八戒你行啊,短短的几年时间你就跟往前大不一样了。俺说那是他没有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如果带了一双发现的眼睛的话,那么就可以知道俺老猪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等闲之辈。
过了一阵子猴哥问俺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俺说办法是有,不过不能轻易地告诉你。以前取经一路上猴哥特别喜欢卖关子,什么话都只说一半,害得俺老猪还得蒙头蒙脑地想老半天;如今俺终于有机会卖关子了,所以理所当然地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
后来,不管猴哥怎么问,俺始终装成一问三不知。看得出来,猴哥很着急,抓耳挠头的。
俺寻思不能赶尽杀绝,得适可而止,不然到时候估计猴哥又得骂俺呆子了。
于是俺故意装得很神气地说,猴哥啊,老猪的肚子饿了。
猴哥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赶紧叫旁边的猴头们下去弄吃的。
俺另外说了一句,山果免谈啊!
猴哥说那当然。
之后俺又补充了一句,斋饭免谈啊!
猴哥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吃斋饭,呆子你放心,保证好酒好菜地招呼你。
饭菜果然很丰富,最重要的是还有鸡腿。俺很奇怪说猴头们都吃这个了?猴哥说哪里哪里,这是放在冰箱里招呼客人用的,咱们还是比较喜欢吃果子些。
老猪从来都不是一个亏待人的人,只要别人送俺一根葱,俺绝对会送他一根蒜;比如现在吧,猴哥给俺置办了这么多好吃的,俺就得给他的花果山出谋划策。
猴哥说,呆子,说说你的高见!
一听呆子俺就不乐意了,认为这是对俺智商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俺老猪还是比较聪明的。所以就显出了欲言还休的样子。
猴哥不可能看不出来,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又赶着紧陪不是,又是敬烟又是倒酒的,好话说了一大堆。俺寻思暂时给猴哥点儿教训,也不用做得过了火,毕竟咱们以前都是师兄弟,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早就已经情同手足了。那种感情不是可以说出口的,就像连理树,即使要让它们分开那也是需要时间、也是不容易的。
俺跟猴哥说,你这山头不要让它光秃秃的,也不要让它生杂草,等果树栽上以后你在上面撒一些牧草的种子,要不到半年的时间牧草就会疯长出来,到时候就可以用它们来喂养牛羊之类的家畜了,正好你那养马场空着。
猴哥直勾勾地盯着俺看,直看得俺不好意思了。
猴哥说八戒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样的眼光啊,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俺问猴哥知不知道李天王在高老庄投资了两个市场?猴哥说听说过,不过好像他的事跟咱并没有关系啊?
看来猴哥还不清楚这些情况。
李天王在高老庄投资的一个是水果市场,一个是粮食批发市场,所以俺就跟猴哥说得赶紧给李天王打个招呼,把那个水果批发市场包下来,把花果山结出的山果弄到那里去,一定好卖。这个消息老猪也是在前一阵子才知道的,当时李天王正在高老庄祠堂附近转悠,没想到一不小心竟然把他给碰上了。李天王当时并没有想到咱们,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害怕以后在人情的问题上不好面对。
猴哥花果山的水果是比较有名气的,自从当年猴哥跟随师父去西天取经之后,花果山的那些猴头们群龙无首了,猴哥在的时候还能时不时地上天庭去弄点儿好吃的下来,猴哥一走,什么都没有了。于是那些猴头们就自己想办法找关系把花果山的一部分山果运到了外面去卖,据说大受人们的欢迎;只不过那些猴头没有一般人聪明,更没有猴哥聪明,不知道做大做强,所以花果山的山果始终还是无名之辈。
推土机就暂时搁在猴哥哪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完事儿,虽然放在自家里也并没有多少时候用,但总感觉自家的东西去了别家,心里放心不下。
先前猴哥说大概一两天就可以了,主要是把原来上山的路拓宽,好后面上山的时候车子也能开上去,没想到石头特多,前进得很艰难。
回到家后俺就跟清妹妹商量,说要不要把李天王其中的那个粮食批发市场包下来,依咱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同时维持两个比较大的路子应该没什么问题。清妹妹说你别忘了变形的事儿,我虽然无所谓,忍耐一点儿就过去了,但我父母比较在意这些;再说当初是你自己答应要去变形的,千万不能反悔,不然咱们在老人家面前没法交代。变形的事儿钟医生还在研究一套更加可行的方案,说到时候能更精确地监测到克隆体的各项指标。还有就是,俺认为一个市场只需要定时地拿出一笔钱就可以了,只要行销对路,一般没有什么风险,再说那笔钱对变形的事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把它投出来,小钱生大钱,让以后的路显得更宽一些。
清妹妹还是比较赞同俺的看法,只是说地方势力比较大,不好跟他们硬碰硬。这点也是俺以前的顾虑,高老庄稍微大一点儿的项目基本上都有当官儿的或者是组织插手,外面的人进去一般都会受到排挤。俺老猪虽然忌讳没有那么多,但那些人毕竟是地头蛇,以后不可避免地会跟他们打交道,所以还是礼让为先,不跟他们掺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俗话说强龙还不能压地头蛇呢,更何况俺老猪也并不是什么强龙。
这种事儿俺还是比较看好猴哥,他是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想做的事不管你是谁拦都拦不住,搞得不好就跟你掐架。俺认为这得益于猴哥的洒脱,显得什么都无所谓;也许正是这样,当一个人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别人就会畏惧他。诚如那句话所说,要钱的怕要命的,要命的怕不要命的。如果猴哥能到这里来的话,俺老猪的底气也能增加几分。
俺给李天王打电话提起这事儿,天王说有人正在跟他联系,如果是咱们要的话他一定考虑优先。
过了一天,猴哥又来电话了,叫俺过去看看或者是派个工人过去看看都可以,因为推土机不能动了。推土机是俺跟一个工人给猴哥送过去的,当时俺寻思让工人在那里帮忙整利索了再回来;但猴哥后来说不用,他自己能搞定,只要师傅教他怎样弄就行了,免得麻烦。俺寻思是猴哥的耍性又犯了,看到新奇的玩意儿就总想过个瘾,所以就答应了,只是叫他别随便乱整,不然的话比较麻烦,因为这不像金箍棒那么简单,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看来猴哥还是蛮听话的,有问题了并没有自己动手捣鼓个究竟。
刚好开车的工人比较忙,再加上推土机开过去之前是在家里检修过的,估计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俺决定自己过去走一趟。
去到那里的时候猴哥正跟几个猴头一起在推土机上翻上翻下的,看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俺决定先看看热闹,等他们折腾够了再过去。
猴哥贼精,忙活了一阵子看见没有效果后就再也不忙活了,自己坐在驾驶室内坐镇,指挥一帮猴子猴孙跑来跑去的。那模样哪里是在修车,简直就像探险一样,东摸摸西瞧瞧地,看样子新奇地不得了。
估计在俺来之前他们也折腾一段时间了,也该露面了。
见到俺出现了,猴哥立马指挥他的猴子猴孙们像当年捉拿俺老猪一样把俺四脚朝天地抬了起来,一路颠簸着抬到了猴哥跟前。俺问猴哥到底怎么回事儿?猴哥说他也不知道,只是不管怎么弄它就是不动,比牛魔王的脾气还要倔强三分。说完还显得很恼火的样子,一边抓耳朵一边挤眉弄眼地。
俺先打开推土机的前盖粗略地看了一下,各线路都是正常的,都按照原来开来的时候一样;发动机外面也一切正常;再去看看履带,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俺也纳闷儿了,什么都是正常的没道理不动啊?来之前工人就告诉俺说了,那台推土机保养得最好,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出毛病;更何况在临走的时候还检查过一遍。如果俺老猪找不到原因,也只能叫工人再来跑一趟了。
猴哥见俺跟他一样找不着门儿,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俺一把把猴哥从驾驶室拉下来,自己爬了上去,想试试看到底是怎么个发动不起来。刚一坐上去,俺就瞧见油表的指针已经落到头了。
原来是没油了!害得咱们几个忙活了半天。
后来工人师傅听说了这事儿,情不自禁哈哈大笑。当然,他们笑的是猴哥,因为俺并没有把自己的那些狼狈相说出来,并还夸口说俺是一去就找到原因的。
————
最近高老庄负责文化宣传的人员发给高老庄每家一份宣传高家祠堂的,说是为了配合今后地方上的发展,作为高老庄的人需要多了解一些高老庄的历史。
在俺还没有跟师父的时候,在给兰妹妹干活儿的那段日子,俺曾经去过高家祠堂,那时候那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块不知道是哪代祖宗的灵位牌立在公堂的最高处,之外就是几把破破烂烂的旧椅子,整个大堂显得很阴森,俺当时还吓兰妹妹说这里面一定有鬼,吓得兰妹妹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进去了。以前的高家祠堂外表同样很破旧,仿佛随时都会垮下来一般,不像现在这般亮敞,就跟旅游景点设置的那些古建筑一样,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如今高家祠堂的内部同样比较光鲜,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之后,连原先的灵位牌都改为镀金的了,阳光从旁边的缝隙里照进来,整个屋子都显得金光闪闪的。
自从来到高老庄以后,也去过几次高家祠堂,最让俺觉得奇怪的是,在进祠堂的屋檐下,露天竖立着两尊很别致的塑像,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男的半跪着,双手捧着什么;女的则躺在一张床上,看样子好像是生病了,头发胡乱地掩盖着半边脸,显得很憔悴。俺之前虽然奇怪,但没有问为什么,寻思雕像所表现的主题一定是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因为时下有许多的雕塑都这样,从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并没有诸如伟人雕塑、历史事件雕塑那样拥有宏大的主题。
在看完他们发下来的宣传单以后,俺才发现自己错了。虽然那组雕塑并不是伟人,但是在高老庄历代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心目中,始终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教材,目的是让人们进行反省和参考。
关于那组雕塑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然,到底是不是传说咱们现代人无法确定,毕竟年代久远。俺寻思或许真的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只不过经过后人的润色和杜撰之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或许这本来就只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只不过先人们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所以才把他们说成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雕像主人公的名字男的叫高俅,女的叫司马贞。当然,咱们可以肯定高俅不是《水浒传》中的那个那个高俅,因为两者身处的年代相差实在太远了,即使是用十头牛拉都拉不到一块儿去。司马贞是一大户人家的闺女,高俅是一贫农的儿子。两者在一个极度错误的时间里相遇了,然后又相爱了,继而演绎了一场悲壮的爱情故事。
司马贞与高俅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两个人,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面;但自从他们见面后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发誓永永远远都不再分开。
当高俅与司马贞相遇的时候,司马贞已经与另外一个富豪家的子弟订了亲,是她父母的意思;本来司马贞是不答应这场婚事的,但她的父母说了,如果两家能结为亲家的话,必定能让两家的家业都得以长存。司马贞认为父母是把她当成了家族的砝码,根本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所以整天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声称只有退掉这门亲事之后她才会出来。高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出现在司马贞眼前的。
高俅的父亲是个木匠,那天他是帮他父亲干活儿来的,根据司马贞父亲的要求,为她打造一顶出嫁用的轿子。
做工的工地在院子里的空地上,高俅就跟他父亲在那里忙碌起来,拉锯、弹墨、劈木头。司马贞房间的窗子就朝向做工的空地,她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院落的情况,包括经过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当然,她也看见了年轻的高俅,正虎虎生气地抡着斧头一下一下地砍下去。
司马贞是独生女,从小就娇生惯养,家族里所有的人都让着她,不敢在她提出要求之后说出半个不字,就连她的父母亲都不例外,只要是她想要而又得不到的东西,经过一番生气之后就一定能得到,因为所有人——包括她父母——都会向她妥协。她想,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吧,她不能嫁给那个富家子弟,因为她讨厌他那副嘴脸,她不敢想象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上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只是没想到的是,如今她父母已经不再听她话了,她以前百试百灵的那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因为他们正在为她的出嫁做准备。满院子到处都是红的,连她母亲的衣服都是,好像在欢庆她将要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眼下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高俅他们父子看,看他们边挥动汗水、边有说有笑。
特别是那个年轻的高俅,一脸朝气,仿佛所有的黑暗去到他的身边都会消失掉一样。他的身上有一股魔力,吸引着司马贞将单调的做工过程也看得津津有味。
高俅父子在司马家一共做了三天工,司马贞就趴在窗前看了整整三天。看他们怎样在木屑飞扬中把木头锯开,那散落的就好像她现在的心情;看在他们怎样把大的木头锯成小块,分裂的模样仿佛她的心和肺;看他们怎样把小块的木头打磨光滑,那扬起的刨花就像小伙子激情飞扬的神色,充满了无尽的生机。木块很滑,滑得太阳照在上面都闪闪发光;她还看他们怎样将一块一块的木头逐一拼接起来,组装成即将要送她出嫁的轿子……三天时间,只不过是俺老猪贪睡时的那么一小段,却让两颗原本陌生的心紧紧地靠往一起。
那个年轻的高俅的模样让她羡慕不已。在她看来,高俅所代表的就是一种不屈的精神,一种昂扬向上的劲头,一种尽心尽力的表率;而这些品质她都没有,她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个男子能够用像他做木工一样的态度带她离开这个她厌烦的地方。当然,她也知道这只是幻想,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
联系到自身,司马贞觉得自己甚至还不如眼前的这两父子。自己虽然从小享尽富贵,但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自己喜欢的事,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机会,却又轮不到她自己做主;但眼前的两父子则不同,虽然他们需要在太阳底下挥汗为别人家做工、才能挣到糊口的钱,但他们做的是他们喜欢做的事,不用像自己一样背负着心灵的枷锁。
也许,除了死亡,否则,这副枷锁还会伴随她以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