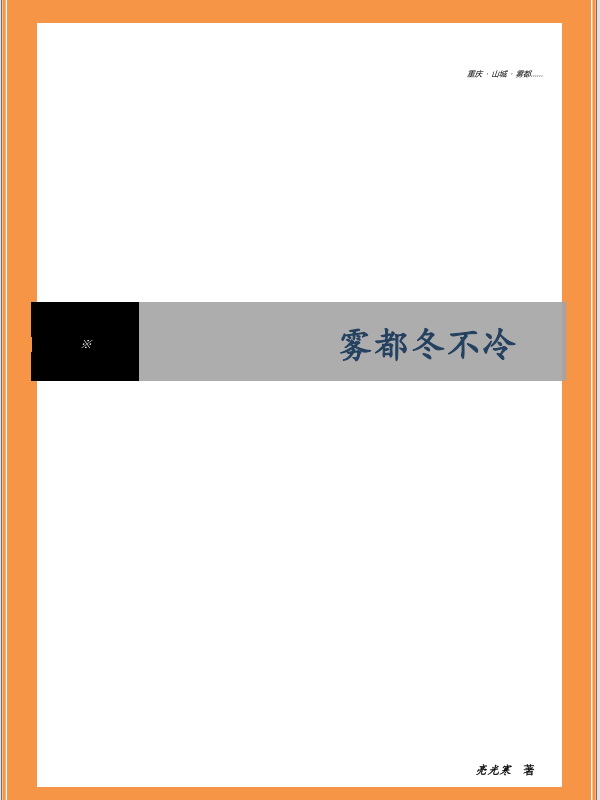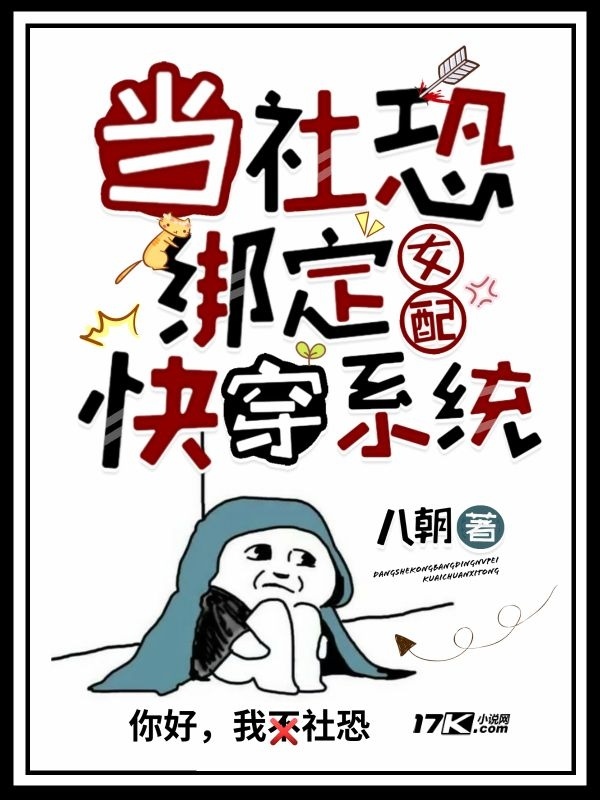死亡,是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两个字眼儿,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最后她决定走一条她从来没有走过,但是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死亡。她想,走一次前途渺茫、自己选择的路,应该要比走别人安排的路满足吧。
第三天傍晚,也就是高俅跟他父亲准备收工的那个时刻,司马贞用她自己最喜欢的粉红色裙带作为带她往极乐世界的交通工具。
那天,高俅正在帮他的父亲收拾做工的家什,等下准备向司马老爷讨要工钱。突然地,从旁边的阁楼里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就听到有人**的声音。父亲见多识广,大叫一声“不好”,急忙叫高俅站在那里别动,自己则飞快地跑向声音发出来的地方。高俅年轻,好奇心强,所以在收拾完家什以后还是沿着父亲的踪迹跟了去。
刚才的声响来源于司马贞的闺房,此时她正躺在父亲的臂弯里双目紧闭。父亲说你过来,先看着她,我去叫司马家的老爷来。于是,他就像他父亲刚才的样子,把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臂弯里。
她的双目睁开了,微微地看着他,他的器宇轩昂,仿佛给她注入了新的生命。她感觉自己的心比往常的任何一次都要跳得激烈,还感觉到一股热腾腾的气流从身体的某个地方一直传递着,直到发梢。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高俅的心里同样像小鹿在撞似地,怀里抱着的这个美人儿,正在痴痴地看着自己,哪有不动心之理?就这样,两个年轻的人,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相爱了。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段恋情势必会招来各个方面的反对,连高俅的父母亲都不支持他的做法,还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但他们毅然决然地相爱了,说什么也不分开。
司马老爷说,既然这样,你司马贞从今往后就不再是我的女儿!
司马贞自由了,但是她从此失去了大富大贵的生活,每天只能粗茶淡饭,并且还不一定能吃饱。
高俅的母亲曾经对她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咱家高俅是不能给你那种富贵生活的。
司马贞回答地很干脆,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算再苦再累也感觉值!
她学会了淘米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学会了把黄了的菜叶晒干然后做成美味的咸菜。她先前温润的小手也变得粗糙起来,但是他说了,现在的她要比以前的她更好看。
她不说话,只是偷偷地笑,然后在心里开出一朵温馨的花。
那年,国内战乱,民不聊生,恰又逢流行鼠疫,死伤者无数。随着年关的越来越近,灾情也越来越严重。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司马贞发现自己下不得床来。而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鼠疫。
根据常理,鼠疫病人是应该要加以隔离的,但高俅说什么都不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说即便是死也要在一起,因为他们的性命早已在他们遇见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得到了重生。病床上的她显得很憔悴,但是她表现得很坚强。看着了无生气的她,他痛心疾首,心想要是当初自己没有那么固执的话,说不定她的病情现在还有得治。她说没关系,她的命早就应该结束了,现在的是他给的,刚好可以还给他。他每天到处寻医病的方,趟过了无数的荆棘和坎坷。
也许是他的诚心感动了神灵,所以在一个夜晚,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托梦给他,说按照他所提供的地址,就可以找到医病的方。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试试,因为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老人说的药方是生长在天山上的雪莲,如今正是采摘的好时节。
老人还说了,要想治好她的病,只能在固定的时辰摘取,不然就会一无用处。那个时辰就是莲花绽放的那一刻。
为了等到莲花的盛开,他没日没夜地守候在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生长在半山腰上的一株雪莲。他守候的时候,仿佛守候着的是她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天气愈来愈寒冷。终于,雪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洋洋洒洒地飞向了大地。雪花很快乐,但是他很冷。直到他身上都已经结冰,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那里有他的希望——雪莲花。
雪莲花开的那天特冷,但他还是在花朵刚刚绽放开来的那一刻将它摘了下来。他是一路跌撞着回到家的,身上布满了厚厚的冰层。到得床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她看起来早就已经气绝身亡了。于是,他就以高家祠堂里雕像的姿态一直跪在司马贞的床前,直到被活活地冻死……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伟大真诚的爱情,就把他们当时的姿态雕刻了出来,作为教训后人的榜样……清妹妹说她以前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没有这样完整,真没想到高家祠堂还有这么一段感人的故事;哪天得抽空去拜拜他们。俺寻思了一下,跟清妹妹说,到时候记得叫上俺啊!
————
钟医生今天打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了解决那个排泄功能不正常的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叫俺抽时间过去看看。俺寻思还是约个具体的时间好些,所以就告诉他说俺明天就过去。
之前那个排泄不正常的毛病钟医生说是因为变形后的八戒大脑关于那部分的指令与排泄系统的神经不一致的结果。比方说大脑发出的指令是在吃食物的时候该分泌多少剂量的消化液,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那么多,多了的话就会引起相反的作用;又比如说吃下去的东西大脑安排肠道蠕动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但变形后的肠道蠕动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可以消化完成,所以剩下的那段时间做的基本就是无用功,白白地消耗能量不说,对肠道也是极大地磨损。
去到那里才知道,钟医生所指的方法其实听起来很可怕,就是改变大脑的存储信息。俺说这可不行,那样一来俺不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么?以前几千年里发生过的那些事对俺来说非常重要,这个方法万万使不得。钟医生说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想先做个试验,看看成功率有多大,不一定能实施;但如果能成功的话,无疑是解决之前那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更何况现在还是在克隆八戒身上做实验。
钟医生建议俺说再生产两个克隆八戒出来,鉴于钟医生自己也顺便做了研究,所以他决定后面的两个克隆八戒只收一个的费用。之前那两个克隆八戒俺已经交代过了,属于医生自己操作不当所引起的,造成了损失;并且钟医生自己也已经答应不再另外收费。
钟医生的打算是这样的。在他把其它的器官跟组织放进到调整的那个机器里面后,克隆八戒的大脑跟小脑同样会被转移到一个很精密的、类似于微波炉的容器中。它看上去像微波炉,其实不是,它的功能要比微波炉的大多了。这个“微波炉”分为两个界面,一边存放克隆八戒的大脑与小脑,另一边存放正常人的克隆大脑与小脑。这台机器的作用就是把克隆八戒脑海中存储的信息转化成正常人的形式。比如之前俺的鼻孔大、肺大,现在变小了,就有必要改变一下脑海中存储的信息,免得它们不协调;比如之前俺的肠宽胃大,现在就有必要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把记忆变成一个正常人的记忆。
这回钟医生取的是俺脚底心上的细胞,俺问他为什么,他说脚底心上的细胞性能要更稳定一些。
整个克隆的程序跟上一次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只有钟医生一个人,他的儿子还有女儿都没有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特别是他的女儿,长得那么标致,不多看两眼真的是一种损失。
在钟医生忙着操作的过程中,俺在他的实验室又四下里转悠了一回,发现这里又多出了许多新鲜的玩意儿,都是前所未见的。上一次俺见识到一只带轮子的脚,这回俺又见识了一只带喷气筒的脚,用来加速人们的前进速度,就像喷气式飞机一样,还可以把人送到天空中去。它上面一共有两个喷气筒,后面一个,脚底一个。俺问钟医生为什么不装四个?前后左右都有嘛。钟医生说那样不行,并且也行不通,因为装在脚背上是没用的,人在下落的过程中是不用加速的。俺又问为什么不在脚的前面装?钟医生说暂时还没有发明后视眼,在倒退的时候看不到后方的情况,所以不能加速,只需按照一般的速度就可以了。另外俺还看到了一种“弹簧手”,据说它的内部是由新型弹簧组成,可以伸长到数十米长,再远的东西想要拿到手都不成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你坐在客厅,想要去厨房拿一杯果汁、而你又不想走路的话,完全可以坐在原地,然后用意念控制手臂的长短,在拐弯儿的时候同样能根据需要弯折的程度进行转动,直到完全向着果汁的方向为止。
钟医生说研发这种器官的本意就是为现在的工作狂还有懒人所设计的,足不出户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还可以从十层楼的地方伸手下来到底楼的商店里买香烟。
钟医生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商人,只要具有一定市场的都在他的研发范围之内。俺告诉他说咱们是同行,虽然有唯利是图的嫌疑,但出发点总是好的。
————
没事儿了俺也喜欢去鱼塘里钓鱼。虽然说大街上到处都有卖鱼的人,但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饲料喂养出来的,根本没什么营养;不但没营养,吃多了对人体还会有害,所以咱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买那种鱼吃。高老庄有不少人也喜欢去河里钓鱼,个大、味儿也不错。但河里的鱼有一个缺点就是肉质太粗,因为一般能被钓上来的都是超过十斤的,稍微小一些的都禁不起河浪的冲击,上不来;更大一些的又相对狡猾,不会上来找吃的。所以俺一般也不会去那里钓。
俺钓鱼的基地很秘密,除非是很熟的人,否则俺不会告诉他。
俺钓鱼的去处就是别家的私人鱼塘。
本来,私人鱼塘是不会允许别人钓鱼的,但那里面的鱼非常美味,俺经常都是情不自禁地非要到那些地方去不可。有人可能会担心说万一要是被鱼塘的主人抓住不就麻烦了?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已经考虑到了。因为一般是下雨天咱们才会去那些地方钓鱼,所以在去之前得进行一番伪装,好使鱼塘的主人在烟雨朦胧里看不清咱们的真面目;即便是真被发现了那也不怕,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最后交钱了事。钱对咱们并不会构成威胁,所以一点儿都不担心这种情况。
上面俺用到了一个词,“咱们”,的确,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的人并不止俺老猪一个人,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感觉还挺流行。据说他们中间还有人自家有鱼塘、来别家“偷”的人,他们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境是在别的地方是体会不到的,他们寻求的就是这种刺激。
“咱们”都是临时组成起来的。比如正当你寻找目标、看到底哪个鱼塘比较安全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人一动不动地坐在某个鱼塘边,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里是相对安全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坐下来钓鱼了,不用说都知道,他们先前一定是打探过的。大家都心照不宣,谁都不会吱声。
在这样的队伍中,俺见识过几个很奇怪的老人。
有次同样是下雨天,俺带着渔具和一个折叠凳四下里找、看哪个鱼塘适合隐蔽的时候,看到附近的一个鱼塘边坐着一位老人家。他什么遮雨的工具都没有戴,光秃秃着个脑袋;不但这样,他还在自己身上批了一块红色的布,看上去非常醒眼。咱们干这种事儿本来就不算正大光明,衣服一般都会尽量选灰暗的颜色,以免被人注意到,所以在老人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估计是怕跟着露馅儿。
俺走过去的时候,老人显得很理直气壮的,仿佛偷人家的鱼是应该的。
俺压低声儿跟老儿说,您呐,还是把身上的红布拿下来吧,这样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老人家转过头来,眯缝着眼睛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俺,然后上上下下瞄了个遍,说道:你以为我是在偷鱼呀!
俺又接着问:您不偷鱼那坐在这里干什么?
老人家说:我在这里等挨骂!鱼塘的主人在看到咱们这些人之后虽然不会报警,但还是会嘀咕几句的,碰上厉害一点儿的就得准备胶袋接口水。所以,被人骂是很正常的。咱们都在躲骂,老人家却来找骂,不知是什么回事儿。
老人家说:在单位在家里,都是我骂别人,现在想出来尝一尝被别人骂的滋味。
如此找挨骂的人俺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还有一次,也是下雨天。那天俺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找了个相对容易藏身的鱼塘后就在岸边坐下来,开始专心致志地钓鱼。俺旁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看上去很专注,一直都是一动不动的。还没到中午,清妹妹说家里有点儿事,叫俺先回去一下。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俺一共钓了三条,每条都是一斤多,心想煮出来一定很美味。奇怪的是,旁边那位老人家比俺还要先来,到那时候为止一条小鱼都没有钓到,俺寻思这老儿的运气不怎么好。
等过了一阵子俺回到那里的时候,老儿仍然跟先前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仿佛根本就没挪动过屁股一样,旁边的水桶里照样一条鱼都没有。奇怪归奇怪,俺自己还是要钓鱼的。
直到老人家把钓鱼线收回来的时候俺才找到了答案,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都钓不到鱼了。因为老人家的鱼线上压根儿就没有鱼钩。
俺很不解,问老儿是不是他的鱼钩被鱼塘里的鱼吃了?
老人家摇摇头,用缓慢的语气说:我钓鱼从来都不用鱼钩!
那您用什么?
用意志!老人家用力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又着手收拾自己的钓鱼线了。
怎么用意志钓鱼?俺又接着问。这个问题在太有吸引力了。
老儿说,钓鱼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直接把鱼从鱼塘里冥想出来,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转移他所专注的东西;具体到钓鱼这件事上来讲就是钓鱼者只要心里想着一条鱼,然后想象把它从水里提起来,如果火候到了的话,就能做到这一点。俺问为什么他自己钓鱼的时候还要鱼竿、鱼线呢?老人家说他现在才开始学,还处于初级阶段,等以后功夫到家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凭空钓鱼了。
俺很好奇,问他用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一共钓了多少条?老儿说他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一条鱼都没钓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