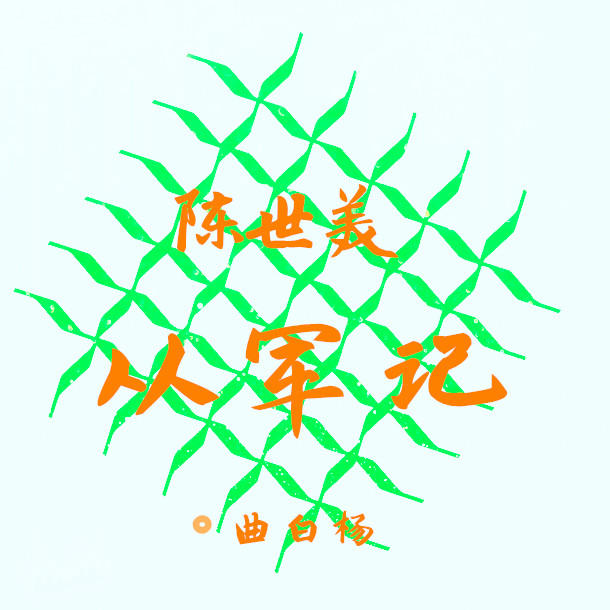沈昱宸生辰过后,不消几日就到了年关,这一年下半年的所有节日,都被沈昱宸以灾年为由全免了,这除夕宴却是不能免的,关系到来年的运势,须得慎重以待,隆重非常。
年下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除夕前两日,嘉宁殿中宋浩陵禀完了公务,问了一件与他不怎么相关的事儿,“帝君,有件事需要示意,除夕宴柳姑娘的位次该如何安排。”
“嗯?”沈昱宸略感意外,“这不是礼官的事么,怎么是你来问。”
宋浩陵笑道:“礼官如果真为这么件小事来请示帝君,按帝君的行事恐怕是直接撤职了,柳姑娘太特殊,名义上是宫里的琴师,按礼只能在外殿,可她又得帝君与长宁公主另眼相待,礼官也很为难,来的时候碰上了,就代为请示。”
“你怎么看。”沈昱宸随口问道。
“臣也为难。”
“那你为难吧。”
宋浩陵无语,他似乎不该好心帮忙啊,帮着帮着就帮到自己身上了,想归想,可也不敢怠慢,想了想道:“臣以为在风姑娘之下,百官家眷之上。柳姑娘的身份朝臣都已明了,并且她又是长宁公主的贵客,这样安排也不算过分。”
“嗯,那就这样吧。”
柳清持从外面进来,正好听到二人谈话,“这样安排不好,区区一个琴师怎配居此高位,我可不愿自寻烦恼。”
沈昱宸:“长宁公主的贵客,得此礼遇算不得过分。”
“随你吧,不过我向来不善应酬矫作,若是得罪了什么人,总之是你去权衡,可别来怨我。”
沈昱宸深深地望着她:“这个倒是不难,你想怎样便怎样。”
宋浩陵觉得自己该出去了,礼官还在等着他的回答。
“我送给你的画收到了?”沈昱宸问。
“我不知道你有这么清闲。”
“你不肯给我想要的贺礼也就算了,我给自己送了份礼,你也要冷嘲热讽。”他的目光紧紧地禁锢住她,语气似乎有些冷漠,她可以拒绝,可以说不,他都允许,但是她绝不能想要去控制他的心念。
柳清持被他眼中的冷厉震摄住了,强硬的话语也稍软了几分,转过身道:“随便你,你觉得是那就是吧。”
她命阮和送来的梅花插在青瓷胆瓶里,就摆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玉骨风姿,遗世独立,“你去看过梅花了,它长得还好吗,这个时候花应该全开了吧。”
他的声音有些苍凉,又有些怀念,她听在耳中心里蓦地一颤,几分悲恻染上心头,他的哀乐不能轻易示人,总是藏在心里,一个人慢慢在时光里消磨,久而久之,便如同此刻,浓郁凄凉,催动人心,她也被他感染而神色低沉,“人间绝境,你不去看看。”
沈昱宸微有怅然之色,“风仪宫冷清了许多年,少有人去,我也有好些年没去过了。”
“怎么会。”柳清持目含异色,风仪宫是他母亲生前居所,即便是再不得闲,也断不至于多年不踏足一步。
“既然你来了,那就陪我去看一看罢。”沈昱宸望向她,征询她的意见。
嘉宁殿离风仪宫不远,严冬风寒,一路的萧杀冷意直扑面而来,柳清持昨天已经走过了一回,倒也习惯。沈昱宸多年不曾踏足此处,看着似乎有些陌生了,“我记忆中的风仪宫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么冷,还有些许人声,早些年我很愿意往母后那里去,就算她已经不在了,我也能从那屋子里感受到她的气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来的少了,渐渐地不愿再踏足这里。有一年冬天元福在我面前提起梅花,我朝他发了好大的火,那是我唯一一次对他发怒,自此以后,风仪宫就再没人敢来了,这株梅花也再无人提起。”
两人缓慢走过白玉石阶,眼中逐渐开满繁花漫天,玉树琼枝,遗然于世。“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无数关于父皇母后的故事,总不过是情深似海,一世相依,我也曾认为真的是这样。”
柳清持看着他:“本来就是这样,你用不着怀疑。”竟还是因为她的母亲慕汐月,始终是他心上的一道不能愈合的伤口,可是慕汐月又有什么错呢,她得以如今的安稳,只是得幸于这世上有一个柳若尘。
“我从不怀疑,只是他们,你们都对我太过残忍。”他面色阴郁沉痛,似乎不愿去回想,“父皇身负顽疾,命里早逝已成定数,母后身体向来康健,在父皇走后弃我而去甘愿殉葬,终归是我在她心里不及父皇万一,我的名字是她所取,也只是为了让父皇心里少些负罪。”
他望着她忽然笑了,带着些莫名的冷嘲,“然而这都不算什么,十二岁以前,我至少能认为就算他们之间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其他人,至少我是他们的唯一,就算他们不在了,也依然还在我身边守护我,可是你却不该出现,更不该擅作主张将我带走,一夜之间,我忽然觉得我一无所有,我的父亲一辈子愧对那个人,我的母亲为了我的父亲甘愿把我变成那个人,就连你不也是为了这个名字才会留在这深宫。”当初她的一句“你不如他”让他日日夜夜都在与一个死人作斗争,何其残酷。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原本只是不愿你太过在意此事而深陷其中,反会害了你。”她低沉着声音,她没有料到当初有意为之的刻薄言语竟然会藏在他心里这么多年,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结。
“罢了,已经发生的事,多说无益,我如你们所愿一路走到今天,那么你也不要再妄图把握我的思想,”他忽而望着她的双眼,一贯温和的神情,“如果有一天我无法再压制心中的魔魇,那么这天下都要陪我一起颠倒。”
柳清持忽而觉得此刻他竟是如此的陌生又真实,像是忽然掀开了温文尔雅的面孔露出里面无尽的黑夜来,坚强冷硬,那漠然的气息似乎已经凝成了实质。井水无波空起寂,她望着里面倒映出他的颀长的身影,风骨卓绝,立于天地,一时竟难以移开双眼。便突然地这么静了下来,他望着一树繁花,涌动着难言的情绪,转头看她,望见井里美轮美奂的一幕,繁花开满天空,两人并肩而立,竟是如此的风华万千。
沈昱宸一只手探向她的耳后,柳清持猛然惊醒,匆忙偏头躲开护住蒙面的绣帕,望向他的眼中满是惊恐,此时的他,已非她所能掌握,如果他现在执意而为,她根本无法抵抗。沈昱宸只手停在半空顿了一顿,越过她伸向她脑后的梅枝,轻飘飘的折了一枝,“你竟然也会害怕,怕我,你不是一直都看这世事如尘埃,不管什么都入不了你的眼么,竟然也会怕我。”
他眼中的毫不掩饰的讽刺彻底将她激怒,抄过井沿上陈旧的花浇,舀了些水泼到他脸上,“清醒了没有,清醒了就回去,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柳清持寒着一双眼,转身就走,他望着她的毫不留情的背影,手中的梅枝掉落在水面,碎了一场旷世奇景。他亦转身离开,那一树繁花逐渐被留在身后。冬日的夜来的早,再过两日就是除夕,宫里到处是飘摇的红,柔和的红光照过他们走的每一步路,直到隔水亭畔,寒凉的冷风从湖面吹过,扯动两人的衣襟。
沈昱宸叫住她,“清持,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我当时在想,在那里看到你应该是最合适的地方,我原本只是想想,没想到真的做了出来,要怪只怪那梅花太妖异,容易乱人心志。”
柳清持没有回头,背对着他道:“我要回去了。”
言罢,便登舟离岸,在茫茫夜色里渐行渐远。
沈昱宸在隔水亭待了一会儿,便也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