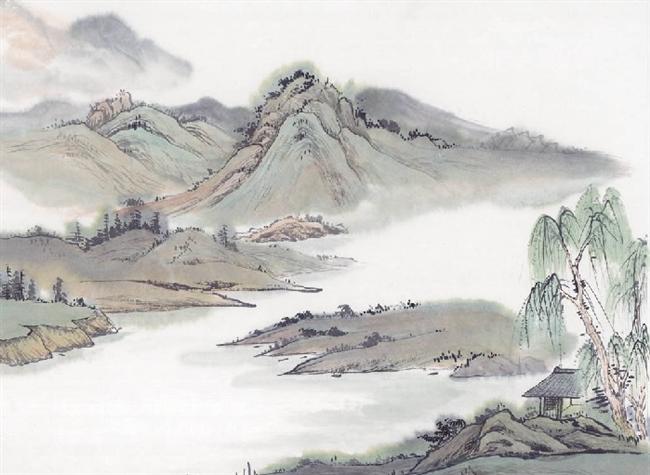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秋风过野之后,日子也就过的快了,日短夜长,风霜肃冷,满目的凋败景致,枯寂的气息笼的人也了无意兴,仿佛转眼就到了冬季。今年接连两受天灾的河双城经过四个月休整已恢复了不少,百姓得以安身,只需熬过这冬天,等到来年开春重新耕种土地,便算是度过了这道难关。
河双城驿馆的院子里,一个身着银灰色锦袍的年轻男子拆开了手中颇厚的书信,望着那熟悉的字迹,抱怨的口吻,不禁摇头笑了,一张张看过之后暖意浓浓,这凛冽寒风也退却了不少。
忽而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老者走来出言相戏谑:“看大公子这副神情,必定又是二公子又来信催促你回去了。”
“先生,”沈云岫恭敬一揖,随后将老人引进屋去,“咱们屋里坐。”
叶缙先生点头默许,对这学生也是非常受用,进了屋里,沈云岫命人上热茶,又点了个手炉放到老者手中,所做行云流水,一派自然。末了才道:“先生猜的不错,是怀稷来信,我这次出来的也算是久了。天气冷,还送了衣物过来,等会我差人给您送过去。”
叶老先生笑问:“嗯?二公子还有这个心?老夫倒是没料到,回去少不得夸赞两句。”他在祈王府任先生多年,对这两个学生甚为熟悉,沈云岫心思缜密,行事稳重,更为低调;二公子沈怀稷还是万事随心,少年心性,张扬得意。这两兄弟感情之佳,在京中那是赞声如潮,皆言祈王之福,连带着自己也是备受推崇。
沈云岫解释:“是王妃备下的,怀稷没有出过门,倒是想不到这一层。”
“原来如此,”叶老先生点头称是,又问,“城中诸事可都安顿好了。”
沈云岫道:“都安定下来了,多亏先生与李大夫医术卓绝才得以保住众人性命,下月初就动身回去了,年前可以赶回京都。只是李大夫多番推辞不愿回京封赏,也强求不得。”
“好。”叶老沉吟了一会儿,又望着弟子认真道,“老夫刚听闻石源又来驿馆了,那石源来了也有七八次,你当真不肯见他一面。”
沈云岫散了先前欢欣,移开眼暗淡一笑,“先生明白,又何必我多言,这石源我不能见。”
叶老慨然一叹,语重心长,“你这孩子向来懂事,心里头压着事儿也不与人说,这石源是你外祖父的属下,如今年事已高,想见旧主遗孤一面,也是人之常情,你几次三番拒他已是于心不忍,只怕你日后心中愧责难安,不若召他来就在这当着老夫的面见他一面,旁人也说不得什么,你看如何?”
沈云岫道:“先生一心为我着想是云岫之幸,只是人言可畏,我又怎敢连累先生,我的身份来此本就诸多不利,我也不想引人猜疑,也就作罢吧。”
叶老点头道:“你思虑周详,如此是最好,只是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别为此失了父子和气。”
“云岫明白。”
送走叶缙先生,沈云岫站在窗前望着院中枯树神色不明,来到母亲故土,却事事不由己,处处需谨慎,这恐怕是为人子最大了悲哀了。叶先生之计虽可行,他却不愿如此,担心传到祈王耳中令父王不快。这几年,沈云岫与祈王关系缓和了不少,也说不上有多好,总觉得父王对他没有以前那层隔阂了,两人相处虽淡,却也终于像是对父子了。于石源,也只能对不起这位忠仆了,非他无情无义,只是什么都不及父王来的重要。早命人传了话,心意收了,请老人回去,不必再来。
散漫着又过了几日,寒风凄紧,空气冰凉,是一日比一日冷了。眼看归期将近,沈云岫也就不再出门,每日只与与叶老先生围着火炉品茶下棋,不时也论些政事,过的倒也还惬意。这日近午时,天空乌压压的一片黑云,不多时就飘落了雪。
沈云岫朝院子里望了一眼,对叶老笑道:“下雪了,我们回去那几日也正是冷的时候,先生可要保重身体。”
叶老先生轻呷了口茶,“尽量护着这身老骨头,不让你挨骂,来来来,该你了。”
沈云岫怡然落下一子,叶老学富五车,这一手棋艺也丝毫不逊当朝国手,只可惜也是终身不愿出仕,只守着家中几间学堂度过了半生,晚年才应林孝言老先生之邀到祈王府教学。沈云岫经他教了也有十余年,这谋棋之术却总是输一着,此次也不例外,过了一个时辰已是落了下风。最后胜负分晓,又是输了半子。
一局过后,有个驿馆的门卫冒着风雪穿过院子进来了,手中捧着个布包,进门垂着脑袋跪地颤声道:“大公子,这是石老伯送过来的,说是从前顾王妃最爱吃的杞子糕,请大公子带回去代为拜祭,老人家也不容易,外头还下着雪呢,一路拿过来护在怀里还是热的,我们兄弟几个也是不忍心,请大公子收了吧。”
沈云岫霍然起身,大声问道:“他在哪?”
“石老伯留下这个就走了。”
“给我追回来!”
“啊?”那守卫一时不明,马上反应过来,生怕他反悔似的忙起身出去了,“是,小的这就去追回来。”
“先生您···”沈云岫回过头正待请叶老先回屋去休息,转过身却已见叶老靠着卧榻睡着了,轻微的鼾声,一如这沸腾的茶水悠远安详,沈云岫无言,也唯有在心里深深道了个谢。
这石源自称是沈云岫外祖父前梁庄王的下属,自庄王府败落了之后,就在城里开了个小酒馆聊以度日,沈云岫的身份自是人所众知,河双城官职有大半都还是前梁旧部所任,饶是如此,谁也不愿来趟这浑水。梁族是新帝心里的一根刺,一旦时机成熟,必定就要连根拔起,又有谁愿意去做这个出头鸟?
石源是个清瘦的老头儿,穿一身灰黑的旧衣,苍老的面容严肃冷漠,骨子却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刚强,见了故主遗孤,规规矩矩地矮身行了个大礼,“老奴见过小主人。”
沈云岫已经迅速冷静下来,听他这一句理智又占了上风,引他入座,和声道:“石老伯请坐,您对母亲的一片心意,我会带到,如今天冷,您也不必每日往这里跑,还是要多保重身体。”
石源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我这把老骨头算得了什么,只可惜了郡主年纪轻轻客死异乡,如此冤枉!”
沈云岫心中暗叹,自己真是冲动,对这石源也是又赞又叹,这直性子也不管自己身处何地,对母亲一家倒是忠诚,于是耐心解释:“母亲虽早逝,可她在祈王府过的很好,与我父王感情深厚,石老伯,您多心了。”
石源一双鹰眼落在他的脸上,锐利地如同刀割,冷笑一声道:“很好,如果真的好,又怎么会无端死去,郡主身体一向康健,便是生下小主人你也还平安过了一年,又怎么会在第二年就无缘无故的死了?”
提及母亲沈云岫心情低沉,母亲亡故府里少有人敢提起,怕的就是勾起他难过,想不到今日竟被这老者撕开来了,敬他忠心,却也无奈:“母亲生下我之后身体就不大见好,后来也是得急病而亡,与他人无关,死者已矣,生者犹存,老伯安心吧。”
“一派胡言!”老人起身恶狠狠地盯着他,一步步逼近,“郡主自小身体康健少有生病的时候,如果真是生子落下了病根,怎么不见有消息传回来,反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此事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分明是有人蓄意谋害,如果沈君翌那个奸邪小人真对郡主上心,又怎么就迫不及待地再迎新人。”
“够了,”沈云岫冷冷地起身,“你对我母亲一片赤诚在下敬佩,只是你不该出言辱我父王,更不该亵渎他们之间的感情,你走吧,我不会再见你。”
“小主人,你不能被仇人蒙蔽了双眼···”
“我不是你的主人,立刻离开!”沈云岫厉声相斥,怒上心来,他心中一直仰望着的父亲,和母亲那般美丽的传说,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污蔑。
“谁呀,这么吵吵闹闹,老头子觉都睡不安稳。”躺在榻上的叶老打了个哈欠徐徐起身,望着沈云岫寒着一张脸,满眼克制的怒意,头一回见徒儿这么失态,不禁出声笑了,“云岫啊,奕棋者最忌心浮气躁,被他人左右了心思,老夫教了你那么些年,每每棋差一着,就输在这上面了,老夫罚你回房禁足一日,服是不服。”
沈云岫不动分毫,面色冰寒,连向来尊敬的先生也一并无视了。叶老倒也不怪,走到两人中间,温声调解,“石老弟以前是庄王府上的人,云岫,说来还是你的长辈,庄王府败落已久,树倒猢狲散,难为石老弟还这么念旧情,这是你母家的福分,不得无礼。”
沈云岫气息都乱了,正在气头上哪里还听得进去,要不是看他与母亲渊源颇深极力克制,不然早就出手将他打了出去,哪里还会这么客气!当下冷冷道:“我今日不宜见客,请先生立刻安排人送他回去,云岫谢过了。”
石源怨愤至极地望着多日来心心念念要见的小主人,凄惨大笑,一双老眼也浑浊了不少,指着沈云岫怒斥:“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你当真知道祈王是怎样对待郡主的吗,你娘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啊!”反手就推开了前来押他的守卫,厉声大喝:“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走,来错了,我来错了啊!”
沈云岫心中大骇,扶着椅子站定,他对父母之间的情意深信不疑,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斥责父王对不起母亲,其间所带来的冲击是无法想象的沉重。
“云岫!”叶老连忙将他扶住坐下,深知今日之事对他影响之深,眼中也划过了几丝忧虑,出言开解,“当年的祈王与顾王妃乃是京都的一对璧人,别的不说,就单单是祈王当众亲笔所题‘倾澜微雨’的那块牌匾就一度传为佳话,至今都让人艳羡不已,还有种种情状,我这个老头子都耳闻过不少,你不可为这些无稽之谈乱了心神。”
沈云岫只手揉着眉心,满面倦累,“先生,这几日事完了,咱们就回去吧,不等到下个月了。”
“好,好,早些回去也好。”
叶老先生差人送他回房休息,心中又是重重一叹,到底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没经历过风浪。又不禁暗恨这石源也是个疯子,三两句话把人害成什么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