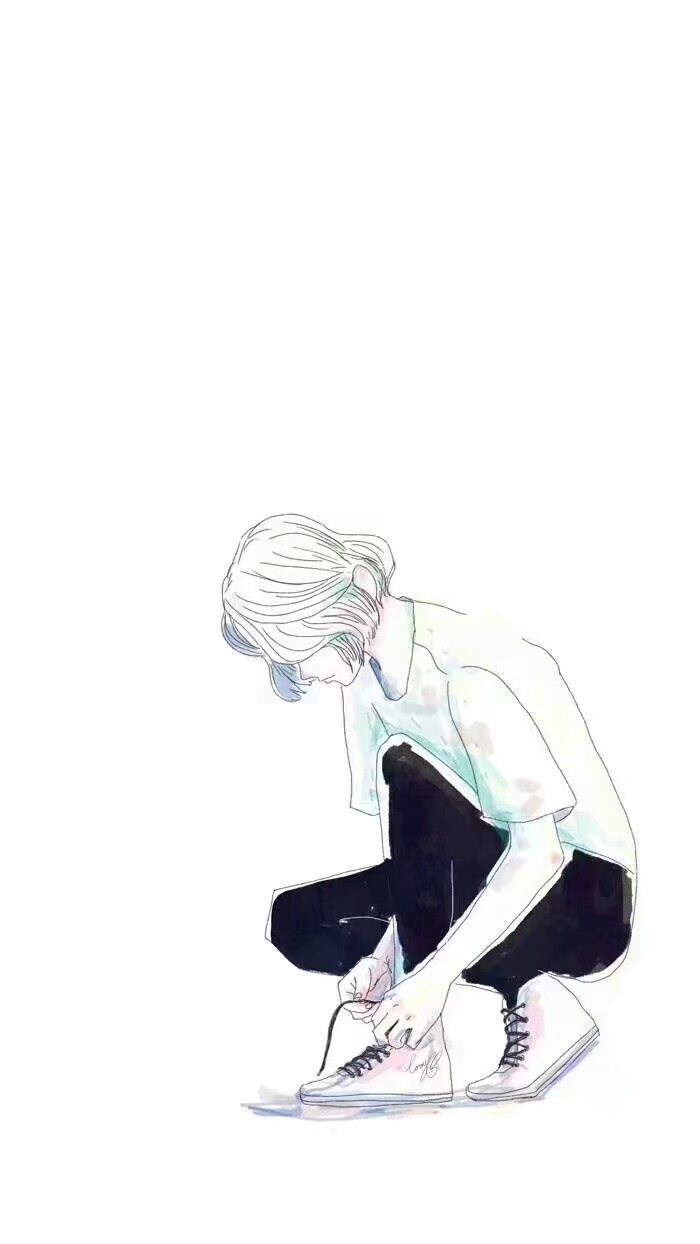却说夏言下了朝之后,回到了家里,依旧像平常一样行事,该吃吃该喝喝,偶尔读些野史怪谈哈哈一笑,根本不把严嵩的弹劾放在心上。
因为在夏言看来,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而降罪。
夏言这时正在练字,“清正廉洁”四个正楷写的是气魄非凡,凛然大气,毫无半分歪斜。
可是这时,一个丫鬟急匆匆地跑来道:“老爷不好了,夫人要寻死!”
“啊!”夏言大惊,赶紧跑去妻苏氏的房中,只见一群丫鬟抱着苏氏道:“夫人,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
苏氏手里拿着剪子痛哭道:“现如今朝廷传言我家之事,害了大人,我不如以死明志,换得一身清白!”
“夫人快快放下剪子啊!”夏言道:“此事与夫人无关的。”
苏氏见夏言来了,立即跪倒在地道:“老爷,请为妾身做主啊!”
夏言扶起苏氏道:“有事起来说话,不要这样,哭哭啼啼的不好。”
苏氏抹了抹眼泪道:“市井上都传闻家父收受严嵩的贿赂,趁机坑害老爷,可是家父并没有这么做啊,请大人明察!”
“岳丈大人的为人为夫的当然清楚。”夏言搂着苏氏坐到了床上道:“夫人不必忧虑,更不要听信那些流言,等圣上查明了真相,自然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的。”
“唉。”苏氏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也不知道卿儿怎么样了,在玉虚宫住的还好吗?如果他能回来,也好助老爷一臂之力啊。”
夏言此人十分清廉,吃穿用度向来节俭,家室也非常简单,不过一妻一妾而已。
十六年前,苏氏生下了一个男孩,样貌十分的可爱,如同粉琢玉雕的一般,谁人看了都无比的欢喜。
夏言给儿子取名为夏真卿,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唐朝的颜真卿一样,以后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却说有一日,夏言带着一家老小在街上游玩,忽然碰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士,他一眼看去,就说出了夏真卿的生辰年月,一丝都不差。
夏言很是惊讶,他作揖道:“请问这位仙长,我儿的面相如何?”
“不好。”老道士摇了摇头道:“此子虽然俊美非常,但是他的命相不吉,他出生之时恰好遭逢丙火墓戌,恐怕很难活过十六岁。”
“那请问道长可有办法解救一二?”苏氏着急地问道:“若是道长能让我儿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我愿为道长重修庙宇。”
“重修庙宇就罢了,施主只要把此子交由贫道抚养,然后每年五月五日给关帝君送上一壶酒就可以了。”老道士微微一笑道:“此次若是能脱难,那以后必将显赫非凡,平平淡淡是不可能了,不过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夏言道:“敢问仙长道号为何?庙宇在哪里?我们有空也好去拜见仙长。”
“贫道昆仑山玉虚宫极一道人。”极一道人一抖拂尘,把夏真卿揽在怀里道:“十六年后,贫道便会让你们一家人团聚的。”
夏言和苏氏都不舍地看向夏真卿,唯恐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极一道人似是感应到了他们的目光,于是回头道:“贫道还有一句话要告诉夏大人。”
夏言问道:“请问仙长还有何事指教?”
“莫做屈子渔翁对,秋风直忆江东行。”极一道人道:“贫道言尽于此,告退!”说罢,转身离去,其余人等无论如何也都找不到那道人的身影了。
“如今已有一十六年。”夏言捋着胡须道:“也不知卿儿是不是该回来了,或许他正在路上也未可知。”
夫妇二人正在怀念夏真卿,外面忽然有人来禀告道:“大人,东厂的曹公公求见。”
“我知道了。”夏言一挥手道:“让他去客厅等我,我马上就到。”
下人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苏氏问道:“这曹公公与我们并无交情,他来作甚?”
“我看他是来调查事情的。”夏言整了整衣冠道:“无妨,我今日就去会会他,看他能查出什么东西来。”
夏言到了大厅,一拱手道:“曹公公今日怎么有空来到寒舍做客?”
“瞧夏大人说的,我们这些做奴才的,哪里有空?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上面只要张张嘴,我们就得跑断腿啊!”曹公公谄媚地笑道:“咋家今日前来,不是为了他事,而是因为军饷一案而来,还望夏大人不要怪罪咋家,咋家也只是替人跑腿的而已。”
“曹公公所言我都知晓。”夏言不苟言笑地道:“请曹公公随便调查,有何事尽管说。”
“咋家不敢谈论调查一事,只是随便来看看。”曹公公道:“还请夏大人多行方便。”
“这个好说。”夏言道:“来人啊。”
一个下人走了过来道:“老爷有何吩咐?”
“以后府中各地,曹公公都可以随便来往。”夏言嘱咐道:“若是有问话,尽管一一照实回答,不要遮掩。”
那下人点了点头道:“是的老爷。”
那曹公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因为按道理来说,一般的官员听他说出了多行方便四个字,那都是把大把大把的银子递给他,央求他替自己美言几句,可没想到这个夏言如此的顽固不化。
他随即一甩袖子道:“既然夏大人这么说了,那咋家可就要好好彻查一番了!”
而在严嵩那一边,也是一个东厂的太监去查案,这个太监姓魏,也是东厂里有名的贪财鬼。
严嵩听闻他来了,赶紧大摆筵席。
那排场唯有一句诗可以形容: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临了严嵩还给那魏公公送了一盒糕点道:“此物乃是扬州的特产,入口既化,酥脆非常,还请魏公公笑纳。”
魏公公用指甲轻轻挑开了封皮,借着烛光,看到里面塞得满满的银票,老脸上的皱纹笑的都挤在一起了道:“咋家多谢严大学士的美意了。”
严嵩赔笑道:“那我上奏的奏折……”
“完全没问题。”魏公公打包票道:“严大学士上奏给圣上的奏折,没有一个是错的!”
魏公公回到了东厂,跟刘公公、张公公一会面道:“二位去驸马都尉和锦衣都督那里,看来赚了不少啊。”
“哪里哪里。”刘公公道:“崔元那个小气鬼,怎么能跟严大学士相比?咋家只是略微得了一点恩惠罢了。”
“却不知曹公公那里怎么样。”张公公道:“这都大半夜了,还不回来,许不是出事了?”
说着话,曹公公从远处走了过来,口中连道:“晦气。”
张公公问道:“曹公公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曹公公长叹一声道:“那个夏言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咋家来回暗示他许多次,他就是不拿银子出来。”
说到这里,曹公公看了看三人道:“想必大家得了不少吧?”
“可不是?”魏公公道:“我这一次,少说也有五万两。”
其余三人表示非常羡慕,而曹公公更是有些嫉妒,别人都有银钱拿,而他竟然一分钱都没到手!越想越是气愤不已。
魏公公看出了曹公公的心思,于是对他道:“既然那个夏言如此不识好歹,依咋家所见,不如我们联合弹劾他,让他吃一吃苦头!”
曹公公闻言点头道:“好,就让他尝一尝小觑咋家的后果!”
这四个太监去了万寿宫,觐见嘉靖皇帝,陶仲文的两个侍童进去汇报,嘉靖皇帝道:“进来。”
这四太监才走进来,跪拜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嘉靖皇帝道:“朕让你们调查的事可有结果?”
魏公公四下看了看道:“此事恐怕有些不方便说。”
站在一边的陶仲文一挥手,他的两个侍童会意,关上门,退下了。
魏公公这才道:“据老奴观察,严大学士并无任何问题。”
刘公公和张公公也都帮崔元和陆柄开脱。
嘉靖皇帝顿时明白了,怒斥道:“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奴才,莫非是说夏爱卿有问题?”
这四个太监吓得连呼“该死。”还是魏公公老成一些,稳住了心神道:“老奴自知罪该万死,可是事实如此,老奴也不敢妄言啊!”
曹公公也道:“魏公公所言不错啊,我曾听夏府的下人说过,那曾铣确实来过,而且极为神秘。”
“不可能。”嘉靖皇帝还是不相信:“夏爱卿乃是三朝老臣,不会做出这等事。”
“圣上仁心仁德是好,可也容易被别人所欺瞒,要知道那夏大人早已对圣上不满了。”魏公公伏地叩首道:“老奴斗胆进言,还望圣上明察啊!”
嘉靖皇帝冷哼一声道:“你若说不出他有丝毫的不敬,我就要你们四个人的脑袋?”
曹公公道:“圣上可还记得当年曾制造沉水香冠五顶赠与夏大人和严大人之事吗?”
嘉靖皇帝点头道:“自然知晓。”
“奴才去夏大人府邸查访之时,发现那沉水香冠不过放在一旁,都积满了灰尘。”曹公公道:“很明显,这就是对圣上的大不敬啊!”
“而反观严大学士,却用轻纱罩住,勿令其有丝毫损坏。”魏公公道:“由此看来,这夏大人比不上严大人忠心。”
嘉靖此时也有些被说动了,正所谓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自古以来便是人言可畏,就连曾子的母亲在把话听了三遍,也担忧自己的孩子去杀人,不得已逃命去,可见这谣言有多么的可怕。
更何况嘉靖皇帝对夏言本来就有一些敬畏,敬畏之余更是想摆脱他,于是嘉靖皇帝迟疑。
就这么一迟疑,让那四个太监看到了希望,准备再加把劲,彻底把夏言告倒。
可就在此事,外面忽然传来了惊慌的声音:“不好了不好了!西宫走水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