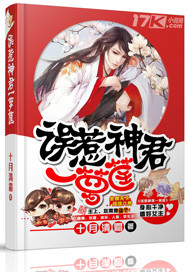这人竟叫柳英俊为少主,又称自己是金一。金一是谁?这个问题问一万个人,可能没一个知道,但问李有财,他听了一定会愤怒的蹦起来。
金一是李有财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名字,李有财的生杀仇人,李有财唯一记住的一个名字。三年前就在离此地不远的李府上,杀害了李有财的父母兄长。
李有财恨,恨透了金一,每天在梦中,李有财都会回到那个夜里,还有蒙着面的金一,他那可怕的话语。他恨,更恨透了自己,恨自己软弱无能、苟且偷生,透露了父亲守护的秘密。
他苦练三年功夫,付出了常人几十倍的努力。为的就是复仇!而金一这个名字只是复仇的开始。
可讽刺的是李有财就连金一的衣衫都没碰到,他已被人像条腊肠一样,挂在肩上。
金一扶起柳英俊,而那扛着李有财的大汉走过来,一把接起柳英俊。金一转过身,对柳伤琴说道:“我家少主对姑娘是一片丹心,所以还请姑娘与我们一起去做客去。”
这虽然是在询问柳伤琴的意见,但这样的情况下,柳伤琴就算反对也根本没有作用。
柳伤琴没有回答,紧紧的抓住了同样颤抖的小青的手。
金一又道:“姑娘别怕,我们只是请你做一回客。”闪身到两女跟前,他的身法竟让人完全看不清,又是几手连点,两女被点上了穴道。他又道:“还请公子来将两位小姐带出去。”他这话是对着孙稽说的。
孙稽一笑道:“金老兄真是甚懂我心,将这美差交与我。”说罢一左一右,两手将两女抱了起来。
两女惊慌失措的看着他,慌张的程度甚至高于看到那大汉扛着昏迷的李有财。因为孙稽的手一过来就在她们的屁股上一扭。
金一看着孙稽将两女带了出去,眼中饱含笑意。
两女被孙稽托着走,再观客栈内外,竟连一个人也见不到。出了客栈,外头有两顶等候许久的大红轿子,两女被孙稽抱进了一顶轿子里。
轿子很宽舒,座上还铺着雪白的毛毯,摸上去十分柔软,一看就是十分珍贵的料子。轿夫抬起了轿子,直到风吹起了轿子的帘,两女才发现已在赶路了。轿夫的功底非常好,赶起路来如履平地。但两女却无心关心这些,他们此刻的心情,就好像挂在悬崖边的人,突然有了饱腹的食物,却毫无用处。
也不知在这样忐忑的挣扎中过了多久,轿子才停下来。
孙稽又将两女抱出,柳伤琴于小青瞧见眼前的光景,目瞪口呆。
他们此刻竟然身处一个巨大的洞内,这是一个巨大的朝天洞。他们正站在洞的底端,四周的洞壁上爬满了植物,而在这口大洞的正中央是一片巨大的水潭,正是因为这一片水潭,四周的景色仿佛活了过来。
月色照进水潭,水潭再反射月光,将这个大洞照的亮堂堂的。月色印在墙上,随着水波粼粼晃动,壁上的植物也好似活了过来,正在用跳舞庆祝这唯美的月色,整个洞内处处显出神秘之感。
在山壁上还有一个洞,这个洞壁口圆滑光整,不是自然形成的。但从远处看,这个洞仿佛不存在。孙稽抱着两女走近了洞,两女才发现这儿原来还有一个洞。众人有序的进了此洞,洞道笔直,没走几步路却看到几个房间。
为什么是房间?
因为在通道内有一个个开着口子的门,门内居然有湖面反射的月光,月光打在里头,将整个空间照亮。柳伤琴看到,里头不仅有床,还有还有梳妆的台子,在台子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胭脂水粉。
不单单只是一个房间,而是每一个看到的房间内都是一样的构造,一样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但房内却没有人,每一个房间也都是空着的。
直到两旁看不到房间,柳伤琴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台子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台子,在台子对面,竟然是一面陡峭的山壁,而两侧却黑的可怕。
台子的左侧有一排向上延伸的阶梯,阶梯的尽头也开在山壁上。
这个阶梯的外侧没有扶手,从上往下望去,一片漆黑。似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张大了口,随时等待掉落的猎物。柳伤琴往下瞧了一眼就不敢再瞧,将双目紧闭。
孙稽却闲庭信步,一下走上了台子。转进洞中,这又是一条有些长得通道,而在通道两端的墙上是挂着火把,火把将通道照的透亮。这儿每隔几丈也有两间房,只是这里的房门紧闭,而且从中竟不断发出男女欢愉的声响。
整个通道内尽是春意。
这里延绵的房间内居然尽是男女欢愉之声,彻彻底底就是一个偷盗的场所。
小青与柳伤琴都是处子,直听的满脸通红。孙稽瞧见她们的模样,又用力的捏了一下她们的身子,微笑道:“若你们不是客人,我也进房间让你们也快乐快乐。”他说完便一直盯着柳伤琴通红的面庞,哪里还有先前那副气宇轩昂的模样。
英雄难过美人关。这话也不是白说的。
孙稽又道:“李有财这小子运气真是不错,身边竟有两位倾国倾城的佳人。”他话中的两位佳人当然没有小青,而是指戚苦儿与柳伤琴。
突然前头有人道:“哟,这不是公子吗,你说好今晚要来找我的。”
这声音妩媚至极,男人通常对这样的声音都无法抗拒,尤其是当这个声音是从一个穿的半遮半掩,身材高挑性感,相貌较好的女子口中说出的。
而眼前这个说话的女子,恰恰就是这样。
在这女子的身旁,还有一大群涌上来的女子。这些女子竟每一个都是称的上“美女”的人,她们一个个挤眉弄眼的对着孙稽。就好像孙稽反而是一个美女,而这些女子都是追求者一般。
孙稽被这群女的堵在洞口,前进不得。后头的男人跟上来,有些女的就找后头的男人这样去做。
柳伤琴看见,最先和孙稽搭话的女子又去找身后的男人了,而且说得话竟然也一模一样。
难道女人就应该这么作践自己?就应该丢了自己的尊严,去一用自己去勾引男人吗?柳伤琴留下了泪水,她的泪是为这些一个个犹如躯壳般的女子而流。为这些只能成为男人工具的女子所流。
孙稽瞧在眼里,他道:“你觉得她们很可怜?”
柳伤琴自然无法回答他。
“但是她们自己却觉得很快乐。”
柳伤琴无法理解,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快乐?
孙稽好像看破了她的心,又道:“她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培训,学习如何让男人舒服,如何让男人快乐,而她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男人享受。在她们自己的心中,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孙稽又道:“她们都在为自己的存在的意义而活,所以她们都很快乐。你说是吗?”她明知柳伤琴无法回答,但还是这么一问。
柳伤琴的泪水却止住,她双眼通红的瞪着孙稽。心中有如万马奔腾,她想“世上本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被迫做这样的事还能开心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以作践自己为荣,因作贱自己而乐的。”
试问又有谁愿意这样做呢?许多女性不断的出卖自己身体,她们难道是真的喜欢这样做才做的?
不!她们只是为了生存。在这残酷无道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用这自己仅有的资本,来换取生存的条件。
就连孙稽也不知道的是,告诉他这些的人欺骗了他。这些女人一点也不快乐,一点也不!只是她们不得已,才必须要这样。
她们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了这里,接受的一切教育与讯息,都是关于取悦男人。她们每隔五年,也就是说当她们五岁,十岁,十五岁时……都要进行筛选。达不到规定的人,就要被淘汰。
什么是被淘汰?在她们的字典里,淘汰的意译就是死!“死”这一个字而已。
在没有实际尝试前,女孩们对这些事还总是兴致勃勃,而当她们真的开始尝试时,她们才开始厌恶了,极度的厌恶。那些满脸胡须,身上散发着浓烈体臭的男人,总是竟乎疯狂的索取自己的一切,每一次做完,都会让她们觉得恶心,恶心到能呕出血。
但是她们不能将这厌恶的情绪表现出来,将这样的情绪表现在男人的面前。每三个月,她们都会进行一次筛选,筛选方法很简单,就是将接客最少的一个人淘汰掉。
所以她们竟乎用处自己的一切,来勾引任何到这里的男人。没有余地,只有不断的勾引,不断的和男人上床,她们才能活下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
她们也不是没有想过逃跑,只是每一个逃跑女子,最后都会被抓回,并在众人眼前,不断的被烧的发红的铁块烙在身上的每一块肌肤,从脚不断向上,直到被活活折磨致死。
她们别无选择,为了活下去。而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就是死,也只有死才能解脱。但谁又会想死呢?她们依然活着,女人们都为了有一天能离开这美丽的月坛,去外头的世界瞧上一眼而活着。
她们不愿承认的是,这些终归是无法实现的。能见到外头世界的,只有她们的尸体。
就在柳伤琴伤感之时,柔软话语漫天的通道内,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一个让柳伤琴看了说不出感觉的男人,无论是他的外表,他的年龄,还是给人的印象,都叫人说不清。这是一个扔到人群里就一定找不出的男子,这是让人分不出年龄的男人。
他的眼睛明亮又饱含光泽,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才会有的眼睛。但他眼角一条条细细的皱纹,仿佛在告诉别人他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者。他的嘴,鲜红的嘴唇,象征着年轻与活力。但他嘴角微微上扬的笑容,好像在告诫着这周围,自己是一个异常危险诡诈的人。他的鼻子高挺,又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刚毅不屈的男人。
种种矛盾的感觉都能从这个男人的脸上体现出来。所以任何人瞧上他的第一眼,都会觉得是一种说不出感觉。当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时,往往让他人能牢记。而一个人身上的特点太多时,反而会让人不好记,尤其是这些特点还是比较矛盾的时候。
而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同于眼前的女子,她穿的很多,几乎将自己所有能遮的地方都遮起来了。甚至连自己的脸也用紫色面纱遮了起来,只露出一对眼睛。
可是只从她的眼睛就能看出,面纱下的面容一定风华绝代。
两人一出现在通道内,所有的女子竟都安静了下来。
孙稽却知道,这些女子都是因为眼前这个紫纱美人而静下来的。因为这个紫纱美人是这儿的首领。在这里,没有女人敢不尊她的话语。也没有女人见到她还敢说话。那“女人们很快乐”的故事,也是这位紫纱美人与孙稽说的。
紫纱美人没有名字,洞里所有的女子都唤她为“梅娘”。所以来这里的主顾也皆称其“梅娘。”
女人们慌张却有秩序的站在通道两端,身子使劲往墙上贴,就好像要与墙壁融为一体。梅娘与男子走在女人们让出的通道中,突然一小阵微风从洞内吹过,梅娘身前一位女子的绸带飘到了她的身上。
那穿着绸缎的女子突然全身发抖,表情抽搐。她立马跪下身,趴在地上说颤抖的求饶着:“梅娘饶命,梅娘饶命,女儿知错了。”
“你知错了?”
“女儿知错了。”
“你何错之有?”
女子惊惶之下,嘴上如同打了结:“女儿肮脏的衣衫,碰了梅娘的身子,女儿错了。”
“很好,你知错就好。”梅娘一边说话,左手悄无声息的拍出。这一掌打得很慢,很慢。慢到周围的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的手掌上。但就连柳伤琴也看得出,这慢的出奇的掌力,也能将那女子的脑袋打的粉碎。
就在这掌快要打到女子头上时,一只手也悄无声息的在梅娘的手腕上一抓。
梅娘的掌竟被抓在半空,打不下去。
“你要救她?”梅娘质问道。
竟是身旁的男子出的手,男子嘴角的微笑更浓了,他说:“我知道,没人能逃过梅娘你的处罚,但你这样就要了她的性命也太暴遣天物了些。”
“那你是什么意思?”
“不知梅娘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来处罚她?”
梅娘冷哼一声,收回了手,说道:“黄莺,你的性命就交给司徒先生了。”
男子道:“那还多谢梅娘。”转过首,对着仍跪在地上的女子道:“你叫黄莺是吗?”
女子抬起脸,她的脸上都是泪水与鼻水,显然吓得不轻。她颤颤巍巍的道:“女儿是黄莺。”
男子道:“黄莺你先跟着我。”
黄莺点头,起身,小心翼翼的跟在男子的身后。
梅娘与男子走到孙稽面前,男子道:“这一趟劳烦孙小友了。”
孙稽道:“司徒先生客气了,我这一趟去什么力也没出上,只做了一回轿夫。”
“哦,没想到这么轻松?”
“李有财这小子在藏剑山庄时机灵的要紧,可今夜遇到他时,却笨的要紧,简直是手到擒来。”
男子眼光向后一瞥,瞧见了挂在那大汉身上的李有财,突然笑了起来,对孙稽道:“还请公子随我和梅娘来。”
四周的女子仍一个劲的往墙上贴,梅娘在前头带路,众人跟在身后。
柳伤琴发现,这一条通道甚长。更关键的时,贴在壁上的女子竟一直延伸到洞尾,甚至走出了通道,来到一块大台子上时,还有许多风姿卓韵的女子。
这个台子是开在山壁上的。但这个台子不小,反而很大,大到可以站下几百人。在台子外,空旷无际,偶尔有点点火光出现。下面竟是一片空旷平原,这是眺望过去的光景。另有水泻银幕,打在空中,犹如薄丝缎子,在微风中飘荡。
台子的边上,有十几个侍女,与几张竹椅子。
梅娘坐到了当中的一张大竹椅上,椅上有一块白虎皮。
孙稽放下两女,让两女坐在两张竹椅上。
男子的座椅比较特殊,他身下的应该算不上是椅子,而是由三个侍女跪在地上,拼成的“椅子”。
孙稽也同样在这样的一个“椅子”上坐下了。
金一、余汉阳与那大汉却在一旁站着,闭口不言。
柳英俊则躺在了十几个女人用身子搭成的床上。男子看过了他身上的穴道,也是束手无策。
而李有财呢?
李有财平躺在地上,头被黄莺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梅娘坐到位子上后,眼睛一直盯着柳伤琴。这是一种火热的眼神,这样的眼神通常只有在男人看到女人的时候才会出现。
梅娘道:“司徒先生,你带这两个女子来,可是要赠与我?”
小青与柳伤琴一听身上直冒冷汗,眼睛也张的大大的。男子看了两女一眼,笑道:“还让梅娘误会了,这位美若天仙的柳姑娘是我们少主的妻子。”
梅娘手指着柳英俊,奇道:“他就是郭松仁的儿子?”
“正是,所以还请梅娘有多担待。”
梅娘怒道:“可你知道这里从来都只有男人才能进出。”
“在下正是知道,才与梅娘说了少主的事。”
梅娘道:“那你可知道,坏了规矩,就要有所补偿。”
男子道:“在下自然知道。”
从怀里取出一个方盒,交到梅娘手上。
梅娘打开了方盒,方盒中竟盛放着一颗珍珠。一颗璀璨照人,能让所有女人尖叫,甚至疯狂至极的珍珠。这颗珍珠晶莹
剔透,从珍珠心里缓缓透出色晕,看起来是这么的诱人。
就连柳伤琴与小青,看到这颗珍珠后,都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一双眼睛紧紧的盯着。周围的女子更不用说,喜好珠宝玉器,是女人的天性,他们一个个眼睛长得大大的,好像恨不得眼珠子能滚出来。
可是梅娘呢?
她淡淡的看来一眼珍珠,又将方盒盖上了。
她竟然一连点点的反应都没有。男子微笑道:“不知梅娘还满意吗?”
梅娘点了点头道:“好。”
男子笑了,这一次是咧开了嘴的笑。他站起身,走到柳伤琴两女面前,道:“柳姑娘与小青姑娘,在下司徒江,向两位问好了。”
小青道:“你怎知道我们的名字?”
“几位的行踪,我们在两日前就已掌握了。这次请几位来,并无恶意。”
柳伤琴道:“那你放我们走。”
司徒江道:“柳姑娘说笑了,姑娘可是我们未来的盟主夫人,何言‘放’字。”
“那我们现在就要走。”柳伤琴拉着小青站起了身,两女又架起了昏晕过去的李有财。司徒江也不阻拦,看着他们走到洞口。
洞口却被两个侍女拦住了。柳伤琴转过身:“你这又是何意?”
司徒江笑了,这又是另外一种笑,笑容中带着调戏的意味。他说:“在下的确不敢阻拦姑娘,可梅娘没说不敢。”
他又道:“在下斗胆问一句,姑娘可愿嫁给我们少主?”
柳伤琴瞧着柳英俊,垂下了头。在她的心中,与柳英俊是一种兄妹的情感。就算柳英俊欺骗了他十几年,就算他砍下了胖子的手臂,她都没有怨他。
但柳伤琴却心有所属,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心中的选择。
柳伤琴毅然道:“不,我这辈子除了李有财不嫁。”
司徒江笑了,梅娘也笑了,金一等人也笑了,甚至台子上所有的人都笑了。
他们为什么要笑?因为有可笑的事才会笑。
可这有什么可笑的?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柳伤琴都是一个痴人说梦,不自量力的弱女子。
这自然很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