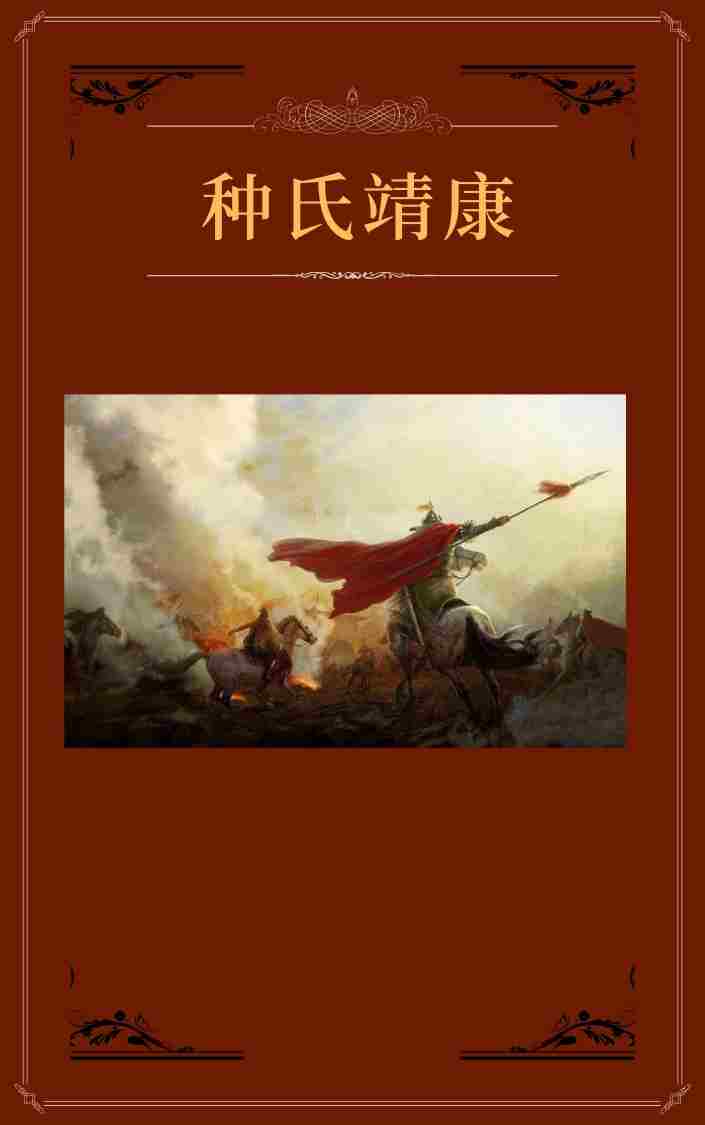昨夜混战,驿所后院的马厩倒塌,群马或死或逃。蛇怪偷袭之初,卧倒而眠的军马大半都被蛇怪咬死,剩下二十几匹警觉性高的军马聚在一起,逃过一劫。
后来马厩又被六神撞塌,场面混乱不堪,又伤了十多匹,幸运的军马惊慌失措,从北门裂口奔逃而去。
这些逃出去的骏马又被天命教道法抓住两匹,最后才救得道相脱困。
在剩下不到十匹骏马穿过后院林子,三三两两组成一队,各奔前程去了。
越吴道两边皆是延绵起伏的山梁沟壑,其间树林密布,雾霭沉沉,如今朝阳初升,已是辰时,只听驰道左侧的林子中忽的传出两声马嘶,一晃便奔出两匹骏马,跑在前边的骏马浑身通红,只有背鬃和马尾乌黑,却是一匹上好的赤骝马,而跟在后面的却是一匹马嘴乌黑,浑身土黄的黑骊马。
赤骝马跑到道中,停了下来,拨拉着尖耳,对着黑骊马不住嘶鸣,像似要和黑骊马分道而行。
黑骊马跑到近前,打着响鼻,用后踢不住轻踢着赤骝马的后臀,却是在表示友好。
赤骝马不再动作,静静地立在驰道边,望向远方。
忽的赤骝马一声欢嘶,撒开马腿,向前急奔而去,黑骊马见状,跟在后面,低头狂追。
“好家伙,你命还真大啊,昨夜那般混乱都不曾伤到你,怎么后边还跟着一匹?”
驰道远处,渐渐显出一人一马,一位身材高大的灰衣人手中牵着一匹黑马向两马迎了过来。
赤骝马跑到近前,不住轻轻用马首蹭着灰衣人的前胸。
黑骊马在旁警惕地盯着灰衣人,像似在哪里见过般,不住摇头回想。忽的黑骊马喷了个响鼻,渐渐放松警惕,它终于想起了灰衣人的身份。
这灰衣人便是刘云清,刘云清早先一身青装,在与蛇怪混战之时变的破烂不堪,便借了周德一身灰衣,难怪黑骊马一时认不得刘云清。而赤骝马一路与刘云清行来,对刘云清身上的气味早已熟悉非常。
“这匹黑马后踢被蛇怪所伤,勉强跑了两里,如今伤势渐重,再也驮不了人了,你这家伙可出现的真及时啊。”刘云清轻轻抚摸赤骝马的背鬃,心情自是十分欣喜。
刘云清早先与易云商讨完后,众人权衡利弊,做出一套计划。
刘云清不禁回想起易云的话,闽牧州与越牧州所尊有别,越牧州盛兴释教,而闽牧州却独尊道教,天命教徒夺得天工牌,定会去闽牧州九仙山祭祖,因为天命教创教始祖天易真人的诞辰便是三月二十三日。
如今已是初四,若不赶在三月二十三到达九仙山,到时祭典一完,他们便会北上天命教总坛真武山,到那时便算易云也无能无力了,毕竟天命教首座刑天也是不弱于易云的当世宗师啊。
刘云清正愁无坐骑可骑,若是这般走到下个驿所,却也要一日的时间,如今时间对于刘云清十分重要。
周德一大早便和易云南下越牧州,周德驿所属于越牧州统辖,这件事已造成五十多人的死亡,周德当然要将此事上报州兵府,然后转报帝都兵部等待审批。
而易云受佛光所邀,却是先下越牧州,等私事一了,便会和刘云清在闽牧州汇合,一切都要等到三月二十三日再说了,也只有这个机会可以夺回天工牌。
半个月时间道相与道法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回真武山的,天命教教义严苛,祭典对于每一个天命教徒都极其重要,是故他们会寻最近的分坛,祭拜祖先。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刘云清想了很多,却是愈想愈乱,当下摇了摇头,如今只有赶到闽牧州在议了。
刘云清将身后受伤的黑马马具卸下,将其放回林中,这般情况也只有任其自生自灭。
刘云清跨上赤骝马,将腰刀挂在腰际,大喝一声,向前驰去。
“得得”“得得”刘云清眉头一皱,向后望去,怎么那匹黑骊马却是紧紧跟在自己身后,刘云清见赤骝马忽的停下,对着自己不断嘶鸣,当下心中了然。
如今混乱已过,马儿也是向往自由的,却是自己疏忽了,刘云清跳下马来,将停在近前的黑骊马的马具一并卸下,拍了拍马臀,见黑骊马渐渐走远,这才又跳上马来,向前疾驰而去。
“得得”“得得”黑骊马又不远不近的跟在了刘云清身后,刘云清心中不解:“这马儿却是奇怪,卸了马具,如今已是自由之身,再也不用受先前束缚,却为何还是跟在身后。”
刘云清又赶了两次,见黑骊马仍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又见赤骝马不住对着自己喷着响鼻,像似在阻止自己自己驱赶般,当下心中暗笑:“这两个家伙却是在昨夜蛇怪之灾中共患难过的,不会是也与自己和周德般成为至交了吧。”想到这里刘云清忽的哈哈大笑,不再理会身后黑骊马。
如今辰时近消,要赶在晌午到达驿所,好马儿,快跑啊,还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天工牌,天命教却是如何知道天工牌在我身上?他们又夺牌作甚?”刘云清心中疑问渐渐多了起来,但他怎么会知道便在博物候将天工牌交给陈普文的时候便被天命教徒盯上了,之所以那时没有动手是因为天策府的暗探一直守在左右。
天工牌是博物候的护身法宝,他们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此牌,那么他们应该是想对博物候下手了。易云道人的话萦绕在刘云清耳边,听得刘云清心中烦乱,只是不断地催促着胯下骏马,“难道天下真的要乱了吗?连博物候都有人想要扳倒。”
闽牧州北沿长江,南临南冥,东依群山,地势极其优越。城外以东,群山如屏,最有名的便是神兵山、九仙山、乌阳山。
闽牧州主城叶煌城便盘卧在三山脚下,宗朝时城中编户植榕,全城绿荫,所以主城便被称为叶煌城,到了帝朝闽牧州百姓已然如此传统。
叶煌城外又有神兵山下的冶城,临海的罗城,沿江的子城环卫,却是各司其所长。
帝宗大战期间,闽牧州却少涉战火侵染,一直繁盛如初。北方流离失所的百姓大量南移入闽,这次事件吴人郑鼎《都会记》称为“衣冠南渡”。
言道:“至此,人口繁昌,叶煌一分为四,北建子城已云商贸,南设罗城以典船舶,东有冶城以出利器,正所谓时和年丰,实给人足,已然南之大都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