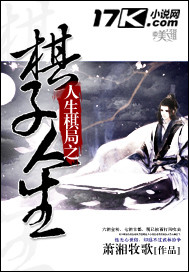第十一章 抚州知县洪培德
子夜午时,一全身棕色上品良马从西侧城门疾驰而来,城门缓缓撑开,骑上一俊朗少年眼睛里透着股犀利,纵马飞跃,一身银白镶边披风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英姿飒爽……
一丝的朦胧月光渐没入云层,白日那充满生气的大地随即间被吞噬,黑暗中平静的瓦砾上一矫健的身行正蓄势待发,沉静的府邸紧闭,槛门正中匾额上由上好红墨砌印鉴楷模着‘抚州府尹’四个大字。
烛灯掌影中,一约摸三十有八九的福态男子前排而行,慈眉善目,负手背后掀有一册书卷,后则乃随跟间距着一四十左右的男子,手中掌灯,背脊略俯,体态削瘦。两人并无交涉过多,只待那福态男子推门步入房内,那削瘦之人才悄然掌灯离去。
待院内静默如初后,那矫健的身行才纵身飞跃而下,悄声潜入房内,还未定住心性,暗中觉察一股夹杂着狠利的掌劲横劈过来,警觉之下忙提气引力迎合,一招下来,竟各退半步无从胜负。屋内微灯倏然掌起,莫绾清抬头一看,原是一彪悍男子,此刻正怒目对视,相貌陋俗,难辨析年岁。
“来者何人,竟敢夜闯我‘抚州府邸’。”一男子掀开帷幔从内侧频步而出,怒喝一声。
莫绾清侧目一看,竟是那先前进入屋内的福态男子,此刻正一脸戒备注视着自己。
“在下莫绾清,受锦衣卫督指挥使毛大人所托,秘密护送洪培德洪大人进京。”
“可有信物凭证?”
莫绾清从怀里摸出临行前毛骧交咐的一只青雕玉佩递给那人,幽幽的玉雕透着股汪汪清绿,滑致细腻。
那福态男子皱眉凝神了半响,才轻叹一声,“我就是洪培德。”随即看向莫绾清笑道:“莫少侠今夜便留宿在下府尹,明日再行打算。”
“可是……”
“好了,莫少侠稍等片刻,”洪培德并不给莫绾清返驳的机会。即刻命令身边那位彪悍男子,“虎啸,去叫管家为这位莫少侠安排一下。”
莫绾清当即倍感疑惑,这难道便是百姓口中所念叨的好官?心中免不起隔阂,但又念至或是自己太过浮躁,虽心中颇为不愉,却也无可奈何,以至夜中难以沉稳入眠。直至五更时分,朦胧睡意起时,隐约中觉察闪现一人影,心下一惊,顿时醒来,待看来人,竟是那抚州府知县洪培德。只见洪培德一身粗布麻衣,做平民打扮,对他打了个“嘘-”的手势,顷刻间会意的莫绾清随即翻身而起。
莫绾清怎么也没想到,洪培德不但为官清廉,且处事低调谨慎。夜间那般做,无非是用以掩人耳目,唯恐府内藏有细作,如此那般大张旗鼓,只怕还未行程,便已被细作盯梢上。他即能发现他的存在,那细作也亦可,如此这般便顺水推舟的来了个金蝉脱壳。
这边二人趁着夜色悄潜出府,而另一边则大张旗鼓的布置着官腔套路,随着队列而行的当然少不了洪培德的贴身护卫虎啸。
路上洪培德皆以秀才自居,以进京赴考为由,莫绾清则做伴读打扮,一路下来竟也算相安无事,直至到得江西景德镇。
景德镇通以陶瓷闻名天下,素有‘瓷都’之美誉,天下人无不羡艳。连着昔日无所癖好的莫绾清也忍禁不住心中频频冒出多留素日的念头,怎耐宿命使然。
十二月的冬至已是寒霜披露,怎耐天公难测,临近小镇道途,本着细絮的鹅毛飘雪却逐渐纷飞起来。莫绾清尾随洪培德钻进一间路边毛棚,小二沏上一壶清茶,掀盖嗅闻,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轻琢一小口,暖流直泌入心脾,顿感身心疏缓。
席间洪培德又命店家温了一小壶浊酒,自己斟上一酢,又为莫绾清满上一杯,见莫绾清迟迟不饮,便笑问道:“莫小兄弟不饮酒?”见莫绾清垂目半天不做声响,又笑劝道:“其实我也并不好饮,平日里也只是重要场席才恭维一下,这不,今日也着实寒凉,借酒驱驱身上寒气。若半路被这寒气沁了身子,病上几日,耽搁了行程,岂不悔之?再说,温过的酒烈性不强。”
正犹豫间,忽地从侧伸出一只手以即快之速将桌上酒杯夺去,顷刻间,莫绾清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劲气,一贯的警觉霍然而起。
“哈……小兄弟不好饮,小老儿就替他饮了这杯吧!”几声爽朗的笑后,一洪亮的声音响起,二人回头一看,竟是一皱巴老头,模样似有六旬,一身衣襟凌乱破旧,在这寒冽的冬季竟也不见他颤栗半分,反倒是一幅炯炯神态,想来是平日里习以为常了吧!
莫绾清正要起怒,却被洪培德暗中小踢了一脚以示,便只好强行抑制。
那小老儿自顾自的饮了一杯,却也并不尽下主宾之理,竟又恬不知耻的端起桌上壶酒豪饮起来,完全对于旁侧二人视若无睹,饮完还不忘咂舌评说,“这酒咋那么没味呐!一点也不好喝。”
闻听此言,莫绾清没好气的朝他翻了个白眼。洪培德却截然相反,不但笑言以对,还客气的请他入坐。
“承蒙侠士不嫌弃,可否一并入坐?”
“好!”
那小老儿也不客气,一扔酒壶,甩手撩起袖子,一撅屁股便坐在了莫绾清的旁侧毫无形像的横扫起来,洪培德又命小二加了几道菜,请了一壶酒。
为节省盘缠,一路下来,二人也尽都清汤寡水,并不大肆挥霍,今日却因此人的到来,硬生生的加了一倍,莫绾清瞅着严重缩水的钱袋,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安排。
午晌时分,客座渐疏,小二过来收拾琳琅满目的桌面,莫绾清随着洪培德小憩了会,便开始了行程,谁知来马厩里一看,顿时呆了,马厩虽有马俩匹,却惟独不见自家那俩匹,急蹿之下忙址过店二的衣襟厉声问道:“我们的马呢?”
店二颓缩着身子,脸色顿时刹白,带着满是哭腔的颤声央求道:“客,客官,饶了我吧!我真不知道,马,马儿一直都在这里呀!我去收拾之前还喂过它草料呢。”
“你再编胡话试试”莫绾清拎起拳头就欲揍过去。
“绾清”一旁的洪培德见状忙出声喝住。
洪培德朝莫绾清使了个眼色,待莫绾清松开那店二才把他拉到一旁小声道:“那小二没说谎,我刚才检查过,马槽里的马料上沾有未干的粘涎,应该离去不久,现下最要紧的是追回被偷的马。”
洪培德知道莫绾清心里着急,他亦是如此,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失去马的重要性,整个行程或许会因为这个而被耽搁,但他更清楚的知道凌乱中那份该持有的冷静。
“我刚才看见一穿着破烂的老头牵马过去了。”经店小二询问,靠近边排桌上一中年男子脱口而出。转而向莫绾清二人侧目看来,“哎呀!刚才见你们在一桌有说有笑的,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语气里颇带有戏谑,见莫绾清横眉冷眼对了过来,立即嘎然而止。
经那人提醒,莫绾清低头一瞥,发现挂在腰间的钱袋不知何时已空空如也,心下一紧,猛然想起那老儿临走之际醺醉的撞了一下自已,心中蹭然明了一切终究是局一场,万般心细还是钻了套。
走了一程,寻了一路,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在临近小镇的一个村落里,二人找到了买马的宿主,只可惜,他们似乎晚了一步,马已经被转手卖给了途经的商户。茫茫人海,找到买马的宿主已是万幸,何况转手的是个漂浮不定的商户,二人自知已无希望,洪培德更是难抵自责。
早曾听闻这洪培德是贫苦出身,见惯了贫穷苦寒,难免怜悯心甚,虽在官场摸爬滚打了许些年,多了份警惕,但刚正不阿的性子犹在,之所以受百姓拥戴,无非就是体恤民心,曾几何时他的父亲亦是这般性情,只可惜下场却是那么惨烈的触目惊心。莫绾清并不怨怪他,只是听他自责,却不知何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