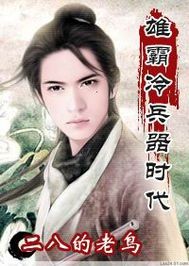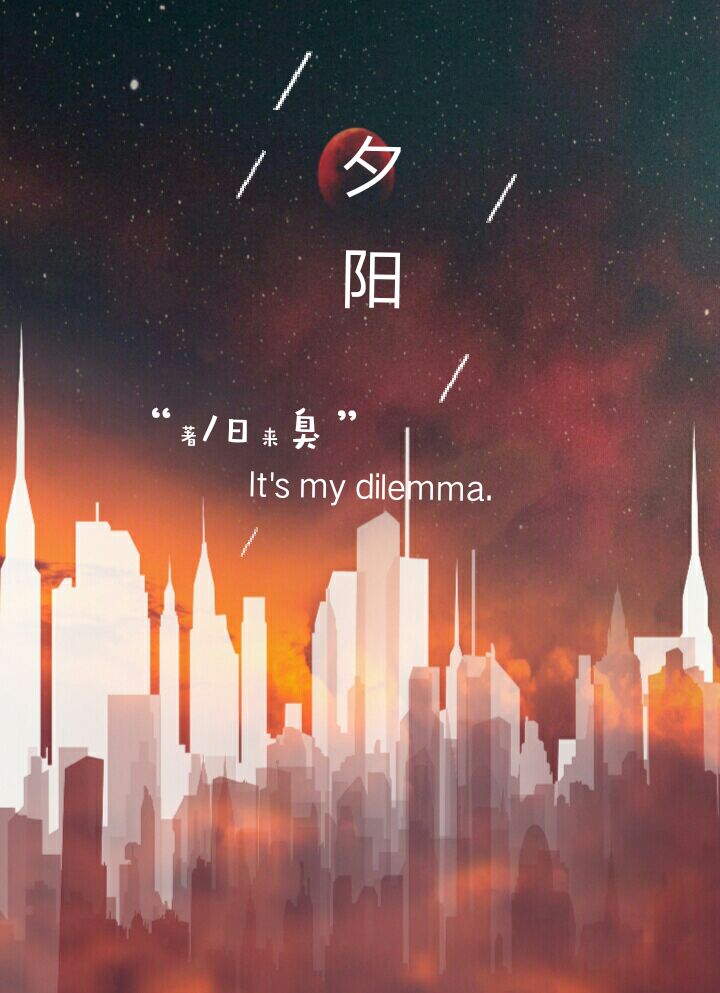牧沙起身,捂着头适应着阵阵的疼,阵阵的眩,阵阵的难受。掀开被子打开门,赫然发现门口闭目坐着的余昕吓了一跳。凝视他良久,她转身回去病房拿了条毛毯出来给他盖上。腰没直起,右手被他握住。
冰凉的手指还没她的温暖。
“想去哪儿走走?”他暗哑的嗓音听起来让她有种莫名亲切感。她轻轻摇头,左手捂头,“躺久了难受,我起来站站。”
他拉下身上的毛毯简单叠好放在座椅上,“我陪你。”
“不用了,我就在走廊上走走就行了。不会走远。”她拒绝。现在,她的头很疼,脑子里也很乱。
余昕没有妥协:“我不放心。”
她嗤笑:“我还能自杀怎么的?”他坚持拉着她的手,她相当无奈。
天已经亮了,走廊上也有早起的人开始了忙碌。余昕牵着她的手说:“去楼下花园遛遛?顺便吃早点?”
“好。”她表现得很平静。余昕一时拿捏不准她究竟是爆发前的平静还是宛若死亡的宁静。
牵着手,乘坐电梯到1楼。慢慢走过花园,再慢慢走到餐厅。一直到吃完早点回到病房,他才松开手放她自由。
给她端来温水洗手,再用干毛巾擦干手,抹上护手霜。扶着她坐到病床上躺下,“再睡会儿,你现在需要休息。”
她异常听话,乖乖闭上眼,没多久呼吸就趋于平缓,进入了梦乡。护士送来温度表,他轻轻夹在她的腋下,再掖好被角。医生来查房,他告知一切准确的记录。
医生宣布:如若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出院。
“她只有在你面前才会这样乖巧啊。”余晓感叹,叶子点头附和,“嗯,换成其他人要这样干涉她的行动,早炸了锅了。”左小桑双手托腮,“虽然现在说这话感觉有点落井下石,我还是觉得昕和沙沙是最般配的。”
“同感。”司马水斜靠着墙点头,扳手指头,“同样的执着,同样的固执,同样的感性,同样的自由。只有合适的人,才能理解合适的人的一切想法,明白那个人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个字的含意。很多争吵起因不都源自于误会吗?”
余昕抬手做手势:“停!”
几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余晓忍不住说:“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你还要护她到什么时候?有些东西你若不说出来,沙沙会怎么理解,你想过吗?”
“嗯,我觉得,沙沙会当作习惯的关注,不做其他考虑。”叶子坦言。左小桑撅撅嘴:“说的是,沙沙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自作多情。你要是不把话说透了,她真能当作什么都没有一样跟你和平相处下去。”
司马水在一旁点头:“嗯嗯额,的确是这样。以前在我家店里有个师傅就很喜欢沙沙,每次都额外送给她爱心蛋糕。那家伙不敢表白,就等着沙沙哪天忍不住自己来找他,结果沙沙愣是吃了一年的爱心蛋糕依然一往如故,直接把我家店里那个师傅给郁闷跑了。”
左小桑咧嘴笑:“哈哈,她就这样的人。没辙!”
叶子咬着指甲皱着眉说:“这些年她唯一主动找过的男性只有姚睿希那小子吧?”
左小桑想了想,“是。连方吉都是主动表白了之后她才做的反应。只有睿希在她主动跑去人家家里睡觉的。”两人说着话,完全没顾到余昕,更加没注意到他愈来愈冷的脸色。
叶子继续啃拇指:“可她去找姚睿希也是因为和牧睿昔同名的缘故嘛,不能算作有别的感情在里面吧?”
左小桑扬起下巴:“嗯,当成她儿子的那种感情。”
叶子无奈的苦着脸:“想来想去,她根本就没有跟男人主动过嘛……”她扭头去看余昕,“所以说,你想等沙沙自己来跟你表白啊,很悬!”
余晓搂着左小桑坐在凳子上忽然说:“昕,你不会是想就这样守着沙沙一辈子吧?”
叶子愕然:“真的假的?那你这个想法就太伟大了。”
左小桑握着余晓的手皱眉:“为了沙沙的幸福而言,我觉得你还是直说比较好。”
叶子握拳:“YES!为了大家的幸福,你就勉为其难的收了她吧。”她话音一落,就被飞来的枕头砸中了脸。大家齐齐扭头,睡在床上的牧沙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当然,枕头那块儿是空的。
“怕我嫁不出去成你们的心病?”牧沙脸色苍白得没有血色,声音也略微沙哑。左小桑急忙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叶子抱着枕头说:“你是不是可以不去扭曲我们的意思?你明明知道我们是在关心你,偏偏要说那么伤人的话来听。”
牧沙抿着嘴不再说话,挺直了腰板把头扭向一旁。
叶子站起来转身就离开了病房,左小桑见状赶忙追了上去:“叶子,叶子,叶子……哎呀。”她转头看了一眼牧沙,跺跺脚也出了病房。“叶子……”
司马水歪歪头,一语不发出了病房。有种云淡风轻的飘然。
余晓看看余昕,指指牧沙,耸耸肩,自己也出了病房。一下子病房里只剩了余昕和牧沙两个人。
“沙……”余昕刚张嘴,牧沙就如同机关枪一样咄咄逼人,“你走,马上走。我不需要你在这里装好人。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利用大家来逼我妥协。难道说我除了你就没人要了吗?这些年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真没见过你种人。我就那么贱?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凭什么都得听你的?莫名其妙人就没有了,莫名其妙人又出现了……”
牧沙的话语无伦次,说着,说着,眼泪迸了出来,她把头埋进被子里。倔强的不让自己哭出声音。
听见开头的话,余昕也来了气。可听到后面他心里的哀伤莫名的暴增。
莫名其妙人就没了,莫名其妙人又出现了……
当年他就是这样,忽然人就没有了。一走十多年不见人影,连个消息都没有。忽然人又出现了,还自以为是的自诩她的保护者。她一身风尘仆仆,从风雨中来,往风雨中去。自己作践着自己,自己糟蹋着自己。只为了报复当年父母的反对,报复他们的阻止。结果呢?结果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又怎样?没有人懂,没有人疼,没有人真心的爱。
她不是没有渴望过,也不是没有期盼过。十五年啊,她渴望过谁又期盼过什么?现在她心灰意冷,不愿再起波澜的时候,他出现了……
出现了又怎样?没有一句实话,没有一点真诚。他这样的出现与不出现有什么差别?
“沙沙……”
“别叫我!!!!”她捂住耳朵,头疼欲裂,“你走!我不想看见你!走!!”她的声音不大,透着病痛的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