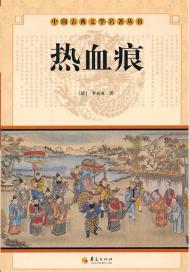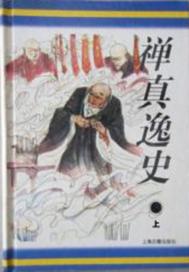绰约墙头花,分辉映衢路。
色随煦日丽,香逐轻风度。
蛱蝶巧窥伺,翩翩竞趋附。
缱绻不复离,回环故相慕。
蛛网何高张,缠缚苦相怖。
难张穿花翅,竟作触株兔。
朱文公有诗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见得人到女色上最易动心,就是极有操守的,到此把生平行谊都坏。且莫说当今的人,即如往古楚霸王,岂不是杀人不贬眼的魔君?轮到虞姬身上,至死犹然恋恋。又如晋朝石崇,爱一个绿珠,不舍得送与孙秀,被他族灭。唐朝乔知之爱一妾,至于为武三思所害。至若耳目所闻见,杭州一个秀才,年纪不多,也有些学问,只是轻薄,好挨光,讨便宜。因与一个赌行中人往来,相好得紧,见他妻子美貌,他便乘机勾搭,故意叫妇人与他首饰,着他彻夜去赌,自己得停眠整宿。还道不像意,又把妇人拐出,藏在坟庵里。他丈夫寻人时,反帮他告状,使他不疑。自谓做得极好,不意被自家人知觉,两个双双自缢在庵中,把一个青年秀才陪着红粉佳人去死,岂不可惜?又还有踹人浑水,占了人拐带来的女人,后来事露,代那拐带的吃官司吃敲吃打;奸**子,被人杀死;被傍人局诈。这数种,却也是寻常有的,不足为奇。如今单讲的是贪人美色,不曾到手,却也骗去许多银子,身受**的,与好色人做个模样。
话说浙江杭州府,宋时名为临安府,是个帝王之都。南柴北米,东菜西鱼,人烟极是凑集,做了个富庶之地,却也是狡狯之场。东首一带,自钱塘江直通大海。沙滩之上,灶户各有分地,煎沙成盐,卖与盐商,分行各地。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桥设立批验盐引所,称掣放行,故此盐商都聚在杭城。有一个商人姓吴名爚字尔辉,祖籍徽郡,因做盐,寓居杭城箭桥大街。年纪三十二三,家中颇有数千家事。但做人极是啬吝,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凭你大熟之年,米五钱一石,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外面恰又装饰体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见一个略有些颜色妇人,便看个死。苦是家中撞了个妪人,年纪也只三十岁,却是生得胖大,虽没有晋南阳王保身重八百斤,却也重有一百廿。一个脸大似面盘,一双脚夫妻两个可互穿得鞋子。房中两个丫鬟,一个秋菊,年四十二;一个冬梅,年三十八。一个髻儿长歪扭在头上,穿了一双趿鞋,日逐在街坊上买东买西,身上一件光青布衫儿,龌龊也有半寸多厚。正是:何处生来窈窕娘,悬河口阔剑眉长。
不须轻把裙儿揭,过处时闻酱醋香。只因家中都是罗刹婆、鬼子母,把他眼睛越弄得饿了,逢着妇人,便出神的看。时常为到盐运司去,往猫儿桥经过。其时桥边有个张二娘,乃是开机坊王老实女儿,哥哥也在学,嫁与张二官,叫名张彀。张家积祖原是走广生意,遗有帐目。张彀要往起身进广收拾,二娘阻他,再三不肯,止留得一个丫鬟桂香伴他。不料一去十月有余,这妇人好生思想。正是:晓窗睡起静支颐,两点愁痕滞翠眉。
云髻半髽慵自整,王孙芳草系深思。常时没情没绪的倚着楼窗看。一日,恰值着吴尔辉过,便盯住两眼去看他。妇人心有所思,那里知道他看?也不躲避。他道这妇人一定有我的情,故此动也不动,卖弄身份。以后装扮得齐齐整整,每日在他门前晃。有时遇着,也有时不遇着。心中常自道:“今日这一睃,是丢与我的眼色,那一笑,与我甚是有情。”若不见他在窗口时,便踱来踱去,一日穿梭般走这样百十遍。
也是合当有事,巧巧遇着一个光棍,道:“这塌毛甚是可恶,怎在这所在哄诱人良家妇女。”意思道他专在这厢走动,便拿他鹅头。不料一打听,这妇人是良家,丈夫虽不在家,却极正气,无人走动。这光棍道:“待我生一计美这蛮子。”算计定了,次日立在妇人门首,只见这吴尔辉看惯了,仍旧这等侧着头,斜着眼,望着楼窗走来。光棍却从他背后轻轻把他袖底一扯,道:“朝奉。”吴尔辉正看得高兴,吃了一惊,道:“你是甚人?素不相识。”这光棍笑道:“朝奉,我看你光景,想是看想这妇人。”吴尔辉红了脸道:“并没这事。若有这事,不得好死,遭恶官司。”光棍道:“不妨,这是我房下,朝奉若要,我便送与朝奉。”吴尔辉道:“我断不干这样事。”板着脸去了。次日,这个光棍又买解,仍旧立在妇人门前,走过来道:“朝奉,舍下吃茶去。”吴尔辉道:“不曾专拜,叨扰不当。”那光棍又陪着他走,说:“朝奉,昨日说的,在下不是假话。这房下虽不曾与我生有儿女,却也相得。不知近日为些甚么,与老母不投,两边时常竞气,老母要我出他。他人物不是奖说,也有几分,性格待我极好,怎生忍得?只是要做孝子,也做不得义夫。况且两硬必有一伤,不若送与朝奉,得几十两银子,可以另娶一个。他离了婆婆,也得自在。”吴尔辉道:“恩爱夫妻,我怎么来拆散你的?况且我一个朋友讨了一个有夫妇人,被他前夫累累来诈,这带箭老鸦,谁人要他!”光棍道:“我写一纸离书与你是了。”吴尔辉道:“若变脸时,又道离书是我逼勒写的,便画把刀也没用。我怎么落你局中?”光棍道:“这断不相欺。”吴尔辉道:“这再处。”自去了。
到第三日,这光棍打听了他住居,自去相见。吴尔辉见了,怕里面听得,便一把扯着道:“这不是说话处。”倒走出门前来。那光棍道:“覆水难改,在下再无二言。但只是如今也有这等迷痴的人,怪不得朝奉生疑。朝奉若果要,我便告他一个官府执照,道他不孝,情愿离婚,听他改嫁,朝奉便没后患了。”吴尔辉沉吟半日,道:“怕做不来。你若做得来,拿执照与我时,我兑二十两;人到我门前时,找上三十两,共五十两。你肯便做?”光棍道:“少些。似他这标致,若落水,怕没有二百金?但他待我极恩爱,今日也是迫于母命。没奈何,怎忍做这没阴骘事?好歹送与朝奉,一百两罢。”吴尔辉道:“太多,再加十两。”两边又说,说到七十两,先要执照为据兑银。
此时,光棍便与两个一般走空骗人好伙计商量起来,做起一张呈子,便到钱塘县。此时本县缺官,本府三府署印面审词状。这光棍递上呈子,那三府接上一看:具呈人张青。
呈为恳恩除逆事。切青年幼丧父,依母存活。上年蹇娶悍妇王氏,恃强抵触,屡训不悛,忤母致病。里邻陈情、朱吉等证。痛思忤逆不孝,事关七出。鰸妇不去。孀母不生。叩乞批照离嫁,实为恩德。上呈。那三府看了呈,问道:“如今忤逆之子,多系爱妻逆母。你若果为母出妻,可谓孝子。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或是宠妾逐妻,种种隐情,驾忤逆为名有之。我这边还要拘两邻审。”光棍道:“都是实情。老爷不信,就着人拘两邻便是。”三府便掣了一根签,叫一个甲首分付道:“拘两邻回话。”这甲首便同了光棍,出离县门。光棍道:“先到舍下,待小弟邀两邻过来。”就往运司河下便走。将近肚子桥,只见两个人走来,道:“张小山,怎么这样呆?”光棍便对甲首道:“这是我左邻陈望湖,这是右邻朱敬松。”那敬松便道:“小山,夫妻之情,虽然他有些不是,冲突令堂,再看他半年三月处置。”光棍道:“这样妇人,一日也难合伙,说甚半年三月。”陈望湖道:“你如今且回去,再接他阿哥,同着我们劝他一番。又不改,离异未迟。”光棍道:“望湖,我们要做人家的人,不三日五日大闹,碗儿、盏儿甩得沸反,一月少也要买六七遭。便一生没老婆,也留他不得。如今我已告准,着这位老牌来请列位面审,便准离了。”敬松道:“只可打拢,怎么打开?我不去,不做这没阴骘事。”甲首道:“现奉本县老爷火签拘你们,怎推得不去?”陈望湖道:“这也是他们大娘做事拙,实的虚不得。”光棍道:“今日我们且同到舍下坐一坐,明日来回话。”甲首道:“老爷立等。”敬松道:“这时候早堂已退了,晚堂不是回话的时节,还是明日罢。”陈望湖道:“巧言不如直道。你毕竟要了落老牌。屋里碗碟昨日打得粉碎,令正没好气,也不肯替你安排,倒不如在这边酒店里坐一坐罢。”四个便在桥边酒店坐下,一头吃酒,一头说。敬松道:“看不出,好一个人儿怎么这等狠。”陈望湖道:“令堂也琐碎些。只是逆来顺受,不该这等放泼,出言吐语,教道乡村。”甲首道:“这须拿他出来,拶他一拶,打他二十个巴掌,看他怕不怕。”光棍道:“倒也不怕的。”敬松道:“罢,与他做甚冤家。等他再嫁个好主顾。”差人道:“不知甚么人晦气哩。”吃了一会,光棍下楼去了一刻,称了差使钱来。差人不吃饭,写了一个饭票。这三个都吃了饭,送出差使钱来。差人捏一捏,道:“这原不是斗殴户婚田土,讲得差使起的。只是也还轻些。”敬松道:“这里想有三分银子,明日回话后,再找一分。”差人道:“再是这样一个包儿罢。”陈望湖道:“酌中找二分罢。”差人道:“明日我到那边请列位。”望湖道:“没甚汤水,怎劳你远走?明日绝早,我们三个自来罢。”差人道:“这等明早来桥边会,火签耽延不得的。”次早,差人到得桥边,只见三个已在那边,就同到县中。伺候升了堂,差人过去缴签,禀道:“带两邻回话的。”三府便道:“怎么说?”光棍道:“小人张青,因妻子忤逆母亲,告照离异,蒙著唤两邻审问,今日在这边伺候。”三府道:“那两邻怎么说?”只见这两个道:“小人是两邻。这张青是从小极孝顺的。他妻子委是不贤,常与他母亲争竞。前日失手推了母亲一交,致气成病,以致激恼老爷。”三府道:“这还该拿来处。”光棍便叩头道:“不敢费老爷天心,只求老爷龙笔赐照。”三府便提起笔写道:王氏不孝,两邻证之已详,一出无辞矣。姑免拘究,准与离异。批罢,光棍道:“求老爷赐一颗宝。”三府便与了一颗印。光棍又用了一钱银子,挂了号,好不欣然,来见吴尔辉。吴尔辉看了执照,道:“果然你肯把他嫁我?”光棍道:“不嫁你,告执照?”尔辉满心欢喜,便悄悄进去,拿了一封银子:十七两摇丝,三两水丝。光棍看了道:“兑准的么?后边银水还要好些,明日就送过来。”尔辉道:“我还要择一日。今日初七,十一日好,你可送到葛岭小庄上来。”那光棍已是诓了二十两到手了。
第二日,央了个光棍,穿了件好齐整海青,戴了顶方巾,他自做了伴当,走到张家来。那光棍先走到坐启布帘边,叫一声:“张二爷在家么?”妇人在里边应道:“不在家。”光棍便问道:“那里去了?”里边又应道:“一向广里去,还未回。”只见戴巾的对光棍道:“你与他一同起身的,怎还未回?”光棍道:“我与他同回的。想他不在这边,明日那边寻他是了。”戴巾的转身便去。那妇人听了,不知甚意,故忙叫:“老爹请坐吃茶,我还有话问。”那人已自去了。妇人道:“桂香,快去扯他管家来问。”此时这光棍故意慢走,被桂香一把拖住,道:“娘有话问你。”光棍道:“不要扯,老爹还要我跟去拜客。”桂香只是拖住不放。扯到家中,妇人问道:“你们那家?几时与我二爷起身?如今二爷在那边?”这人趦趄不说。妇人叫桂香拿茶来,道:“一定要你说个明白。”光棍道:“我姓俞,适才来的是我老爹,叫我在广东做生意。你们二爷一同起身,因二爷缺些盘缠,问我借了几两银子,故此我老爹来拜。”妇人道:“他怎么没盘缠?”光棍道:“他银子都买了苏木、胡椒与铜货,身边剩得不多,故此问我们借。”妇人道:“他几时起身?”光棍道:“是三月初三。妇人道”你几时到的?“光棍道”前月廿人。“妇人道”怎同来,他又不到?你说明日那边寻,是那边?“光棍道”我说明日再寻,他不曾说那边。“妇人道”我明明听得的。好管家,说了我谢你。“光棍道”说了口面狼藉,又是我的孽。“又待要走,妇人便赶来留,说”桂香,我针线匾里有一百铜钱,拿来送管家买酒吃。光棍道:“说便说,二娘不要气。”妇人道:“我不气便了。”光棍道:“你二爷在广时,曾阚一个杨鸾儿,与他极过得好,要跟二爷来。二爷不肯,直到临起身,那杨鸾哭哭啼啼,定要嫁他,身边自拿出一注银子,把二爷赎身,二爷一厘不曾破费。因添了一个内眷,又讨了一个丫头,恐怕路上盘缠不够,问我借银十两同来。”妇人道:“既同来,得知他在那里?”光棍道:“这不好说。”妇人道:“这一定要说。”光棍道:“这内眷生得也只二娘模样,做人温柔,身边想还有钱。二爷怕与二娘合不来,路上说要寻一个庄——在钱塘门外——与他住。故此到江头时,他的货都往进龙浦赤山埠湖里去,想都安顿在庄上。目下也必定回了。”妇人道:“如何等得他回?一定要累你替我去寻他。”光棍道:“我为这几两银子毕竟要寻他,只是不好领二娘去。且等明日,寻着了他来回复。”这光棍骗了一百钱去了。
这妇人气得不要,人上央人,去接阿哥王秀才来。把这话一说,连那王秀才弄得将信将疑,道:“料也躲不过,等他自回。”妇人道:“他都把这些货发在身边发卖,有了小老婆,又有钱用,这黑心忘八还肯回来?好歹等那人明日回复,后日你倍我去寻他。”兄妹两个吃了些酒,约定自去。等到初十下午,只见这光棍走将来。桂香看了,忙赶进去道:“那人来了。”这妇人忙走出道:“曾寻着么?”光棍道:“见了,在钱塘门外一个庄上。早起老爹去拜,你二爷便出来相见,留住吃饭。这货虽发一半到店家,还未曾兑得银子,约月半后还。姨娘因我是同来熟人,叫我到里面,与我酒吃。现成下饭,烧鸭、熩蹄子、湖头鲫鱼,倒也齐整。姨娘不像在舡中穿个青布衫,穿的是玄色冰纱衫,白生绢袄衬,水红胡罗裙,打扮得越娇了。二爷问我道:‘你曾到我家么?’我道:‘不曾。’他说:‘千万不可把家中得知。’昨日不曾分付得,我又尖了这遭嘴。”这妇人听了,把脚来连顿几顿,道:“有这忘八,你这等穿吃快活,丢我独自在家。明早央你替我同去寻他。”光棍道:“怕没工夫。况且我领了你去,张二爷须怪我,后边不好讨这注银子。”妇人道:“你只领我到,我自进去罢。日后银子竟在我身上还,没银子我便点他货与你。”又留他吃了些酒,假喃喃的道:“没要紧,又做这场恶。”妇人又扎缚他道:“我们明日老等你,千定要来。”光棍去了。妇人隔夜约定轿子,又约了王秀才。清晨起来,煮了饭,安排了些鱼肉之类。先是轿夫到,次后王秀才来。等了半晌,这光棍洋洋也到。那妇人好不心焦,一到便叫他吃了饭,分付桂香看家。妇人上了轿,王秀才与光棍随着,一行人望钱塘门而来。
这厢吴尔辉自得了执照,料得稳如磐石,只是家中妪人不大本分,又想张家娘子又是不怕阿婆的料,也不善,恐怕好日头争竞起来。他假说芜湖收帐,收拾了铺陈,带了个心腹小郎欢哥、一个小厮喜童,来到湖上,赁了个庄,税了张好凉床、桌椅,买了些动用家伙碗盏,簇新做顶红滴水月白胡罗帐,绵绸被单,收拾得齐齐整整,只等新人来。只见这张家轿夫抬个落山徤,早已出钱塘门。光棍与王秀才走了一身汗,也到城外。妇人推开帘儿问道:“到也不曾?”光棍道:“转出湖头便是。只是二娘这来,须见得张二爷好说话。若他不在,止见得姨娘,他一个不认帐,叫我也没趣。况且把他得知了,移了窠,叫我再那里去寻?如今轿子且离着十来家人家歇,等我进去先见了,我出来招呼,你们便进去,我不出来,你们不要冲进。我直要骗他到厅上,叫他躲不及你们方好。”王秀才连声道:“有理,有理。”就歇下轿,王秀才借人家门首坐了。
光棍公然摇摆进去,见了吴尔辉。吴尔辉道:“来了么?”光棍道:“轿已在门前,说的物可见赐。”吴尔辉说:“待人进门着。”光棍道:“这吴朝奉,桥在门前,飞了去?只是在下也有些体面,就是他令兄,也是个在庠朋友,见在外边送。当面在这里兑银子,不惟在下不成模样,连他令兄也觉难为。如今我自领了银子去,等他令兄进来。只是他令兄,朝奉须打点一个席儿待一待,也是朝奉体面。”吴尔辉便叫小厮去看,道果然轿子歇在十来家门前。尔辉便叫小厮去叫厨子,将银子交出。都不是前番银子,一半九二三逼冲,一半八程极逼火。光棍道:“朝奉不忠厚,怎拿这银子出来?要换过。”吴尔辉道:“兄胡乱用一用罢。这里寓居,更换不便。”光棍定要换,吴尔辉便拿出一两逼火,道:“换是没得换,兄就要去这两作东罢。”光棍恐怕耽延长久,妇人等不得赶进来,便假脱手道:“罢,罢,再要添也不成体面。”作辞去了。走到轿边,道:“两个睡得高兴,等了半日才起来。如今正在厅上与个徽州人说话,快进去。”妇人听了,忙叫轿夫,一个偏在那里系草鞋带,不来。妇人恨不得下轿跑去,便与王秀才一同闯进庄门。
吴尔辉正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那边等王秀才。这妇人一下轿道:“欺心忘八,讨得好小!”那吴尔辉愕然道:“这是你丈夫情愿嫁与我,有甚欺心?”妇人一面嚷,王秀才道:“舍妹夫在那里?”吴尔辉道:“学生便是。”王秀才道:“混帐!舍妹夫张二兄在那里?”吴尔辉道:“他收了银子去了,今日学生就是妹夫了。”王秀才道:“他收拾银子躲了么?闻他娶一个妾在这里。”吴尔辉道:“娶妾的便是学生。”王秀才道:“妹子不要嚷,我们差来了,娶妾的是此位,张二已躲去了。我们且回罢。”吴尔辉道:“怎么就去?令妹夫已将令妹嫁与学生,足下来送,学生还有个薄席,一定要宽坐。”王秀才道:“这等叫舍妹夫出来。”吴尔辉道:“他拿了银子去了,还在轿边讲话。”此时说来,都是驴头不对马嘴。妇人倒弄得打头不应脑,没得说。王秀才道:“方才轿边说话的是俞家家人,是领我们来寻舍妹夫的,那里是舍妹夫。”吴尔辉道:“正是你前边令妹夫。他道令妹不孝,在县中告了个执照,得学生七十两银子,把令妹与学生作妾。”王秀才道:“奇事,从那边说起?舍妹夫在广东不回,是这个人来说,与他同回,带一个妾住在这厢,舍妹特来白嘴。既没有妾在此,罢了,有甚得你银子、嫁你作妾事?”吴尔辉道:“拿执照来时,兑去二十,今日兑去五十,明明白白。令妹夫得银子去,怎么没人得银?”扯了王秀才道:“学生得罪!宅上不曾送得礼来,故尊舅见怪,学生就补来。桶儿亲,日后正要来往,恕罪,恕罪。”王秀才道:“怎么说个礼?连舍妹早丧公婆,丈夫在广,有甚不孝,谁人告照?”吴尔辉道:“尊舅歪厮缠,现有执照离书在此。”忙忙的拿出来看,王秀才看了道:“张青也不是舍妹夫名字。是了,你串通光棍,诓骗良**子为妾。”一把便来抢这执照。吴尔辉慌忙藏了,道:“你抢了,终不然丢去七十两银子?这等是你通同光棍,假照诓骗我银子了。”王秀才道:“放屁!”一掌便打过去,吴尔辉躲过,大叫道:“地方救人!光棍图赖婚姻打人。”王秀才也叫道:“光棍强占良**子,殴辱斯文。”哄了一屋的人,也不知那个说的是。王秀才叫轿夫且抬了妹子回去:“我自与他理论。”吴尔辉如何肯放,旁边人也道:“执照真的,没一个无因而来之理。”两下甚难解交。
巧巧儿按察司湖舡中吃酒回,一声屈,叫锁发钱塘县审,发到县来。王秀才说是秀才,学中讨收管。吴尔辉先在铺中受享一夜。次日王秀才排了破靴阵,走到县中,行了个七上八落的庭参礼。王秀才便递上一张,是假照诓占事,道:“生员有妹嫁与张彀。土豪吴爚乘他夫在广,假造爷台执照!强抢王氏,以致声冤送台,付乞正法。”你一句,我一句,那三府道:“知道,我一定重处。”就叫这一起。只见吴爚也是一张状子,道诓劫事,道:“无子娶妾遭光棍串同王氏,诓去银七十两。”那三府道:“王生员,你那妹子没个要嫁光景,怎敢来占?”王秀才道:“生员妹子原有夫张彀,在广生理。土豪吴爚贪他姿色,欺他孤身,串通光棍,假称同伙,道生员妹夫娶妾在吴爚家,诓生员妹子去。若不是生员随去,竟为强占了。”三府叫吴爚道:“你怎敢强占人家子女?”吴爚道:“小人因无子,要娶妾。王氏夫张青拿了爷台执照,说他妻子不孝,老爷准他离异,要卖与小的。昨日他送这妇人到门,兑七十两银子去,却教这王生员道小人强占,希图白赖。”就递上抄白执照,三府道:“王生员,这执照莫不是果有的事?”王秀才道:“老大人,舍妹并无公婆,张彀未回,两邻可审,见在外边。”三府道:“叫进来。”只见众邻里一齐跪在阶下。三府道:“叫一个知事体的上来。”一个赵裁缝便跪上去。三府道:“张青可是你邻里?”赵裁缝道:“小的邻舍只有张彀,没有张青。”三府道:“是张彀么?”赵裁缝道:“是,是。”三府道:“如今在那里?”赵缝裁道:“旧年八月去广里未回。”三府道:“王氏在家与何人过活?”赵裁缝道:“他阿婆三年前已死,阿公旧年春死在广东,家中止有一个丫头桂香。”三府道:“他前日为甚么出去?”赵裁缝道:“是大前日,有个人道他丈夫讨小在钱塘门外,反了两日,赶去的。余外小的不知。”三府道:“你不要谎说。”赵裁缝道:“谎说前程不吉。”三府道:“你莫不是买来两邻?”赵裁缝慌道:“见有十家牌,张彀过了赵志,裁缝生理便是小的。”三府讨上去一看,上边是:周仁吴月钱十孙经冯焕李子孝王春蒋大成共十个,并没个陈清、朱吉,心里也认了几分错,就叫吴爚道:“执照是你与张青同告的么?”吴爚道:“是张青自告的。”三府道:“你娶王氏,那个为媒?”吴爚道:“小的与他对树剥皮,自家交易的。”三府道:“兑银子时,也没人见了?”吴爚道:“二十两摇丝,五十两冲头,都是张青亲收。”三府道:“在那家交银?妇人曾知道么?”吴爚道:“昨日轿子到门,交的银子。原说瞒着妇人的。”三府道:“好一个兀突蠢才!娶妾须要明媒,岂有一个自来交易的?”吴爚道:“小的有老爷执照为据。”三府道:“拿上来。”吴爚道:“小的已抄白在老爷上边,真本在家里。”三府便叫前日拘张青两邻差人。那甲首正该班,道:“是小的。”三府道:“张青住在那里?”答应道:“说在荐桥。”三府道:“你仍旧拘他与两邻来。”甲首道:“那日是他自来的,小的并不曾认得所在。”三府道:“又是一个糊涂奴才。”三府便叫王生员:“我想你两家都为人赚了。你那妹子原无嫁人的事,不消讲了。”便叫吴爚:“你这奴才,若论起做媒没人,交银无证,坐你一个诓骗人家子女,也无辞。”吴爚便叩头道:“老爷冤枉。”“只是你还把执照来支吾,又道见妇人到门发银,也属有理。如今上司批发,不可迟延。限你五日内,与差人这奴才寻获张青。若拿不到,差人三十板,把这朦胧告照、局骗良人妇女罪名坐在你身上。”叫讨的当保,王生员与王氏邻里暂发宁家。
可笑这吴爚在外吃亲友笑,在家吃妪人骂,道:“没廉耻入娘贼,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耐了气,只得与差人东走西闯,赔了许多酒食,那里去寻一个人影儿?到第四日,差人对吴爚道:“吴朝奉,我认晦气,跑了四日了,明前该转限。我们衙门里人,诓得伸直脚打两腿;你有身家的人,怎当得这拷问?况且朦胧诓骗都是个该徒的罪名。须寻得一个分上才好。”吴爚原是一个臭吝不舍钱的,说到事在其间,也啬吝不得,便与他去寻分上。正走间,一个人道:“张二倒回来了,王秀才妹子着甚鬼,东走西跑打官司。”差人道:“我们也去看看,莫不是张青?”去时只见张家堆上许多货,张彀还立在门前收货,妇人立在帘边。这张二且是生得标致,与张青那里有一毫相像。吴爚见了,越觉羞惭。正是:柳姬依旧归韩子,叱利应羞错用心。差人打合吴爚,寻了一个三府乡亲,倒讨上河,说要在王氏身上追这七十两银子。分上进去,三府道:“他七十两银子再不要提起罢了。只要得王秀才不来作对,说你诓骗,还去惹他?”但是上司批发,毕竟要归结,止可为他把事卸在张青身上,具由申复。只这样做,又费两名水手。三府为他具由,把诓骗都说在张青身上,照提缉获。吴爚不体来历,罚谷,事完也用去百十两。正是:羊肉不吃得,惹了一身羶。当时街坊上编了一个《桂枝儿》道:吴朝奉,你本来极臭极吝。人一文,你便当做百文。又谁知,落了烟花阱。人又不得得,没了七十金。又惹了官司也,着甚么要紧!总之,人一为**所迷,便不暇致详,便为人愚弄。若使吴君无意于妇人,棍徒虽巧,亦安能诓骗得他?只因贪看妇人,弄出如此事体,岂不是一个好窥瞷良家妇女的明鉴?古人道得好:他财莫要,他马莫骑。这便是个不受骗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