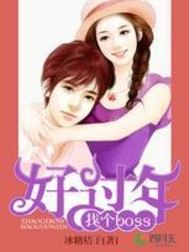我们缓步走出咖啡馆,外面的天空也渐渐黯淡下来,漆黑的夜色没有来由地向我们袭来。
我们在一条小巷子里找了一家清净的小饭店吃了顿晚餐。餐桌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随后,梅子与我一起打车来到我所暂住的宾馆。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梅子走到窗前,用手拨开淡黄色的窗帘的一角,站在窗前看了一眼广州城的夜景,稍后将窗帘理顺好又将脸转向我这一边,用眼睛扫视了一番房间的陈设,最后一屁股坐在床的一角,很肯定地说到:“这里的确适合你?”
“恩,是比较幽静。”我点点头,我将外套脱下来反转过来叠好轻轻放在沙发上,只穿一件黑色的粗毛衣。
我从床头柜里翻出空调机的遥控器,将室内温度调高到23度的位置,又在凌乱的沙发角落摸到电视遥控器,将电视打开,按了几下没有什么合我胃口的频道,最终选了一个上演肥皂剧的。
随后我又到卫生间将旅店的电水壶装满水插上电源,三分钟后水烧开了,我将两个杯子冲洗一遍,甩干水一一摆放在桌上,放进旅店供应的简便茶叶包,又将开水注入透明的玻璃杯子里。
碧绿的茶叶在杯中呈翻滚状态一粒一粒往上涌来,很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清香的味道。
而梅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忙东忙西,眼神中流露出陶醉的惊喜,像是欣赏某个匠人在制作一件工艺品似的,她始终都没有插手的意思。
差不多在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和梅子只是相对而坐,各自喝着各自杯中的茶水,我们如一对相伴多年的朋友一样,知晓对方的性情,都在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忍心让自己扰乱这片十分难得的宁静。
期间我站起来为梅子添了两次水,梅子既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打破这种宁静的气氛。
喝完第三杯茶时,可能觉得房间里的温度上来了,梅子站起来摘下围脖,也脱去了外面红色的外套,里面只穿一件绿色的无领羊毛衫。
此外,我们如木偶般对望。仅此而已。
电视里何时播放一档情感节目我不得而知。倒是梅子的眼睛很快被节目吸引过去了。
我不得不顺着梅子的目光将注意力放在电视节目里面。在主持人具有挑逗性的提问下,两个可能曾经是恋人的年轻男女,在旋律优美的音乐声中一一各自诉说着离开对方十年后重逢的感受和心情。
节目最后穿插着这对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的男女恋人在主持人的再三怂恿下相拥互抱的镜头。
梅子也是看到这个场景而痛哭悲戚起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子的泣哭声在房间里环绕开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只是麻木地将纸巾抽出来一张一张塞到她的手里,她的眼泪像永远也擦不尽似的,茶几上堆满了被梅子揉成各种形状的纸巾,而她的手里还攥着我刚刚递过去的一片纸巾。
到节目结束,梅子方才停止了哭泣,她默默地将桌子上一堆被自己的手捏出奇形怪状的纸巾收拢后全部丢进垃圾桶。
稍后,又拿起手袋走进卫生间,或许觉得脸上妆容破坏的实在厉害极了,她可能在卫生间里补了妆,待她走出卫生间时,在她的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的刚才因悲痛而显露出来的泪痕,只是眼圈四周有点点的泛红。
“我的样子是不是吓着你了。”梅子边说边从手袋里摸出一包硬盒烟和ZIPOO打火机,她如释重负般恢复到刚来旅馆时的状态。
“没有,只是我不知道去怎样抚慰你?”我忧心重重地看着梅子将一颗香烟点燃。
“你还是没什么变化?”梅子吐出一口烟雾,不无挖苦地说道。烟雾在我的面前弥漫开来,张牙五爪变换着各种图形。
“可能改不了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又想起米粒儿那天在咖啡馆对我说过的话。性格这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的确让我费一番脑子,我也同时失去了很多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转眼消失的无影无踪。
“也许?”梅子表示同意。她将烟头扔进烟灰缸后又补充到:“但必要的关心还是要的。”说完,将一双略带嘲讽的复杂的眼珠子钉在我的脸上。
我点头。我不得不点头,我的弱点无疑早在八年前已经暴露在她的面前。从与她在广州的第一天见面起,我根本没有在心里真正关心过她,甚至也不知道她八年来是如何的生活下来的。这一点,让我自愧不如。
“与米粒儿也同样保持一定的距离?”梅子近乎讽刺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此时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不想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我也不想在前恋人面前谈起与现任恋人有关的任何问题,我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替代不了你此时慌张的心境?”梅子随手点上一支香烟,使劲嘬了口,烟雾在她的嘴角处徐徐散开,顿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味道。
我无法描绘出我此时糟糕的心情。
半倾,她才用近似哭泣的口吻缓缓对我说到“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后还说再见有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