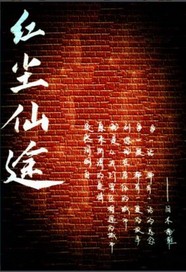吴笙到医馆时,暗影已经睡了。大夫知她是个女人,说她相公体质极好,所以那么重的内伤也没有丧命,不过需要休息调养。吴笙没有说他不是自己的相公,只向大夫道了谢,便蹑手蹑脚地进去看暗影。
他的确像睡了,依旧蒙着面,只是胸前缠了大纱布,手上到处缠了小纱布,桌上还放着喝尽的药碗。吴笙想,很遗憾处理伤口的时候她不在,毕竟,除了美男的脸,身上也很想看......
她见他的一只胳膊露在外面,便替他放回被褥下,动作到一半却停住了,拿着他的手臂细细观摩起来。
很精致,很有力的一只手。吴笙用手指在上面一点一点,像玩自己的银剑一样。又转向看着他的脸,伸手指挑了挑蒙在他脸上的布,她真的好喜欢这张脸!与刚才喝倒千杯红那个男人的妩媚比起来,暗影和岑风的俊美让她喜欢不知多少倍。
这一幕如果让旁人看见,一定会以为他是断袖。
“你在做什么。”
吴笙一惊,险些折断暗影的手,见床来的人醒来,正疑惑地望着她,忙将他的手臂放回去,没好气道:“我看看你的脉搏,还能干啥!”
不过除了胳膊,暗影手臂都缠满了白布,她怎么号脉的?
吴笙站起身,道:“呀,天都黑了,你没事的话,我就要回客栈了!”
暗影想了想,道:“客栈不安全,去岑风的驿站。”
吴笙不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一时失手着了那采花贼的道,她是完全可以抓住他至少也能全身而退的。
暗影了然,努力迂回道:“主要是,那个人太卑鄙,吴笙女侠你这么侠义,跟他斗会吃亏。”
吴笙果然欣然一笑,说也是,她还是去岑风那里好了。暗影松了口气,吴笙却忽然转过身,道:“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安全。”
暗影道:“我是男的。”
吴笙道:“刚刚大夫说,你是我相公。”
“嗯?”
“我的意思是,那贼人可能会把你当对手。”
暗影哑然。
始作俑者哈哈大笑,道了句“自己小心”,就冲出了医馆,渗人的笑声仍久久回荡......
吴笙到驿站时,除了唐宣、岑风还有她恨之入骨的张慕宇,竟然还多了两个人——秦牧川和秦霜儿。
几人相对问了好,岑风解释道,秦霜儿的未婚夫是东远候段顺义之子,而今年秋祭是东远候主持,所以秦家兄妹特地前来参加。
吴笙听人说过,所谓秋祭是允州、济宁一代的习俗,三年一次,在八九月左右举行,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东远候两年前被封于济宁境内,虽然不怎么管朝廷政事,不过身份高贵,由他主持秋祭最恰当不过。不过秋祭通常不会邀请外地人参加,亲家兄妹此番前来,也不过作为东远候亲眷出现而已。
岑风解释时,秦霜儿一直望着张慕宇,张慕宇则缄口不言,甚至不抬头。吴笙便想起来秦牧川说过,秦霜儿曾经为了张慕宇赢龙舟赛而自己倒在秦家龙舟前,这样也是情深义重吧,可惜却要嫁给段——吴笙不知道段顺义的儿子叫什么,只觉得有些悲哀,为什么就张慕宇就没有娶她呢?
秦霜儿眉宇间的惆怅昭然若揭,大家也不好问婚期什么的。转而听秦牧川说起自己的婚事,只道在十月初,与妹妹的没隔多久,岑风也只是笑笑。
秦牧川还是那么温文尔雅,除了微笑似乎未有别的表情。这就是那个在西湖边上为自己披衣解围的男子,就像一幅山水画,安静而美好。真的,他不像商人,不像一般商人。
吴笙与岑风送秦家兄妹到路口,自始至终,张慕宇都没有说话。吴笙听岑风与秦牧川说了些什么,好像提到张慕辰,她也没问,道别时,秦牧川向她微笑,道:“吴笙,好久不见。”
吴笙笑道:“怎么现在才说这句话。”
秦牧川道:“什么时候说都是一样的。我已经跟岑风和慕宇说了,秋祭之后,大家就去侯府赴宴,你也来。”
岑风点头。
吴笙道:“我也去?我用什么身份去,侠女吴笙?”
秦牧川一笑,道:“不是,以岑云的名义。”
岑云?那不是秦牧川的未婚妻?难怪他意味深长地跟自己说“好久不见”,吴笙道:“不,不好吧。”
岑风道:“你说过,你见过绑走慕辰那个人的脸。”
吴笙点头。
秦牧川道:“所以,你必须去。”
原来是为了救张慕辰,吴笙立即答应下来,问张慕辰被抓难道和东远候府有关?
岑风道:“还不确定,所以要去看看。”
秦牧川和秦霜儿告辞离开,剩下四个人围坐桌前,张慕宇还是低头,不说一句话。
唐宣解释道,秋祭在两日后,从子时开始到午时结束,下午便去侯府赴宴。
吴笙询问张慕辰的事,岑风告诉他,他们一路追踪到济宁,本来一直很低调,直到为了找吴笙露面,随后侯府的请柬就来了。吴笙愧疚,都是自己害得他们暴露,好好的找人变成了吃饭。
岑风让她不必自责,说去一趟侯府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在劫杀的黑衣人身上找到了侯府的令牌,这下大家都在明处,反而不好动手,探探虚实也是必要的。
吴笙略懂,然后不明白那些黑衣人为什么把张慕辰抓到这里,当时是为了抓赵麟,现在难道是因为吴笙当日欺骗,所以拿张慕辰出气么?
岑风道,事情没那么简单,甚至有时候他觉得,那日抓赵麟不过是个幌子,而真正要抓的,就是张慕辰。“
吴笙大惊,倾向于认为哥哥在迂回地宽慰自己害了张慕辰的事,所以不发表言论。
而张慕宇,依旧一句话都没说。
吴笙转眼看了看他,一反常态的张慕宇,她没有讨厌的心思了。
那夜月色依旧朦胧,吴笙住在岑风和张慕宇对面,夜很深了,张慕宇的房间依旧亮着灯。吴笙心想,他是在难过么?因为秦霜儿要嫁给别人了。吴笙打开窗,静静地靠在窗边,看着对面。
她记得那日西湖事后,秦霜儿温柔地维护着张慕宇,那份情,宛如日月。虽然吴笙依旧不明白秦霜儿为何喜欢张慕宇那种人,不过眼看着两人一个惆怅一个忧伤,还是有些帮着难过。
这时对面的窗也打开了,张慕宇看见吴笙,似乎怔了怔,然后关上了窗。吴笙心里一鲠,难道他嫌弃见她么?就像她嫌弃见他一样?
吴笙也关上窗,躺下睡了。
对面,张慕宇灭了烛,却睡不着。她在看什么,看自己为何不睡觉么?
吴笙不知道那日将他打晕保护在怀里的是张慕宇,即便知道,也没什么改变。她还是讨厌他,他的地位现在还比不上和她只有两面之缘的哥哥。
敲门声轻轻响起,张慕宇起身开门,门外却正好站着吴笙。
相对片刻,张慕宇道:“你,什么事。”
吴笙有些局促,道:“我不问清楚睡不好觉,所以过来了。”
张慕宇道:“什么事。”
吴笙恍然觉得这时候的张慕宇变成了暗影,竟然惜字如金。片刻,道:“张慕宇你说清楚,你凭什么讨厌我!”
张慕宇一时未解,道:“什么?”
吴笙指着他的窗,道:“你看见我就关了窗,你凭什么不想见我。应该被嫌弃厌恶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你明白吗?”
张慕宇道:“你,就说这个。”
吴笙道:“对。”
张慕宇道:“你不是恨我么,还会在意我讨厌你?”
吴笙轻哼一声,道:“我是恨你,可是你不能恨我,因为你没有理由。”
张慕宇缓缓道:“我有的。”
吴笙瞪着她,道:“还有,你不要学暗影,你根本学不像。你还是做那个厚颜无耻下流浪荡的公子哥张慕宇,不要学暗影。”
“暗影?”张慕宇想了想,笑道:“你是说,那个戴面具的黑衣人。他叫暗影?”
吴笙猛然想起赵麟说的不能暴露,已经收不回来了,便“哼”一声转身离开,回了自己的房间。
“暗影,”张慕宇立在门前,思衬道:“他果然是暗影。竟然有真正的暗影来保护你,吴笙,你到底是有多重要。”
隔壁,岑风站在门口听完两人的对话,此刻收回放在门上的手,摇摇头,回到床上。
次日一早,吴笙已不在驿站,是个人都知道她去医馆了。岑风便看着张慕宇,若有所思一笑,张慕宇靠近道:“得了吧,我知道你昨晚在听。”
岑风不避讳,点头道:“我又没有不承认。”
张慕宇叹口气,道:“我本来以为你的美貌已经让她倾倒了,没想到那家伙带个面具就比过了你,早知道,我也带个面具好了。”
岑风只笑笑。黑衣人与他见面时,没有面具却蒙住了脸,看来,吴笙已经见过他的模样。暗影的话,是不可以让任何人见到自己的,但是,他为什么.....
这时候吴笙刚踏进医馆,她买了些清淡的饭菜,惹得检查饭食的大夫尚且夸她会做事,虚不受补嘛,这个道理哪个人不懂?吴笙十分得意地走进房里,咵地一声放下饭菜,不理会暗影复杂的目光,径自坐到他床边,道:“昨晚怎么样,采花贼找你了么?”
暗影不答,闭上双眼养神。
吴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时的她就像当日在她面前的张慕宇一样无耻,而她应该完全能体味暗影此刻的心情....
“喂喂,别睡了,我给你带了吃的,还有——当当当!”
她拿出一只黑色面具,形状与之前一样,很恰当地罩住双眼,不过没有纹路,活脱脱一块黑铁压了个槽、穿了俩空,笑道:“我昨儿回去的时候让人做的,时间不够,只能这样了。”
暗影这个开眼,还是没有说话。
吴笙丝毫不觉得尴尬,伸手向前却被拦住,便道:“把你那块布丢了——是从夜行衣上撕的吧?怎么说,这也是我的一番心意,而且蒙着布你吃饭都不方便。”
暗影终于揭下蒙脸布,结过吴笙手里的面具,有些嫌弃,还是准备带上。
吴笙赶紧趁机看着暗影的脸,再次暗叹道:“好好看——”
暗影见她痴痴地盯着自己,道:“看够了么。”
吴笙很真诚地回道:“没有。你为什么非要遮住脸?那么好看的脸——”
暗影戴好了面具,吴笙便叹一口气,失落地转而去拿饭菜。吴笙扶他坐好,见暗影手上缠着布,就准备喂他。对方却摇摇头,自己将纱布拆了下来。
吴笙终于皱眉,不乐道:“至于么,你还有伤。”
暗影拆完双手,道:“不碍事。”
吴笙将东西递给他,看着他吃,幽怨道:“我说,就算你总不理我。我也没法对你不好了。”
暗影停住动作,道:“为什么。”
吴笙恬不知耻地说了一句:“我被你美色征服了。”言毕自己一笑,继续道:“等哪一天不再戴面具了,我就再也不离开你。”
暗影咋舌,然后继续吃饭,面具遮掩的双眼低垂,不知在想什么。
吴笙又道:“后天济宁秋祭,你知道么。下午我要和岑风他们去东远候府赴宴,可惜了你暂时不能动。”
暗影闻言,道:“小心。”
吴笙笑道:“你不放心吗?”
暗影不答,吴笙嘟嘟唇,终究自觉无趣,道了句“那我先走了”,便起身向外走去。
“吴笙——”
吴笙回头,对上那双深沉如潭水的眼睛,良久,听他缓缓道:
“我叫漠。”
吴笙沉默良久,重重地点头,然后走出房间。
漠。
如果不知道暗影,就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吴笙走出医馆,就靠到墙上,抬眼看向天空。
他总是不理她,不过,这已经是他所能给的一切,保护,面容,还有他的名字。她觉得心里好重,被什么压得缓不过气,仿佛没有设计好的初见也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都不重要。
济宁的秋祭果然十分盛大,虽然吴笙根本没去看。岑风让她去看看的,说大家都在,也可以试试能不能发现什么,她答应了,却还是没有去。
从得知“漠”字后,吴笙就没有再去医馆,回驿站也不爱说话。平常唠唠叨叨的两个人忽然都不爱说话了,岑风十分地不习惯。好在张慕宇在很快的恢复正常,早早便催着岑风去旁观秋祭了,中午回来时,还十分兴奋的说个不停,比如多大的风筝,多大的灯笼。
吴笙早换好了女装,因为扮岑云,还特地插了几支发饰,开门出来时,张慕宇不知死活地说道:“好像那日龙舟赛的——”
然后他话音未落,就慌忙跳开很远,嘴里气急败坏骂道:“吴笙你这个悍妇!”
吴笙不理他,侯府差人来请,她便如得胜的将领一样伸手挽住岑风的胳膊,柔柔道:“哥哥,我们走吧。”
岑风闻言一笑,道:“走吧,云儿。”
张慕宇气得半死,远远地跟在后面。
吴笙一边走,一边靠近岑风耳际,轻声道:“我刚刚划破了他的腰带。”
岑风一怔,继而宠溺地看着这个出损招的妹妹,道:“他会发现么。”
“我划的后背,除非衣服散开。”
岑风回头,冲着张慕宇意味深长地一笑。
张慕宇刹那间有种不好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