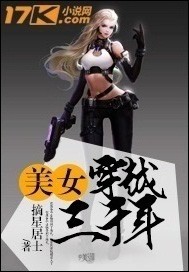“公子,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快点,黑蛇都逃的没影了。”这已经是李斜阳第六次催促了,不过白氏郎仍好似充耳不闻,满腹心事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走着,李斜阳暗想,这可是你逼我的,飞身跃到白氏郎面前,夺过他手中的莲王就跑,白氏郎吃了一惊,急忙追去,截住李斜阳,不想动武,恐伤了兄弟和气,伸出手,板着脸命令道:“拿来!”
“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动凡心了?”李斜阳将莲王藏在身后,学着白氏郎的样子板着脸问,白氏郎倒是想动凡心,不过他深知他不能,斩钉截铁否认:“没有这回事。”
“既然没有,那就没有必要留着她送你的东西。”李斜阳说完,高扬起手,用力将莲王丢进了湖中,白氏郎目瞪口呆,想也不想就向莲王落水的地方冲去,立在湖面,张开一只手掌,打算用仙法将莲王吸上来。
岸上,李斜阳看着手中的莲王,忧虑重重地摇头:“哎,劫数啊!”
白氏郎只吸到一块石头,再看李斜阳,才知道中了他的计,飞身回岸,夺回莲王,藏进了怀中,愠怒地问:“玩够了?可以走了吧?”
李斜阳愁着脸跟在他身后,看来,白氏郎心底情爱的种子已经萌芽,如果任由它疯长,后果不堪设想,他必须想个办法让其断了那个念头才行,目光转了转,一挥袖,天空忽然飘下大片大片牡丹花瓣,故作惊讶地道:“公子你看,义母传信让我们回去见她呢,她一定是知道我们不久前刚从天庭下来,想传我们回去问问义父的近况。”
如果是在以前,白氏郎一定深信不疑,刚被李斜阳耍了一次,不能不怀疑他又在耍诈,伸手接住一片花瓣,果然不出白氏郎所料,花瓣在他手中变成了小石子,利剑一样的目光扫向李斜阳,李斜阳讪笑:“我,我也只是想让你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嘛。”
白氏郎按下不快,给他一颗定心丸:“黑蛇不能不擒,我答应你,收服他后我立刻离开,行了吧?”
李斜阳对他的保证并无多大信心,陷入沉思,萌了芽的小草光用石头压着是没有用的,得连根拔起才行,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仙乐皇朝。
乐小倩听说白氏郎来过,直怨伯邑考不通知她,然后又问莲仙对白氏郎的印象,结果如何,莲仙只用一句话回答她:“十二年的等待,付之尘埃。”
“怎么回事啊?”乐小倩一头雾水,伯邑考因莲仙的话有感而发:“怨相遇,愿相遇,相遇转眼化别离;怨相遇,愿相遇,未相遇此生何益。”
“莫非白氏郎已经娶妻了?”乐小倩也只能想到这个理由了,伯邑考压低声音道:“白氏郎已经是神仙,他们没有可能了。”
乐小倩恍然大悟,挪到莲仙身边,拥住她安慰道:“小姐姐,别这样,缘分的事没办法勉强的,再者,仙凡落叶城青年才俊那么多,一定会有比白氏郎更好的,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
为了分散莲仙注意力,话题转移到了伯邑考身上:“你这次回来有些奇怪啊,走到哪都打着把伞,你怕晒啊?”
“嗯,是啊,这次受伤,身体虚弱了不少。”伯邑考支吾道,黑白无常曾叮嘱他,如果他要长时间在凡间待着,必得撑把伞,否则白天的阳气太重,会将他的魂魄烤化,除非阴天和晚上才没有关系。
莲仙这才想起自伯邑考回来后她还没和他聊过,她一直都想知道他这半年的遭遇,“当初是谁救了你?”
伯邑考轻描淡写地道:“一个表哥,天庭的人。”
“你当初一定伤得很重,所以才这么晚回来,是不是?”莲仙话未落音,乐小倩接着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捎个口信来,我们好去探望你嘛,省的每天为你担心。”
伯邑考心里既有温暖也有伤感,勉强笑道:“是我不对,以后会记住的。”
“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为了庆祝我们又能像从前一样在一起,应该好好喝几杯才是。”乐小倩提议道,刚挽住莲仙和伯邑考的手臂,忽听不远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惊叫,一个宫女匆匆从房里跑出来,刚出门就晕了过去,莲仙三人吃了一惊,齐皆往那个房间跑去,只见惠仁魂不附体地靠坐在床边,恐怖的是他的双腿被一条狰狞的蛇尾取代。
乐小倩蹙眉道;“小姐姐,你们为什么要把这只蛇妖带回来,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
“我,我不是蛇妖,我是我师父手中的佛珠成精,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们相信我。”惠仁惨白着脸辩解,乐小倩嗤之以鼻:“出家人?你一没剃度,二没穿僧衣,你说你是出家人?”
惠仁情绪低沉地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是我师父手中的一串佛珠,我的师父是一位得道高僧,可能是因为长年听他念经的关系,有一天我居然变成了人形,不过我的出现显然不是件好事,差点吓死我的师父不说,也令平静的寺院掀起了波澜,那些僧众他们一个个全都畏我如虎,排挤我,远离我,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师父也因大家的不肯接纳而不肯收我为徒,我很不开心,度日如年,于是一个人偷偷跑出了寺院,化名惠仁独闯江湖,有一天无意闯入一个洞府,看到里面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内丹,听说内丹可以让人增加功力,我想也没想就服下了,没想到这颗内丹是黑蛇的手下奉献给黑蛇的,我却给私吞了,后来遭到黑蛇的追杀差点丢命不说,还把自己弄成现在这副鬼样,我真是咎由自取。”
“原来是这样。”莲仙亲眼见黑蛇非置惠仁于死地,她相信惠仁说的是真的,乐小倩也勉强相信了,问惠仁:“你现在这样怎么办?你刚还差点吓死一个宫女,我怕你留下来会天下大乱。”
惠仁低头不语,他知道他应该离开,可他不知道他这样能去哪儿,伯邑考沉吟着道:“他这样出去被人撞见一样会吓死人,不如先想想怎样让他变回正常人,再让他走。”
“这可难倒我了。”乐小倩摊手,场面静默了一会,莲仙悠悠道:“娘亲常说佛克魔,或许诵念佛经对他会有帮助。”
乐小倩点头,“那就让他留下来念几天经试试,这个房间不能让旁人靠近,必须锁起来,饭菜我则亲自给他送来。”
惠仁连连称谢,乐小倩将房门锁起来,洗去了那名吓晕过去的宫女的记忆,将她哄好后,吩咐她备酒菜给伯邑考庆贺,伯邑考本觉得没什么好庆贺的,但为了不让她们看出异常,将所有的话咽回了肚子。
酒菜上桌,三人推杯换盏,结果都醉了,乐小倩醉了是因为她真的为伯邑考的回来感到高兴,伯邑考和莲仙则因为怀有心事而醉,三人被宫人扶回了房间,夜幕降临,随之降临的是一场腥风血雨。
老天爷赐予世人黑夜,是为了让他们喧闹了一天的心得以平静一下,可有些人却借此之便选择了活在黑夜,沈夜游就是这样一个人,黑夜被他拿来做保护伞,只要黑夜降临,他就会由透明变成索命的幽灵。
沈夜游本是一只胆小怕事受尽欺凌的山羊精,被白氏郎所救后认了他为师,白氏郎觉得带着他行走江湖有所不便,遂把他留在了家里,岂料白牡丹觉得他天赋异禀,又把他带去了圣乐神宫,沈夜游刚开始听说白牡丹要把他训练成杀手是很抗拒的,不过后来知道她要他杀的都是一些十恶不赦死不悔改的恶人,才进了圣乐神宫的门,神宫门徒分为两派,一派在明,一派在暗,在明者负责收集恶人的罪证并加以警告,如果仍不悔改便上报白牡丹,白牡丹则发出诛杀令,由在暗的猎手执行,这时候就轮到沈夜游他们出场了,所谓猎手,猎的不是财物,而是人头。
还是白天的时候,沈夜游随乌鸦精来到了仙乐皇朝,暗中见到他要下手的目标莲仙,当他看到目标是一个年纪轻轻弱不禁风的女子,不由得起了一丝疑惑,往常他所杀的不是满脸横肉的地主恶霸,就是贪赃枉法的狗官,还从没杀过一个女子,这让他有些犹豫,想问个清楚:“她犯了什么罪,令祖师婆婆下诛杀令?”
莲仙被下诛杀令是个前所未有的例外,白牡丹如果知道莲仙是她最好的姐妹的女儿,恐怕快马加鞭收回成命还来不及。
乌鸦精反问沈夜游:“这个女子迷惑有妇之夫,造成人家一家内忧外患,甚至可能家破人亡,算不算罪大恶极?宫主说了,她一定要我盯着你完成任务,否则我们都不用回去了。”
沈夜游听了她的话,蹙眉问:“祖师婆婆这么紧张,这个女子迷惑的人该不会是公子师父吧?”
乌鸦精用力点了点头,沈夜游恍然大悟,再看莲仙,眼中多了很多阴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待夜深,沈夜游和乌鸦精出现在长乐宫院中,躲在墙角的阴影里,莲仙睡了一觉酒醒了些,但头还是有些沉,便来到院中吹吹冷风清醒一下,揉着额头正想吩咐身后的婢女明早记得给乐小倩和伯邑考准备醒酒茶,忽听身后响起闷哼声和倒地声,疑惑回头,一道玄光冲她袭来,好在她反应够快,身子往旁边一歪,躲了过去,还没喘口气,乌鸦精又扬剑朝她刺来,招招狠辣,莲仙不敢有丝毫大意,疲于周旋,可酒劲上来,越斗越觉得力不从心,乌鸦精手中的剑刺向莲仙的腹部,莲仙双手呈拈花指状以仙法死死抵抗,两人立在半空僵持不下,沈夜游见机会来了,猝然出手,一掌击在莲仙心口,莲仙急往地面摔去,翻滚了好几下才稳住身子,直接晕了过去。
天空一道惊雷划过,第一情深从书房出来,被这道雷吓得不轻,“好好的怎么响这么大的雷?仙儿最怕打雷了,快走,快走。”
一行人往长乐宫赶,半道上,第一情深看到半空中两道玄光一闪而逝,还以为何仙姑来看女儿了,可转念一想,距离何仙姑出关的日子还有半个月,如果没什么事她不会提前出来的,带着一丝疑问赶到长乐宫,眼前的景象差点令他窒息过去,宫女横七竖八地倒在眼前,莲仙则仰面躺在不远的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第一情深仓皇跑过去,扶起莲仙,探了探她的鼻息,已经气若游丝,悲痛欲绝,嘶声冲宫人喊道:“立刻上邀月宫通知皇后,快!”
他一心急却给忘了,闭关的人不容受到打扰,否则恐有性命危险,红烛接到皇朝的急令,很是为难,一面担心何仙姑受到刺激,导致走火入魔,一面又担心莲仙延误救治,如果有什么危险,她担当不起,一番艰难抉择后,还是进去婉转的将事情转告给了何仙姑,何仙姑一听当即乱了心神,急忙稳住丹田之气,最后仍不免受了点伤,不顾自己身体不适,火急火燎下了山。
莲仙被连夜送到了大佛寺,伯邑考和乐小倩第二天一早得到消息,魂都吓没了,匆匆出了宫赶去大佛寺,大佛寺重兵把守,何仙姑在大殿为莲仙疗伤,殿外,一班僧侣为莲仙诵经祈福,莲仙受伤的消息由香众传了出去,很多百姓自发加入祈福行列。
白氏郎和李斜阳追了黑蛇一夜,可是黑蛇太狡猾,跑到百姓家里附在凡人身上,等白氏郎想辙时,他又跑得没影了,白氏郎二人忙了一夜,累得不行,进了一个茶寮喝茶,由此听说了莲仙的消息,白氏郎凳子都没坐热就站起身,李斜阳死死按住他的手不放,两人对了个眼色,都没心情喝茶了,离开茶寮,无人处,李斜阳拦住白氏郎,论武力他是打不过白氏郎的,只能和他讲条件了,“我知道我是拦不住公子的,公子如果非去不可,发个誓如何?如果你动了和她相守之心,那李斜阳最后便不得善终。”
白氏郎黑着脸瞪着李斜阳,心想你可真行,想出这么绝的方法来约束我,不悦地问:“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李斜阳圆滑地道:“我只是想趁此机会证明一下我在公子心中的地位。”
白氏郎扯过他的衣襟就走,“不用发誓了,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定力,既然我可以脱身一次,第二次也一定行。”
他说的如此笃定,缘何最后还是泥足深陷,不可自拔?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心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抵御一切诱惑,可是他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情字,就算心如铁石,最后也难免跌入爱池,沉溺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