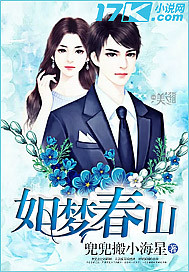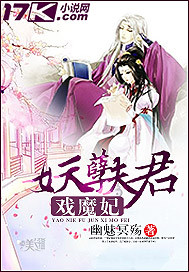回到房中,司青关上门便忍不住大笑起来,“姐姐你真行,刚刚那个族长,一开始凶的像头狼,没想到最后被姐姐说的像霜打过的茄子,脸都气绿了,我看着他那张脸,我就想笑,姐姐真是……”
“那个族长只不过是个小丑,空长了一把年纪,却是个地道的缺心眼。要不是夫人派人去他那儿告状,他才不会来呢”司潇饮了口茶,悠然道。
“姐姐怎么知道是夫人派人去告状的啊?”
“来湖州之前,我早已打听过钱家底细,钱家是百年名门不假,不过真正的钱家名门子弟远在河南做官,这钱其不过是正统钱家的旁支远亲,早年一穷二白,不过是在族谱上有个名字,连年关祭祀都轮不上他的,虽说之后他靠贩盐起家也算是赚下一番家业,可士农工商,商乃四民之末,即便他富可敌国,也终被那些名门长老的看不起,更懒得管他们家的事,刚才你注意了没,那个族长和他身边的人头上大汗淋漓,按说这五月的天,没理由如此之热,再加上他们身上都沾有大量灰土,一看便知是经过一番长途跋涉而来。我们到钱府方才几日,消息怎可能传得这样快?所以我敢断定,是夫人不能与我正面交锋,而找他们去搬救兵。即是如此,他们当然希望这事早了早好,根本无心跟我纠缠,否则的话,以那位族长的威望和地位,哪那么容易放过我。”
“那姐姐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夫人此番落败,必不会善罢甘休,等着瞧吧,以后还有好戏看呢”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七夕。傍晚时分,钱府的丫头们纷纷出的院来玩,司潇从小生长英国,并不知道七夕是什么节日,又不便询问,怕露了马脚,而司月从小被辗转变卖,终日挨打受骂,更不知七夕了。两人只好跟着贴身丫环佩弦一起玩闹,听她们言谈,倒也大概明了了七八分,正玩到兴头上,只听外面掌门的老婆儿们来报:二爷回来了——
“钱家老二?他不是在学里念书么?” 司潇不禁心生疑虑,忙拉住佩弦询问。“二少爷什么时候说要回来的,怎么没人说起来过?”
“大约十天前,二爷写信来说,乡学附近闹起了白口糊,地方官为了学子的安全,派大夫给他们检查了身子,没有问题的就让回来,等避过这一阵子,再继续课业。”佩弦一边应道,一边急急拉司潇向前厅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