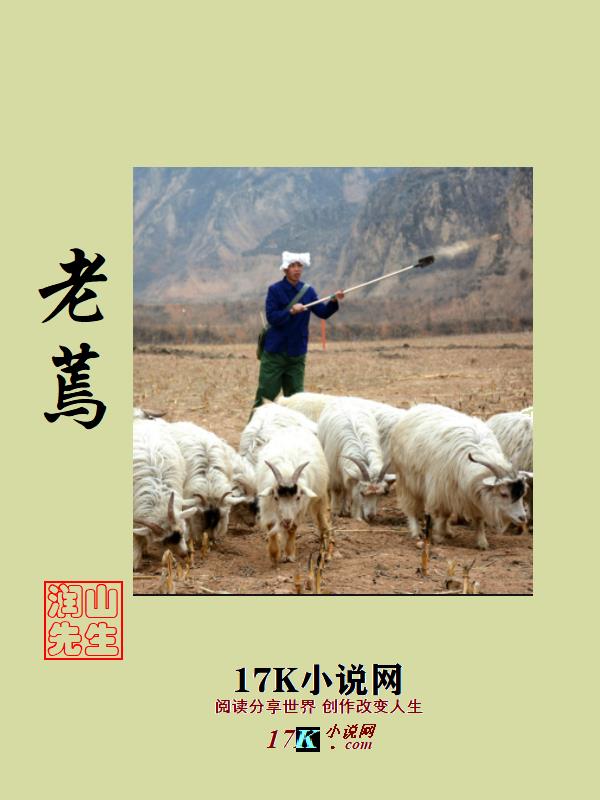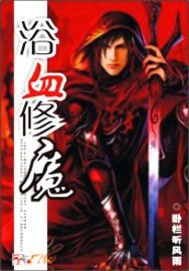今天是莲女嫁人的第三天,按理说是该要回门的了,可是婆婆不太满意,媳妇边干活边哼戏文的样子,一没有人就会在那里管自己念叨着:“不要个脸的。”
第四天,新媳妇起晚了,不知道为什么婆婆看到就是一副怪脸,要笑不笑,要骂不骂的脾气,黑暗着管自己进进出出。而莲女丝毫不经意,大概是昨晚闹腾的多了,吵到家里人了,这时莲女又在丈夫身旁腻歪了一阵子,婆婆见了更是一脸的坏脾气,彻底的黑暗了。
“不要没正性了,赶紧洗洗弄弄,帮忙做饭。”
“...哦...来了...妈我来做吧!你去叫小叔子们,小姑子们起床,该上学了。”
“...霸道胚...”?这婆婆扭过脸子,黑暗着低语着;好似极其不爽的跟自己较着劲儿。
“还不起来,还不起来,想让我去拿铁烫烙了你们一个个是不是?赶紧给我起来!”最后几个字甚是大劲儿,叫得楼下厨房的莲女,乐的一笑,摇着头。
“妈,你最好了,怎么今天不是大嫂叫了呢?大哥好福气,这么个漂亮人,白白可惜了了的。”小小叔这样说着。
“你个小人没规矩,信不信我嘴巴给你拧下来?”
“哈哈”隔壁小女儿听着笑出了声,老四洗完了头,正站在那梳着。
“好好,我起来。不要再这样了,被老四都看光了”
“谁要看你个小不点?笑死人了。”
“啊...妈他说我小?...”
“闭嘴吧你,没正性。”
王母收拾了一些红薯干,面饼,放在了簸箕里拿到屋外晒着。新媳妇莲女此时也做好了饭,正摆着碗筷朝楼上喊着:“吃早饭了,还不起来?小心爸回来看到,拿起竹毛丝就找你们去哈!”
这话一说完,只听楼上“呼咚咚”地就跑了下来。
“大嫂,四姐要打我。”?小小叔子,卖乖着。
“咦,真是叫人笑话了,早知我就真的打得你哭,你信不信?”
“我才不信呢!小心以后嫁人了天天被姐夫欺负,那就高兴了。”
小姑这时也说话了:“好了啦,赶紧洗完脸,吃吃各自忙吧,等下妈见了又得骂了。”
莲女见状,叫了丈夫和婆婆,自己则就躲在厨房收拾,且等到大家吃完,去忙了,公爹也回来了,这才把热上的米粥添了饭端上了桌,而自己只是端着碗,坐在灶坑前,望着火苗拨弄着没有几根菜的稀粥,将就地便吞落下肚去了。
这一年农民可以拥有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权了,那时候为了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只需要抓阄就可以,每个人都有三次机会,以最后一次为标准。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某些“眼红病”之人,借题发挥,跟你大闹“关系论”吵的不可开交。于是这样一来,自然也就还会有人不公平,倒是也把这种气,归在某个人身上。
莲女收拾完了碗筷,跟着公公,也下了水田,顺便带着姑子在田的四周,钊着田埂。莲女弄完一圈,径自挑了猪肥料(猪粪,以及垫在猪圈的稻草,长时间不清理,这些稻草就会发酵,皮肤不好者得用猪牙子草捣烂敷了解毒)
那些上下田间里忙着相同活的人,一看莲女这能干的架势,直夸着这个樟树岭子村的女人。公公性格脾气稍微好些,有点文化,会算账;思路也清晰,对于他人的夸赞,自己则就卸下犁扒子,靠在一边,就蹲在田埂上抽起了旱烟。那一锅一锅的烟草烧完了,打在水里,那水蜘蛛见了也跟着来,打着圈圈去闻那烟草的味道。
王太老吐着烟圈,左眼眯起一条缝,还时不时会颤动着,这些举动好像全都看向了新媳妇所在的位置。抽完最后一锅后,王太老起身,将那烟杆子绕在裤绳上绕了三圈,很是自然的斜插安放着。随后便吩咐着,叫让跟着嫂子学学那个力气。
就这样,第一份的犁田,松田,扒粪的工作也就做完了,可是接下来的几天,这一行人都得如此做着些类似的活计。
而章家的父母,心里念叨着该回门的人却迟迟没有动静,章父宽慰着:“芒种了,许是要帮忙做事情了。”
“也是,我们家也该弄了,明天我就去请人去。”
“没事,第一步的活,我们自己干,叫上小儿子,也该让他学学农活,将来好过自己的日子。”
一连几天的重复忙碌,莲女丝毫没有怨言,反而依旧是那么的单纯,天真惹人爱。在农村之中,好的人会看到别人家新媳妇的好,可是也有人喜欢说三道四,就怕别人家的小日子过的很滋润。
这天师傅来了口信儿,让莲女回去排戏,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娘家这边也出现了农活忙不过来的情况。经过一番思忖之后,莲女连夜就回到了樟树岭子,还好天气未晚,有些亮光,骑着那辆载重自行车就风呼呼的走了。
终于章家的田种完了,也确定了开锣的时间,新郎官瞅着时间也快到了,就也带着礼物上了丈母娘家的门,接了新媳妇回家去。
章家父母和姐姐看着,有的很欣喜,有的面无表情,就一齐站在了那路上,眼望着这两人一并骑了车去了。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碰到养路的同村哥哥,莲女也是那般亲切支应搭话着。可至于家里的氛围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你听“哎我说婶婶,现在的姑娘都是这样的,你管她什么法子呢?让她谦呗!怕个什么劲儿。”
“是下面大嫂子啊?忙不最近?”莲女从厨房的小门里进了,跟族里妯娌大嫂说着话,只是招呼一两句,并未说旁的。就见得那人面笑皮不笑地歪着嘴朝王程氏撇过去脸子;“喽!你看。”说完还扭动了身子,仿佛在模仿南极的动物。
而那王程氏马上缩了一下下巴,暗示他大嫂子不要太大动静,小心人家发现。最尴尬的便是,这一幕刚好被莲女看到,好在莲女并未察觉出什么,反而是提着一袋子荸荠,笑脸相迎着:“大嫂嫂,这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采了很多,甘甜可口,您带下去给两孩子尝尝。妈我来做午饭吧!”
“行,那你做饭,我去打下些菜籽,顺便把那些蕨菜,毛竹笋处理了,知道怎么弄吧?”
“知道的,腌制,晒干各弄一半。”
“好,那你做吧!”
夜晚,忙碌了一晚上的一家人,早已睡下,可是王志德却一直在打扰着莲女,老时的胚土房,其余的房间都是用木板子隔成的,自然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这下可烦死了王程氏,躺在床上,单手压在头下,脑海里直想着插秧时期,乡民们说的话,和自己对这个媳妇的印象,让王程氏心里实在不爽。听着那房里的声音,更是气的鼻息变得沉重了些。而王太老不明所以,以为是听得那声儿,自己在那较着劲,顿时就有了反应,这一下子就更让王程氏甚为反感。冲到新夫妻的房门口就起了动静,只见她拿手用力拍着门板,大声吼叫着:“不要个脸的,屋里头少爷,老爷还在,你个贱货在这会子夜猫上炕?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听到这个动静,楼上的起了,门里的也亮起了灯;楼上的在偷笑,楼下的没几句话都只是被王程氏一人骂了回去。只听得:“不要没正性,姑娘家整日妖媚狐狸样儿,干什么啊!”
莲女不敢做声,毕竟妇道人家,又是新媳妇自然要受得些家教严格些。只是私下里埋怨丈夫不体谅,明明告诉过他自己“好事”晚了一周,可是这个德德鬼,仍是管自己上手,如今这一通骂,让莲女着实委屈。倒在一边就开始后怕“是不是以后自己要永远受这种没理由的谩骂?” 她在担心自己内心原本所想的宁和。
第二天,莲女很早就起床,做好了饭,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部做的非常利索,不论是喂猪,还是鸡鸭鹅都喂的很有模样。大概是学艺的人,比较注重形象,打扮的也很是漂亮。莲女肤白、唇红润;乌黑亮丽的头发,在那个没有任何洗发水的年代,只靠清水“油枯饼”洗洗就那样柔顺的还真不多见。一件鸡心领的半袖内衬,外面一件中长款的红格子西装外套,下身是一条侧门襟的黑色阔腿裤,配上一个亮白色的发卡扎成了公主头,显得整个人格外出挑,这若放在别人家里,估计得受多大的恩宠?可是王母,见了只是一口痰吐在了她的平底皮鞋上。莲女这下委屈了,假装很坚强,拿着锄头拐出了平坦,就蹲在那氺洞上,清洗着那污迹。
此时天并未亮透,为了不让婆家人发现自己的狼狈样儿,也就捏着胆到千里岗下的田里忙去了。
时至中午时分,想念着一家人的午餐,莲女脸上带着微笑,可能是觉得干了一天活定会被夸奖的缘故,怎奈快到家门前了,却停在了外头。
“你看看,这不要脸的喂,一大早起来不声不响,竟然打扮地那么狐媚,真不像个人。”
“不要这么说,各人的脾气。”
“你懂什么,这叫做不入流,每天睡到很晚才起来,管自己脸上光鲜,入门还没几天就回娘家种田去了,这么不知道一二的,真是脸都不要了,也不知道个现世。要不是德德人看中,恩...要我我是不要的,我少了他一个我还有七个,我倒是怕了什么?...真是倒霉啊,结命....”
“.....仓.....”
此时莲女,心里好似有一面“血手印”的大锣,响的是那么的地动山摇,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她倒是一直在做着好媳妇的模样,可怎么就落了一个这样的骂名?此时莲女只觉得肚中生疼,背着的锄头也掉在了地上。好一个婆婆娘,得知后非但不担心,反而更加挖苦了起来,直骂她:“饭不会做,就知道狐媚。”
莲女痛的差点晕倒,可是这一记话,让她脚尖一掂眼露凶狠直勾勾望着那两个“狼狈为奸”的婆娘家,莲女疼的冒汗,一句话没说就钻进了卧室,倒在了床上。
终于第二天了,莲女躺在床上,换下来的被单衣物,浸泡在盆子里,虽然也是红的,但是那血迹却很明显,分明不是一种色泽。本想缓一缓吃点饭,就去洗了,可是人家又自顾自的发了疯叫道:“好啊,真是来当菩萨娘娘了啊,这拉了血的、还要我来给你洗?”
没办法,莲女只好自己爬起来,捧了那木盆下到了溪里洗了,你可别说,虽说是五月,可是高山脚下的溪水不比镇上,寒凉冰彻骨的很,刚对于刚坐上胎的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报复性的打击,可是没奈何只得强忍着心酸泪了。——又好似祥林嫂诉说无门。
过了一日,丈夫和公公也都回来了,正要吃饭,就听见王母对德德鬼说:“你这个老婆要好好给我管管了,喽...去啊。”
莲女见那样,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管自己把炒好的菜,一碗碗摆上桌,自己则就端了一碗有焦锅巴的饭,随意夹了点菜,就到厨房吃了,而那一帮人就管自己好好端坐在正厅有说有笑的吃着。
“不要说我冤枉了你,谁叫你管自己吃,不管我们?这又为何自己委屈了?真是笑话,这样的婆娘家我本就不要,德德人,你给我听好了,除她一个,我还有七个。”
这句话,莲女隔三差五就能听到,可是肚子一直不明白所以,也就担心的回到了娘家,想说找了医生去看看究竟。章母是知道的,女儿这是有喜了,从医院出来,就回到家杀了鸡,抓了鱼就做上了一顿好吃的。饭没吃几口,那凶神恶煞的女鬼,高凸的颧骨头毅然坐在了门口,嘴里说的竟是糊涂话。
“这个女儿,别的都没毛病,就一点不知道安分检点。”
“安不安分,检不检点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在村里向来是最好的。”
“我也没说不好,不过呢!本是不太认可的,但好在娘家近,随时可以来,这样也好,且只叫给她吃三年,管三年,去去些个气质。”说完,王程氏就掏出手帕在那扇着风,气呼呼就走了。
望着那人的背影,章母也气坏了,可是看在小女儿还在养着的份上,只得自己锤了几下胸口,也就算过去。章母定睛望向门口的台子,心里想着:“定是受了冤枉了。”?定了定神,章母关上了屋子,就到了供销社,拿着糖票给开了一斤红糖,又从梁上挂着的竹篮子里掏了六个鸡蛋,一股脑儿地全煮了;放了红糖给小女儿端了去。莲女见状,生怕知道自己受委屈的事,也就只好忍着,故意挤出了微笑应和着。
“哇,这么多啊,妈您吃!”
“我吃什么?弄了就是给你吃的啊!你吃吧!早些年怀你们的时候,我也是吃腻了的。”
将养了几日,村里的大戏又开始了,莲女觉得也好了很多,热闹场的都拒绝了,只演了几场类似《碧玉簪》《孔雀东南飞》的文戏。唱词是这样写的;
"...女儿是 娘亲生来 娘亲养,有长有短总好商量,女儿若有事做错,娘呀 你也肯来原谅..."
“...自古道槽糠之妻不下堂。兰芝无辜被你休?你明白兰芝无过犯,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口?...”
戏完了,可是现实中的“戏份”永远在增加,除非哪天进了土,不然人类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杀青,一幕幕,一场场,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正在无休止的侵蚀着那被高山圈困住的那个人。
转眼间,几个月了,孕妇的害喜和特殊的胃口也重了许多。一出红糖记,让莲女彻底对婆家人失去了希望。
“妈,我要吃红糖水,给我泡。”幸娣说
“就在那小桌上,自己去泡,没正性儿,没见我忙死了吗?”
“哪有?”
“不就在那放着吗?”
小儿子立马叫起来“大嫂房里有一罐。”
“什么?这霸道妇,竟然学会偷东西了。把她与我叫回来。”
四妹听了,立马跑到后面菜地叫了去。
“你好啊,家里总共就这么一罐红糖,还是前些天我老大托关系换了两斤来的,相必你都拿去吃完了?”
“什么红糖?妈我不知道啊”
“就你房里的”王母说着就把那罐红糖摆在了小桌上。
“这不是我娘家带的吗?”
“好啊你,都带回娘家去了?算了,不要解释了。晚上再来跟你计较。”
平白无故地受了冤枉,可怜的孕妇就那样站在那天井里边,就连做饭的活计也不让了,纷纷拿她当成了贼。
可是不争气的孕妇肠道,近日以来特别想吃那菜粿,不论是干萝卜片加豆腐猪肉,还是就酸菜豆腐,哪怕是芥菜梗子包的,这人都能吃下去个四五张,碰巧这时王母在厨房做了,正在用油煎,闻着那个香气,莲女似乎忘了刚才的委屈,又笑着跑了过去卖着乖着:“妈,今天晚上吃粿啊!我也想吃,能不能帮我做几个?”
“你以为今年面粉得了容易啊?这一家子六七口人呢!想吃自己做去。”听完这句话,莲女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转身跑进了老房子里,坐在了奶奶睡的那间屋子,那个眼泪使劲地往下流,哭着哭着也就不顾及什么就睡在了那床上。
打此次事件以后,老大家就开始分了家,只不过分家了还得忙活婆家的一日三餐,等不方便时只用做午饭,莲女没办法只得听之任之。
王太老认了上面的亲叔叔做了儿子,也就继承了叔叔家的所有房子(一间后四合院天井房,和一间土木结构的老屋)以及田地。分了家之后,虽说所有吃的有人提供,但是均按照了份数交办了的,毕竟有人做过贼,心里头定是害怕了些,谨慎了些。
莲女又回娘家了,对着娘家妈一说不给吃饼的事,章母立马就打了面粉,生火烙了一大菜篮子,有豆腐酸菜馅儿的、胡萝卜肉末馅儿的,还有酸萝卜,酸豆角馅儿的,看着莲女吃的一个欢,章母笑了:“不给你吃粿,回家就是了啊!什么鬼人家,吃个粿就穷死了吗?真是不懂事!”这章母说话像极了毛山岗子头头上的外婆,风趣幽默,把莲女和章父也逗得笑出了花。
第二天,检查完,提着一大篮子的菜粿子,就往源头里去了。到了家,也管自己填了火做了饭,热了那馃子,好在章母心细,备了几份调味的,还有两块大洋。
闻见香味的几个小叔小姑子,无一不馋的,推开了隔门就来到了老屋子(这是为了方便照顾亲叔娘的,只不过对面黄金坊亲儿子家住的习惯些,也就不见照应了。)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着,可是莲女并没有小气,分发着就给了去,还特意端起一大盘子递给了婆婆,虽说没有被谢恩,但也算是出了气,临去时说了:“我妈给了我两块大洋,虽说这钱我自己享用就是,但是你们家的柴,我定不能用,给你们一块,就当是我近日里填了烦。”
王母见着一个叹气,管自己喝了一大杯冷酒,而至于那些个饼子,她是一眼都懒得瞧,直到第二天早上,偷偷拿了两个边吃边走去了下村的弟弟家了。
时间又过了几天,这时门上来了一个妇人,大手大脚,头发凌乱,面容俊黑的女人;而手里捧着的竟是那一罐子红糖,一经细问,才得知原来早先那一罐子红糖是叫小儿子偷了去,给了班里的一个女孩儿了。这下,可把王太老气着了,说着便要拿了家法让其受死,好在那妇人急忙劝阻,才免于一顿“血雨腥风”。
可是这个小儿子仍然不知道悔改,那些年王太老做账,是有些家底的,每周上学前总是见王母一块两块的塞,愣是不知道这些钱叫他拿了去请了客,最后还倒欠了24块大洋。东窗事发之后,债主找上了门,全然是一帮不做人事的人,斜眉竖眼地,言语之中也不尽客套;王太老气的,一个拳头就砸在了小儿子的脸上,可是小儿子志相到能忍,一个吭声也没有。王太老直接火死了,管自己拿了那把生铁剑,就打在了志相的后背,顿时一道紫乌就凸显了出来,吓得旁人直接泪崩,赶紧捂住了口鼻;王太老歇斯底里地怒吼到:“你个畜生,这么多钱你一个中学娃娃子,你给了谁?”
“我不能出卖朋友”
“好啊,你倒是会来这一套,讲起了义气是不是?好啊好啊,今天就让你知道个哪样死。”说话间,就背下一捆麻绳,直接将那中学模样的人儿就那样给捆绑起来吊着,曲起双脚刚好可以放两块砖头,王太老又取了一片青瓦放在其脚下,倘若那瓦片碎了或是乱动,定然叫其生不如死。
莲女从外面回来,挽着志德刚要坐下喝点水,就听见正房里哭闹的声音,一进去便看到老妈瘫软在地,哭的嗓子全哑了,两个妹妹也是哭,只是扶不动,陪在了身边。至于下边的长辈虽说在旁边也没法子,这个王太老要动家法又有谁是对手呢?只得硬生生看着他被打。
莲女上前,只见这个小叔子脸上有血,背上衣服也破了,还能很清楚的看到一条条,一道道血口子,莲女用手摸了摸志相,咚的一跪地就开始了求情;只见她是这么说的。
“人家说反哺的乌鸦知情深,虎毒尚不食子,爸,您就可怜了吧!”
“你个不守规矩的孕妇人,是不是也要把你休了去?”王太老依旧怒吼着;还又重重一打,敲在了志相的肩膀上。莲女又说:“爸,您心里尽管不如意,可是事已即出,打出人命就晚了。”
“不要啰嗦,起开。”王太老举着手就要打,莲女见状吓哭着,立马顶着那手,看到王太老也是慌了一下,莲女立马又把那剑夺下扔出了门外。
“爸,爸,我的亲爸,志相倘若被你打死了,也还好,能痛快一场,大不了您就得进了去;要是不打死,以后弄得个残废,你叫他未来的日子怎么过?亲戚朋友们见了,老乡、奶奶们见了又该怎么说?”
王太老坐下了,恨恨地喘着气,忙招呼着志德装起了烟锅子。莲女乘胜追击:“快、把人放下,都没气了...快解开绳子,再晚了人就没了,爸您以后老了可就少了一个上坟磕头的啦!....”这话一出,王太老立马着急地吩咐着解了那绳,没等救下,他自己倒也瘫软地被扶进了房。至于那个婆婆,也拼命作揖着,瘫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拜着。莲女心想事情过去了,也就想着办了一件好事,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可是一站起来,觉得下腹一阵痛,在丝毫没有被发现异样的情况下,自己拐着腿叉开着步子向老屋移了进去。
事后,志相躺在老屋的另一间房里,莲女熬了糖水,志德正喂着,莲女不忍心就劝着:“志相,以后不再办错事了,好好学习着,将来找个好活,你就出去吧,男子汉有本事,自然少不了你风光体面的。”
是啊,只要有本事,也就不怕些个“妖魔鬼怪”,竟是风光体面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