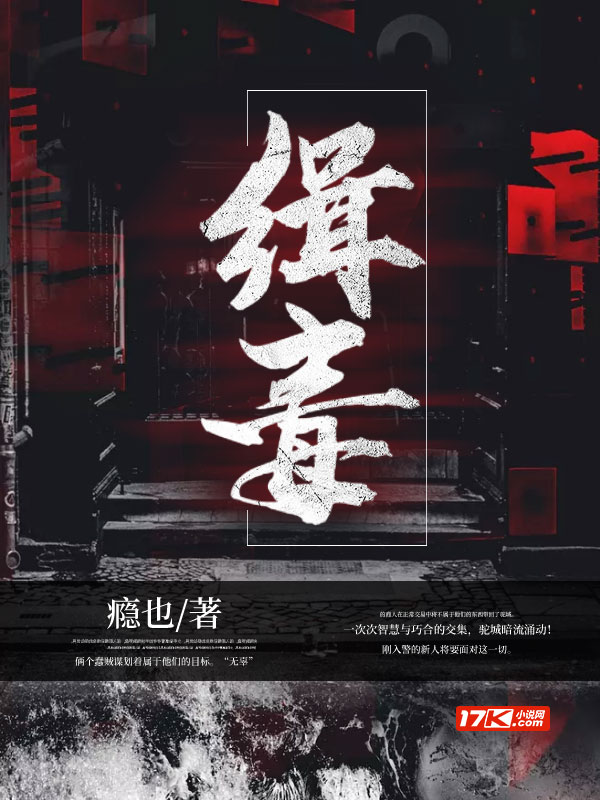最近小公子的话特别多,而且说起话来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前一秒还在问山上如今开的什么花,后一秒就闪着眼睛问我:“穗岁当时怎么偏偏变成我的模样?”眼里闪过一丝玩味。
我一面摆弄着折来的梅花,一边说:“自然是因为小公子好看,我还是一朵花的时候就常见小公子,后来得以化形,也日日见公子来上香,你是所有香客里长得最美的,而且见得多了就记得了,化作你的样子也比较容易。”我没瞎说,我还是花的时候就常常见到夫人带着小公子来上香,小公子一般只去主殿上香,上完香便在莲花池边饮茶作画,等夫人一起回家,我打趣道:“说不定你还画过我呢,在我还是一朵花的时候。”
小公子招手让我去架上取他的画,说笑道:“兴许那一堆陈年画作里就有你。”
我将画一张张摊开,终于找到一张画莲花池的,便喜滋滋地拿去给小公子看,“公子你猜哪个是我?”小公子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摩挲着画上高高低低的莲花。
“公子?”
小公子才从失神中缓过来,干笑几声,指向其中最美的一朵,“我猜穗岁一定是最美的这一朵。”
我很满意小公子的话,虽然我也不确定这一朵是不是,说不定在小公子画画的时候我还没开呢,但那有什么关系,我一定是莲花池中最美的一朵啊,不然怎么就我化作人形了,我们做花的就是要绚丽地开才是。
我坐在案上,和小公子四目而对,随即都展开扇子抿嘴笑了。看吧,我们俩果然越来越像了。
“穗岁,等我死了以后就把我埋在南山吧,我还想看合欢树开花呢。”小公子眉眼弯弯的,就像在诉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要想看,你自己坐马车去看,好好活着,别想着死了以后坟头上的事情。”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是滋味,猛地将扇子一合,扇尾的流苏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度,“要是一声不吭地死了,我就把你埋在穷乡僻壤,四周也没个什么鬼做伴。”如此赌气地说着,就变成小公子的样子走出门去。
倒了寺庙,恭恭敬敬地在主殿上香,随后便走到内院。
内院里,几名扫地僧在青岛着积雪,藏经阁里满是木质香,通过小窗窥见济源正在抄写经书,我轻手轻脚地进去,坐在济源对面的蒲垫上,也不搭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翻看佛经或是给济源作画。无需言语,这是半年多来我们俩之间的默契,寺庙内外都在传言城东李府公子妙手丹青、城北开元寺和尚深谙佛法,二人一见如故,戏称兰城双杰。
如此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等到快吃斋饭的时候我才准备离去,走之前我问济源:“开元寺里香火不断,可是真正解救了什么困苦之人了吗?有刽子手满手鲜血地求心安,有母亲一步一叩求子女平安,有读书人求取功名,有商贾求取家财万贯……这些零零总总,佛能分的清吗?如果佛真的存在,你的佛法又真正解救谁于水火?”
“佛法超度死者,慰藉生者。”济源站在案前如此说到,夕阳给他镀上一层金边,看着倒像一位真佛。
“逝者已逝,超度与否又有何干系?生者已经失去,寥寥数语的慰藉,又有何用处?如此这般,佛法怎么不令枉死者往生,作恶者不再作恶呢?”我的眼里都是眼泪,济源将头埋得低低的,我见他如此也不再纠缠,只是走出藏经阁。
等我回去的时候,小公子已经死了,仅留下书信一封,我没敢看,只是按照小公子的要求将他葬在南山的一棵合欢树下,刻了一个小小的墓碑,上面写着穗岁之墓,从今日起,世上多了一个不再积病的李居安,少了一个李府的丫鬟穗岁。
我三言两语就能将穗岁的暴毙搪塞过去,一定不会在李府引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小公子不在了,我还亲手挖了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坟,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堵得慌,还在思索这是一种什么情绪的时候,眼泪就大滴大滴地落下来。“小公子,现在还是冬天,等合欢树开花了,我再和你一起看。”
在坟前坐得腿有些麻了,便游荡在长街之中,春节的气氛还在,但总觉得没什么滋味,“或许我该去喝点酒,公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喝完酒就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么想着,我就走进一家酒馆,请小二给我来上几壶好酒,一直喝到李府派人来寻,我才晃晃悠悠地坐马车颠回去。夫人见到我的时候又哭又气的,用帕子拭泪,将我拥在怀里,听我一遍遍地叫着穗岁,气得直跳脚:“居安,你自己什么身体不清楚吗?好不容易好点了,你居然跑去喝那么多的酒,你是不是要气死娘亲啊。”这么说着,夫人的眼泪就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紧紧搂住娘亲,嘴上说着:“娘亲,娘亲,穗岁没了,穗岁没了。”
第二日日上三竿的时候,被一声声木鱼声和诵经声吵醒,我寻着声音走去,见以济源为首的一群和尚在做法事,我蹲在济源的身边,问:“济源,这样死者就可以超度了吗?”
木鱼声只是一顿,随后又敲了起来。
济源在李府做了三天的法事,我在坐在他的身边连续抄了三天的佛经。
济源待在李府的最后一天,我提着一碟果脯和一壶酒去他的厢房,没头没脑地说着:“小和尚,穗岁没有了,以后只有居安小公子了。”
吃了很多果脯,但酒一口没喝,我絮絮叨叨地说小公子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事无大小地说,最后说得累了,就含着果脯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被人抱上了床铺,又掰开我的嘴。
第二日早上起来时,嘴巴还是甜甜的,桌上放着一颗含过的果脯,济源却早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