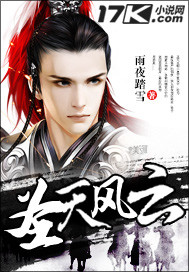周蛮一路向北,越过一座高峰,迎面而来的是一阵狂风。风势甚急,仿佛从风伯的口袋中直吹过来,将他吹得踉跄躬身。他迎风而立,顶着风势艰难前行。越向前风势越猛,他举步为艰,终因脚下不稳,摔倒在地上。他方才落地,便被强风吹得向后翻滚,跌跌撞撞滚出数丈,险些从山峰上滚落。
他好容易再度起身,双目中非但没有怯意,反而越发激昂。他狠吐了口唾沫,咬牙咧嘴,露出一丝不同寻常的微笑。眼中射出浓浓神光,透出无与伦比的执念。风越是强,他便越想从此翻越。不服输的倔强本性支撑着他,原本只是由此路过,如今却变成一场与风伯的决斗。
他每踏出一步便要喘息一阵,强烈的风压从他面前掠过,不但撕扯着面颊,还夺去他身边空气。他呼吸艰难,体力渐衰,先是双足前行,后改为四肢撑地。双手紧紧抓住山坡上的草,一寸寸向前爬行。幸而山上植被每日承受如此狂风侵袭,草叶坚韧,根系深结,勉强撑得周蛮身躯。
他双目紧闭,就此摸索前行,无论什么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耳边嗡嗡轰鸣,仿佛有十口大钟在他脑中敲击,震得他头痛欲裂。
忽地,他四周平静下来,仿佛整个世界在这一瞬停住。他只觉全身酥软,说不出的无力感从心底涌出,流遍全身每一寸神经。他无法动弹,连手指也抬不起来。身体完全静止,似乎连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动也完全消失。
仅仅只经过一瞬,却好似长达千年。他心中突然涌出一种想法:“我,已经死了么?”就在这想法出现同时,他还来不及为死而有所感触,有所悔悟,有所不甘,四周的世界恢复以往。
声音传来,那是熟悉不过的风声。与之前不同,这次风从下来,强度也弱了很多。
他忽地张开双眼,发现自己竟身悬半空,急速下落。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翻过山巅,从悬崖上堕落。神智回归,恐惧感随之而来。他望着身下深不见底的深渊,慌了手脚,在空中苦苦挣扎。可惜这悬崖成探头式,从顶端下来,落得越深便距离崖壁越远。此刻他距崖壁至少有两丈,任他手长撑天也无法攀到。
他带着惨叫由天而降,直落入下面深潭。轰隆一声,平静的潭水向下凹陷,仿佛被敲出一个幽深的洞。水波回返,激得水花四溅,白浪向天空翻涌,好似从水底耸起一座雪山。
周蛮一头砸在水中,就此沉将下去。从百丈高空跌落,水面如大理石般坚硬,直把他撞得七晕八素,通身火烧般疼痛,四周却是冰冷刺骨。这种冷与疼的诡异结合令他倍感煎熬,意识逐渐远去。
此处乃是一个桶状山谷,最低处落差也在八十丈上下。深潭边坡形堤岸只有五丈空间可以立足,紧贴山壁一条尺宽小路螺旋形绕山而上,通向周蛮坠下的那侧悬崖半腰的一眼山洞。
小路的另一端连接着砖石堆砌的台阶,九级台阶之上是个直径五尺的祭坛。祭坛两旁沿山势雕刻两条飞龙,每条长三丈三尺,张牙舞爪,腾云跃空。正中为一座巨大神像,高六丈六尺,双手执宝,面目狰狞。在神像胯下是一扇石门,石门左右各有三名土人把守。
他们只见一人从天而降,惊叹下好奇观望。见那人拖着长长的叫声落入深潭,等了良久不见浮起,不由得伸长脖子,靠近水边。
周蛮入水后向下沉了足有二十尺,水底忽地升起数个气泡。气泡很大,竟将他一点点顶回水面。
土人们惊叹的看着河面,在巨大的气泡托浮下,周蛮的身体逐渐浮起。气泡从水中扩散,形成圆形的浪花推向四周。周蛮如同一块浮木,被青黑色的潭水推向岸边。
土人们提起长矛,警惕的盯着周蛮。他已经靠近河岸,身体随着波浪一下下撞击河边的岩石。两个土人互使眼色,小心翼翼行至岸边,用长矛在周蛮身上轻点,试探虚实。点了几下,见周蛮不动,两人皱起眉头,心下发狠,抬起长矛奋力向周蛮刺去。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河水忽地上扬,一道五尺高的巨浪无风而起,一条巨大的水怪从水底跃出,张开血盆大口欲将周蛮吞入。
周蛮毫无知觉,便如一片残叶在水波中荡漾。当波浪涌起时,他随之上升,刚巧闪过那两个土人的长矛。长矛去势不减,从周蛮身下的水波刺入,正中那水怪下唇。水怪哀鸣一声,身体翻腾,顾不得到口的美食,掉头钻回水中。周蛮则借着浪头之力被抛到岸上,翻滚几圈,撞在那两个土人脚边。
那两个土人岂料到水下有如此怪物,惊骇下弃了长矛,仓惶后退。便是有心欲给擅闯禁地的周蛮致命一击,却因水怪可怖而不敢再度涉足水边。
周蛮死里逃生却不自知,落水时的撞击令他头部受疮,不知何时才会醒来。
土人的长矛涂抹剧毒,莫说人类,便是那水怪也忍受不住。它才潜入水中未久便返回水面。四丈开外的庞大身躯跃出水面,黝黑的鳞色在阳光下闪烁慑人的光泽。它痛苦的咆哮,不住以头击石。背后气孔喷射水柱,在山谷中下起小雨。
所有人只能静静的看着,看着这人力无法抗衡的怪兽尽情的发泄。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阳光越发明媚,潭水终归平静。水怪毕竟身大,些许毒虽令它品尝一番火烧煎熬,却未足令其丧命。它潜回水中,不知何时再度浮起,向柔弱的人们展示它恐怖的力量。
土人们退回石门两侧,一人道:“那个入侵者要如何处理?”
另一个人道:“他擅闯禁地,亵渎神明,自然是杀了。”
先一人道:“那便由你去杀掉他。”
后一人慌忙道:“为什么是我?”
又一人道:“是你提出的,自然该由你做。”
那人道:“我只是按照规矩说出事实,这事我可做不了。那水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上来,我可不想靠近水边。”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却不知村长已带人向此处赶来。
出了村子,在丛林的岔路口,村长面色阴沉,道:“你确定他向这个方向去了?”
一个汉子在前引路,自信道:“一定是这边。我看过足迹,只有这个方向有可疑。”
村长目露杀气,冷哼道:“哼,他的目的果然是神物。”
村长离开村子未久,便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急奔到村长家。孟娇此时正在房中哭泣。她伏倒在床上,抱着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被子嚎啕大哭。忽而抬头,看到胸前父亲送她的挂饰,气得猛扯下来,扔到墙角。还不解气,顺手将桌上的茶壶拾起,扔向那挂饰。茶壶摔破,茶水溅洒墙角。水珠顺着挂饰滴滴答答流淌,仿佛也在哭泣。
少年奔至门口,啪啪的拍着门板。两扇木门被拍得咯吱摇曳,门闩震颤,好似要折断一般。
孟娇本就气恼,听到如此撞门,更觉心烦。她提起椅子向门丢去,嗔叫道:“招鬼呢,拍什么拍?滚,给我滚得远远的。本姑娘今天谁也不见。”
椅子轰的一声撞上门板,惊得那少年向后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他知孟娇脾性,不敢再靠近门边,躲在稍远处大声道:“大小姐,不好了,村长方才带人去了祭坛方向,好像说昨晚被你放走那人逃向了那边。”
孟娇哪有心情理会那些,嚷道:“呸,他死不死与我何干,用你跑来告诉我?”
少年只觉被骂得冤枉,却又无奈,淡淡道:“既然大小姐这么说,那我就先走了。”
少年刚转身,却听房中传出声音,道:“等等,你说昨晚被我放走那人怎么了?”
少年道:“他好像去了祭坛。”
就听房间中又是几声巨响,一把椅子顺着窗子横飞出来,掠过那少年头顶,吓得他仰躺在地,良久未敢起身。
门闩拉动,孟娇迈步而出,面上尽是怒容,狠声道:“难道被爹说中,他的目的果然是神物?姓周的混蛋,我好心放你走,你竟然敢骗我。”看到躺在地上发抖的少年,呵斥道:“还躺着干嘛?给我起来,带上我的弓箭,我们也去祭坛。臭小子,我要你知道欺骗本姑娘的后果有多严重。”
大小姐怒气冲冲而去,那少年哪敢怠慢。进入房中,找出她惯用的弓箭,追在其身后也向祭坛赶去。
王贲小心翼翼的躲藏着。他已等了半个时辰,本欲随着村长而去,又恐其身边好手众多,察觉他跟踪,未敢涉险。正犹豫该如何寻找那神物,却巧遇到孟娇二人。他心中暗呼侥幸,从后尾随。孟娇已气昏了头,哪还顾虑是否有人跟踪。
且说村长带着一行人向祭坛而去,行过一整时辰,前面出现一道墙壁般的悬崖。周蛮便是由此翻越,在坡顶逆风而行,最后落入深潭。
村长带人而来,未曾攀山,而是从旁边进入,顺着侧道绕向西北隅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狭窄却茂密,站在林口无法想象林有多深,单从方向上看,会转过西方,与他路相接。
村长带人而去,每行进十丈便有两人留下,如此约四十丈后,村长等人来到一处崖底。从此向上怕有两百丈才能攀到顶峰,艰难之极。
一人上前,拨开枝叶横生的灌木,小心翼翼挪开岩壁上一块巨石,从巨石后面露出一眼一人大小的洞口。村长吩咐四人守卫,率先进入,另有六名大汉跟随。
这通道约五十丈深,出口在弊端悬崖下的山路尽头。当村长带人出现与山谷侧的山路上时,那几名守卫祭坛的土人仍旧关于谁去给周蛮补上一矛的事情争论不休。
村长远远便看到躺在岸边的周蛮,眉头紧皱,心下怒火中烧,暗讨:“若不是你,我也不会与娇儿大吵,更加不会动手打她。”他双目喷火,紧盯着周蛮,已将所有罪责归咎于他一身。
他们绕过山路来到祭坛旁,身后自有一名汉子迈步向前,在那六名守卫每人脸上扇了个嘴巴,怒斥道:“你们在做什么?让你们看守祭坛,这是何等神圣的使命。你们非但不尽心竭力,还在此争吵。如果惊扰了神明,惹怒了先祖,你们可担当得起?”
那六人跪倒在地,为首一人指着周蛮,小心翼翼将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
村长皱眉道:“潭中有水怪?我族在此已守护了两百余年,怎么从未听闻?何况还是从绝风壁上摔下。那里神风终年不息,莫说是人,便是山妖鬼怪也别想通过。”
那汉子再度怒视那六人,喝道:“难道是你们六个为免罪责,编造出来的故事?”
那六人慌忙跪倒,异口同声道:“不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绝不是我们编造的。”
那汉子还欲发作,却被村长拦住。村长摆手道:“是也好,不是也罢,现在暂且不提。你们去把那小子提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他。”
虽有村长命令,可那六人仍旧战战兢兢,不敢靠近水边。那汉子急了,在最近一人身上狠踢一脚,将那人踢倒在地,骂了一声:“没用的东西。”径自来到水边,抓起周蛮的头发,粗暴的拖将过来。他在土人中身材也算高大,可与周蛮比较仍显矮小许多。
从旁上前两人,分左右将周蛮架住。那汉子复到水边,捧了水来泼在周蛮脸上。周蛮只觉头脑一阵清凉,双目张开,幽幽转醒。
村长身体颤抖,看表情恨不得立即便将周蛮杀死。他强忍怒气,沉声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周蛮怔了片刻,他刚从昏迷中苏醒,后脑还在嗡嗡轰鸣。他尚且搞不清此刻状况,但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危险。他可以从面前这中年男子眼中清楚的看到那**裸的杀意,那种恼怒的恨意是如此深刻,令他有些莫名。
村长不耐的一拳打在他脸上,咆哮道:“我在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周蛮扭动脖子,这一拳虽然挨得结实,但以他异于常人的强健体魄却也算不得什么。他道:“小子姓周,全名周蛮。”
村长点头道:“原来你会说话,我还道是个哑巴。”徘徊几圈,再度怒视周蛮。“你来此目的是什么?不,不,不用问这个,你的目的已再明显不过。你是受谁的命令?看你年纪不大,一定还有其他同党在附近。有多少人,他们现在躲藏在哪里?”
周蛮莫明其妙的看着村长,他几乎怀疑双方时候语言不通,自己竟完全无法理解对方所说的意思。
村长不由分说,又是几拳打在他身上,狠声道:“我问你什么你最好老老实实回答,这样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周蛮奋力甩了下头,强忍着使他眩晕的痛楚,道:“我按十年之约正要去寻家父,路经此地。此行仅我一人,并无同伴相随。”
村长不待他说完,又是一拳打去,怒道:“你想扯谎骗我?你认为你这些话我会相信么?你虽然有办法骗得娇儿,却无论如何也瞒不过我的双眼。你一定是为了我族两百多年来供奉在此的神物。说,是不是?”接着又是几拳。
拳头落在周蛮身上,一阵阵疼痛反令他清醒许多。虽仍旧全身酸痛,但体力已逐渐回复。他虽不懂为何村长如此雷霆大怒,却也知此地不宜久留,野兽般悠长的深呼吸,蓄积能量,观察四周情况,准备伺机脱逃。
想起女儿,村长更是恼火,不由分说,一阵乱打。周蛮紧皱眉头,身上的肌肉紧绷,好似钢铁一般坚硬。村长打得数十下,直震得手腕酸麻,揉着关节狠声道:“混小子,皮骨倒结实。来人,给我打,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孟娇带着那少年来到树林口,守卫自然识得她,见她满面怒容,也不知又是为何生气,未免惹祸上身,左右回避。这回避的举动倒是给了后面尾随的王贲方便,悄悄跟随其后,直至山洞口。四名守卫将洞口附近封锁,想要不被发现的潜入决不可能。
孟娇上前,那四人恭敬施礼,不敢阻拦。孟娇带着那跟班少年进入洞中,急匆匆向前行走。
王贲在外稍停片刻,心道:“此洞如此隐秘,想必定是藏匿神物之处。但不知其中情况,若是迷宫,凭我一人之力怕很难走出。若是死路,只要土人们守在洞口,便是我拿到神物也难以全身而退。”旋又心头冷笑。“看来只有靠那小丫头了。”
他抛出一块石子打中不远处一棵小树。那小树沙沙摇动,顿时吸引那四人注意。其中两人抽出短刀,和另外两人使个眼色,向摇动的小树方向走去。另外两人仍旧守在洞口,弯弓搭箭,以做掩护。
王贲心中暗笑,土人毕竟是土人,好对付得很。他又扔出一块石子打向相反方向。那执弓的二人听到声音,回身向另一侧瞄准。就在这一瞬间,王贲猛然从草丛穿出,扑向其中一人,一手按住其口鼻,另一只手抽出匕首刺入那人心窝。与此同时,抽出匕首,借回转之力顺势一抹,将另一人的脖子割断。
两个土人顷刻间送命,叫也未得叫上一声。另外两人察觉不妥,回身时,王贲已然钻入洞口。
孟娇大踏步向前,刚出山洞,隔着深潭便见到祭台上,周蛮被两人夹着拷打。她突然回身,抓住身后少年的衣领,粗暴的从他手中夺过弓箭,对准周蛮就是一箭。
她并未想过要周蛮性命,只是发泄怒气而已。这一箭带着风声从周蛮身前一寸处划过,射入地面石缝。这一箭突如其来,那几个拷打周蛮的人俱是一惊,急步后撤,骇然道:“什么人?”
村长最先看到孟娇,不禁皱起眉头。他不知女儿所来为何,还道是想搭救周蛮,怒道:“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这是祭坛,是圣地,可容得你这小丫头撒野?”
孟娇全然不理,弯弓又是一箭。这一箭檫过周蛮大腿,将裤子划破一条口子。
周蛮惊道:“且,且慢,你,你难道要射我不成?”
孟娇愤然道:“废话,本姑娘不射你还能射谁?你这个骗子,竟敢欺骗本姑娘,我要你好看。”言罢又是一箭。
这一箭瞄准周蛮肩头,他心下大骇,所幸旁人唯恐波及,散得老远,便是架他那两人也松了力道。他见机而动,猛的俯身向后,好似跌倒一般将那两人同时向后一扯,接着向前翻滚,争夺束缚。箭擦着他后颈而过,击中墙壁,弹了一下掉落地面。
孟娇没想到他竟能闪开,心下更怒,再度拉弓,叫道:“本姑娘就不信射不中你。”
就在此刻,另一侧山洞传来警戒的哨音,所有土人顿时大惊。孟娇正要回身看个究竟,却忽地迎上一个人影。那跟班少年被一拳打倒,头撞在洞壁上昏迷不醒。那条人影一转便贴近孟娇身边。孟娇倒也手脚敏捷,丢了弓箭挥拳便打。怎奈双方实力相差甚远,孟娇一拳被对方轻松闪过,顺势绕到背后,提住手腕,制住她后颈。
土人万没料到如此,一时都慌了手脚。毕竟村长不同凡人,迅猛转身,来到周蛮身后,抽出腰刀抵在周蛮背上。周蛮正吃惊孟娇因何突然受制,却没想到自己竟再度被俘。
王贲擒着孟娇顺洞口向外望去,点头笑道:“这山谷当真了得。若非我尾随你们,怕是万人搜山,搜上数月也莫想找到。”
村长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快放了那姑娘。”
王贲笑道:“村长大人,令媛娇美可爱,我这一抓可就舍不得松手了。”
村长眉头紧皱,哼道:“你怎知她是我女儿?看来你对我们相当了解。”
王贲道:“了解谈不上,事先调查一下敌军情况,此乃行军打仗的基础。昨晚多蒙各位招待,我着实受了不少苦头。”言罢将绑着绷带的手臂向外伸出。
村长道:“原来昨晚逃走的就是你。行军打仗?你是军人?难道是羌族人?”
王贲从容道:“究竟如何呢?是,又或不是。”
村长眯起眼,沉吟片刻,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王贲哈哈狂笑,道:“村长,你这岂非明知故问。我费尽心思才找到此地,你说我是为何而来?”
村长道:“你们的目的果然是神物。”
王贲道:“你最好乖乖交给我,否则令千金怕会有所损伤。”
村长狠声道:“倘若娇儿有半分损伤,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王贲一笑,道:“这些我自然明白,只看你是否愿意用你宝贝女儿的命来换我这粗人一命。”
村长面色变了又变,低声道:“你可别忘了,我手中也有人质。若是你敢对我女儿如何,我便立即斩下这小子双耳。”用力将周蛮向前一推,短刀夹在他耳边。
王贲一怔,随即大笑道:“村长,我看你常年不曾出山,这心是老糊涂了。这小子我见也未曾见过,他的生死与我何干?便是他当真是我部下,老子带兵打仗,攻城取地,不知见过多少将士丧生眼前,哪里还会有那种幼稚的怜悯心?”
村长道:“哼,你骗不了我。快放了我女儿,不然休怪我无情。”
王贲轻蔑道:“不若如此,你我同时下刀,各自割下一人耳朵。我是无所谓,只要这小丫头还活着便足够做我的护身符,缺了眼耳口鼻也无伤大雅。”
村长见王贲语气坚定,不似做假,气势不由弱了几分,皱眉道:“你当真不认识这少年?”
王贲哼笑道:“从未见过。”
周蛮苦叫道:“我早有言在先,此行便只我一人,并无其他人随行。另而,我只是路经此处,不慎跌落悬崖,掉到此处,对你们说的神物云云全无兴趣。”
村长骂道:“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抬手欲打。
周蛮趁他抬手,短刀远离了稍许,猛转身,双手托住他腋下,向上一举,将村长百多斤分量颠到空中。村长怎也没料到自己竟会被抛起,一惊之下已然双脚离地。四下无处借力,眼睁睁看着周蛮从身下而过,奔向神像下那扇石门。
周蛮也是无可奈何,左右无路,仅此处有门,唯有从此而过。他撞开左右土人,野兽一般跃起,在旁边石柱上轻踏,跃上右侧石龙。由石龙上滑梯般而下,又遇两名土人。他向后仰身,闪过长矛,顺势用头顶地翻转过去。双脚方才落地便再度跃起,好像一头猛虎从长矛下掠过,左右各一拳,将那两人打倒。
他几个起落来到石门前,村长大叫道:“快,快,拦住他,千万不能让他进去。”
王贲一笑,暗讨:“那村长如此着紧,可见神物就在里面。未免机关,正好让那小子为我探路。”他携起孟娇,顺着山路急奔,不多时已然来到祭台附近。看到上面土人们惊慌忙碌,纵身而起,掠过一人头顶,又踢倒一人,向石门靠近。
孟娇不停尖叫,扭动厮打,毫不安分。王贲有些恼了,一掌打在其后颈。她眼一翻,昏厥过去。
村长大惊,提刀挡在王贲面前,叫道:“你对她做了什么?”
王贲笑道:“只是让她老实些而已。你快让开。”
村长哼道:“不行,神物是两百多年前祖宗传下的东西,我们有义务拼尽性命来保护。”
那两扇石门上各有一只猛虎,周蛮双手各按住一颗虎头,努力推去,就听哗啷啷锁链响动,两扇巨大石门就这样左右分开。
村长大惊,喃喃道:“这不可能。这石门乃万古不开,便是我族也只能走侧面暗门。我曾找二十人企图推开这石门,结果纹丝未动。他只区区一人,怎么可能推开!”
他发呆之际周蛮已逃入石洞。王贲趁机而走,追着周蛮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