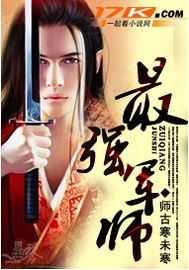詹小月跳起道:“好啊,我还从没见过人成亲呢。成亲喽,黑炭头和莺莺姐要成亲喽。”
胡熊笑道:“是了,我怎么没想到。娘也在此,不如今晚就把他们的婚事办了。”
詹子道:“虽然简陋些,但情势所逼,也不可多求。”
见事态越发不可收拾,胡莺莺无奈道:“我,我答应与他睡在一间便是,这亲事先别忙办了。”
詹子见她改口,也不好逼得太急,道:“也是,如此仓促,准备不足,要操办亲事确实不妥。既然莺莺姑娘也同意与胡山同住,婚礼之时就延后再说吧。”
詹小月才提起的兴奋一口气泄光,不免扫兴。詹子伏在她耳边道:“娃儿莫急,他二人成婚只在迟早而已,到时定让你玩个高兴。”
詹小月喜道:“当真?”
詹子笑道:“自然。你不觉得他们两人很般配么?”
詹小月看看黑如山猪的胡山,又瞧瞧花容月貌的胡莺莺,皱眉道:“如此也能称之为般配?”
詹子含笑点头道:“嗯,嗯,称得,称得。”
吃过饭后,胡熊令众人去各自房间。胡小花许久未见母亲,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整夜便是拉着母亲的手,说她嫁入这里之后的点点滴滴。老太太虽然劳累,可看到女儿那副兴奋模样,脸上只剩微笑。她听着女儿的声音,听着她娇哼,听着她欢笑,满口满心全都是一个男人。她知道她有多幸福,她为此而感到欣慰,为此而感到幸福。
詹子哄着詹小月睡去,小姑娘这一路着实劳累,躺下未久便睡熟了。周蛮待詹小月睡着后将詹子拉到一侧,轻道:“詹老爹,之后你有何打算?”
詹子奇道:“打算?什么打算?”
周蛮道:“既已将他们母子送到此地,那胡熊看来亦不似歹人。我们是否也该启程?”
詹子沉吟道:“的确,照如今看来,胡老夫人一家人也可在此安居乐业。凭那胡山,胡川两兄弟,虽说别的本事没有,但力气还是有的。只要跟胡熊学上几月,上山打猎,必可在此生根。此地距他们村子不远,老夫人不用长途跋涉,又免离乡之苦。此地民风剽悍,上下一心,亭长耳目少有触及,亦可放心生活。确是没有比此地更好的去处了。”
周蛮道:“既然如此,我们也可安心,不如明日便走?”
詹子点头道:“走是可以,只怕娃儿她舍不得哩。”
周蛮道:“可我们还有事,不能一直留在此地。”
詹子道:“好吧,明早你来与娃儿讲。”
詹小月忽地大叫:“一拜天地。”扭个身,依旧酣甜睡着。嘴角挂着微笑,不知做得什么好梦。
胡山与胡莺莺进入房中,这间房不大,一张平板木床,墙角一面磨盘大四方小桌,再无其他。胡莺莺立在门口,千般不愿,万般不肯,却又无可奈何。看着胡山粗野的模样,不免一阵心酸,眼眶湿润起来。
胡山走在前面,一屁股坐在床上,与胡莺莺同房而居令他不知所措,甚至连瞧她一眼也是不敢。于是他二人一个垂泪立在门口,一个垂首坐于床头,均不言语,空气一片死寂。
良久,胡莺莺忍不住抽泣起来,胡山闻声望来,竟见胡莺莺好一张俏脸哭得眼红鼻粉,楚楚惹人怜爱,不仅一阵心疼。他慌忙站起,担心的向胡莺莺走来。却是后者尖叫一声跳开,道:“你,你要做什么?别靠近我。”
胡山被胡莺莺的叫声所惊,整个人僵住,一只脚举在空中,怎也不敢落下。就这样单足立着,时辰久了脚酸腿抖,摇摇晃晃了几下跌在地上。
胡莺莺见他憨态模样,忍不住噗哧一笑,笑过后却又冷起脸色,道:“你是傻的,我叫你不要过来,又没说你不可动弹。”
胡山挠头傻笑,从地上站起,缓缓退到床边。胡莺莺叹了一声,擦着泪痕进入房中,依在墙角的小桌旁,看着地面发呆。
胡山气也不敢大声喘,两人便如此僵持,久了,胡山倦意上涌,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他鼾声如雷,惹得胡莺莺频频皱眉。她推开窗子,望着天空,心道:“为何我如此命苦?娘,娘,您可看到您当初为女儿选了个怎样的丈夫?”
哭了一阵,她也累了,趴在小桌上,思忆着儿时的梦想。当时的她相信自己未来的夫君若非是个顶天立地的大将军,便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学士。可梦想毕竟只是梦想,这震耳欲聋的鼾声将一切破灭。
她累了,阖上眼,时而睡,时而醒,也不知交替了几遍,清晨的阳光带着一日中最初的温暖照射到她脸上。她微微仰头,可尚未及瞧上那太阳一眼,展露出一个微笑,新的事端便发生了。
一个汉子急匆匆奔进院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他叫道:“熊哥,熊哥,不好了,亭长带了不少人来,已将村口堵了。”
胡熊披着衣服出来,身后跟着胡川。后者道:“他们鼻子够灵的,竟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胡熊道:“你不用担心,我量他也不敢进村。”转身对报讯人道:“他们在哪,你带我去看看。”
院子里一闹,其他人也从房中出来。胡小花搀扶着母亲,胡山与胡川来到母亲身边。
老太太道:“唉,果然还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胡小花道:“娘,别这么说。”
詹子与周蛮均是一皱眉,情况紧急,无法撇下他们不管,启程之事只好暂缓。
詹小月打着哈欠走来,懒洋洋道:“那亭长当真不知死心,屁大点一个乡官,闹出这么大事情,就不怕县里来人办他?”
詹子叹道:“他毕竟死了儿子,以捉拿凶手为借口,便是谁来他也不怕。”
胡莺莺立在墙角,心中矛盾,垂首不语。她自然不喜亭长,若被他擒回,势必被其威逼就范,日后不知该如何做人。即便逃出亭长魔掌,下半生却又要陪伴一身憨气的胡山,只怕日子也好不了多少。
老太太道:“我们也去看看吧,倘若当真有事,我们出去便是,总不好给他们村也惹来麻烦。”
胡小花忙道:“娘,您这说得哪里话?这里是我家,便也是您家。您只管在这里安稳住着,外面有熊哥撑着,不会有事。”
老太太坚持道:“不妥,不妥。我们还是一起出去看看。”
见老太太坚持,其他人也无奈。众人绕出院子,在一面残破的小土墙后躲避,远远望着村口情况。
村外聚集一众怕有百来人,为首之人正是那亭长。他包着手臂,指手画脚,声音虽大,却含糊不清,因而很难明辨其言。但见他神情激动,想来是在骂人。
在他身后立着一名女子,看年纪方过桃李之年,样貌俊俏,举止大大咧咧,有股男子气魄。
周蛮未曾见过,不免问道:“那女子是何人?”
其他人尽皆摇头,亦未曾见过此女。还是胡莺莺,思索片刻,道:“亭长家似乎有个女儿,比那死去的胡二年长一岁,但常年不在家中,听说是被送去学些什么。我被他们抢去与那死掉的胡二成亲时,听人讲起,详情我便不知了。”
周蛮喃喃道:“有个女儿?”
詹小月侧目道:“怎么,蛮,看上她了?我觉得她没什么好。”
周蛮摇头道:“我只觉得她有些危险。”
詹子道:“何出此言?”
詹小月却笑道:“蛮,你何时变得如此胆小,竟然怕起一个女人来了。”
周蛮只是不语。他觉得那女子危险,全凭一种感觉,若问缘由却是答不出来。
亭长又与胡熊说了一阵,胡熊转身回来。见亭长那暴跳如雷的模样,显然谈判不成。村中老少尽皆守在村口两面石墙之后,手持强弓短刀,便是亭长有三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轻举妄动。
周蛮道:“亭长来势汹汹,势必不会轻言撤退。倘若有何闪失,我便带你们突围出去。”
詹子皱眉道:“不妥。此时不比当日在小城。当时你只需护住我与娃儿,可如今人数众多,你一人只怕照顾不周全。便是侥幸突围出去,也难保我们没有伤亡。何况若是我们强行突围,岂非连累了靠山村的村民背上一条窝藏犯人的罪责。”
周蛮点头,口中喃喃道:“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顿了顿,又道:“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詹子略显惊愕的望向周蛮,詹小月却嗤笑道:“蛮,你在嘀咕些什么啊,乱七八糟。难道是飞天遁地的咒语不成?”
周蛮脸红一笑,道:“此乃一本书中的一段,幼时爹常念给我听,时日久了便暗记下来。方才不知怎地,突然便在脑中出现。”
詹小月低声道:“蛮,你又想你爹了?”
周蛮长叹一声,摇头不语。
詹子默然片刻,道:“蛮,依你之见,如今我们该当如何?”
周蛮忙道:“如此大事还得由詹老爹作主才是。”
詹子道:“我既问你,你便回答,无需推三阻四。”
周蛮沉吟片刻,道出四字:“金蝉脱壳。”
詹子微微点头,却并不答话,似在等周蛮解释。
周蛮道:“且不提双方战力,如此僵持下去势必给靠山村村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只要我们不在,那亭长自然无理由继续纠缠,亦无法怪罪靠山村。”
詹子点头道:“且那亭长如今将全部视线集中在靠山村上,倘若我们能避过他们耳目出村,必可赢得时间远遁。”
胡莺莺低声道:“又要逃?”
老太太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拉着两个儿子的手。“你们便随恩公们走吧,我老婆子和你们一起,必然会拖累你们。”
两兄弟同时跪倒,道:“娘,你若不走,俺们兄弟也不走。”
詹子道:“老夫人,您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顾虑这些。眼下不能再拖,您就别固执,与我们一起走吧。”
老太太犹豫再三,拗不过众人劝说,只得答应。
胡小花道:“娘,您,您真的要走?这,这,日后女儿要如何见您啊?”
老太太慈祥一笑,道:“娘知道你生活幸福,夫君疼你,爱你便足够了。日后等风声过了,我和你哥又能安定下来便托人通知你。”
胡小花道:“娘,到时一定通知女儿,女儿好去探望你老人家。”
胡莺莺面色为难。她自也知道此刻非逃不可,可她一双莲足已磨出好几个水泡,虽然仗着性子强忍着,但长途跋涉实难承受。
老太太见胡莺莺面露难色,只道她嫌弃自己儿子,不愿与之一起,轻叹,道:“莺莺姑娘,若是你不愿走,留下也可。”
胡莺莺一听便慌了,若是留下定然被亭长捉回去,忙道:“不,不,我与你们一起走。”
胡熊从外回来,正欲回家,却见他们躲在这里,走上前来,道:“几位不在家中休息,怎么都出来了?”看到众人面色,笑道:“你们可是担心?尽管放心,只要有我胡熊在此,量他们也不敢入村。”
詹子道:“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便将方才的打算讲述一遍。
不待听完,胡熊便摆手打断。“老先生是否多虑了?你们只管放心住在我家,我保你们无事。别看现在亭长带人气势汹汹守在外面,可他们毕竟无法持久。我看用不上三天便会离开。只是这几天要委屈各位,不要四处走动。等他们去了,我们照样自由生活。”
众人见胡熊如此说,也不好再坚持,可心中却均以决定离开。
亭长在外直守一日,时近傍晚,村中升起炊烟,香气飘逸而出。他带人从昨夜至今便未曾吃饭,此时闻到这股香气,莫说那些手下民兵,便是他自己亦是口水直流。
前者周蛮所见那女子确是亭长之女,名唤英。胡英来到父亲身边,轻道:“爹,长老来了。”
亭长一怔,惊道:“长老?来了几个?”
胡英道:“一个,带着啬夫及游徼。”
秦朝规划疆土,延袭周制,以郡分,每郡分置守尉,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朝廷设御史监郡,称为监。每县设令,与郡守尉同归朝廷简放。守令下有郡佐县佐,各有守令任用。以下便是乡官,选自民间,大约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及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判诉讼,游徼治盗贼。这长老乃是乡长,正司亭长上职。那亭长不敢怠慢,急忙提袍相迎。
长老年过花甲,一副弱不禁风,随风可倒的模样,似是就此闭眼蹬腿也不稀奇。在他身后跟着两个魁梧汉子,左侧一个颇为高大,直比那胡熊还要猛上少许。连鬓络腮的胡子,扎扎微微,手臂胸口尽是卷曲的毛发,颇为剽悍。另一个身材稍矮,肌肤黝黑,两道眉又密又粗,好似将眼也给挡住了。
那高个汉子便是本乡游徼,在周边地区颇有些威望。那黑汉乃是啬夫。
亭长见三人,忙躬身施礼,道:“不知三位大人到访,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长老张眼看了看亭长,淡淡道:“老朽等人又非登门府上,何来到访之说?既非到访,又何许远迎啊?”
亭长只能道:“是,是。”
啬夫道:“胡金,你这亭长当得好大威风啊。”
亭长一惊,忙道:“小人一向本分,何来威风可言。”
啬夫道:“本分?看看你这架势。带了这么多人来,怕是有一百人吧。有这么多人给你撑腰,你还不够威风?便是长老出门也只带我二人而已。”
亭长只觉双腿发软,不敢看啬夫,望向长老,道:“长老明鉴,小人如此也是逼不得已啊。”
长老道:“哦?如何逼不得已,说来我听。”
亭长道:“想我那儿子,乃是我家一脉单传,看上了一家姑娘,想娶之为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谁知七里胡家村一户兄弟也看上那家姑娘。长老也知,一家姑娘如何能配两家汉?我儿去与那兄弟商量,好言相劝,谁知他们蛮不讲理,不允也便算了,竟还出手大人,将我那儿子活活打死。”说着泪流满面。“长老,您说说,我仅有的儿子被他们打死,这个仇我如何能不报?我带人去,可那兄弟却逃了。他们在山上避了一月,前夜又潜入我家,将我儿媳捋走,又欲杀我。”将左臂刀伤示给那三人看。“若非我命大,此刻只怕已见不到三位大人了。我连夜带人去抓,可他们举家逃窜,如今就藏在这靠山村中。”
啬夫道:“你这伤当真是那对兄弟所为?”亭长一怔,啬夫即怒叱道:“难道你敢做假欺骗我们?”
亭长忙道:“不,不是的。那对兄弟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在外请来几位高手,其中一人身高过马,威武超群。前夜便是他带人潜入我家,将人抢走,又将我扎伤。”
游徼道:“果有此事?”
亭长道:“小的不敢说谎。”
游徼道:“哪里来的泼皮,竟敢跑到我们乡来惹事。让我看看,他究竟如何高大威猛。”
亭长道:“此人便在靠山村中,可那胡熊强硬得很,我又不好带人硬闯。”
游徼冷哼一声,道:“那胡熊本也算是条汉子,但在我面前却也不过寻常猎户尔。”
亭长忙道:“是,是,他哪能与大人您相提并论。”
长老长叹一声,道:“胡金,你当我今日什么也不知便带着啬夫、游徼跑来这里?”
亭长一惊,道:“长老此言何意?”
长老道:“听说你在你儿死后,又去抢人姑娘来与你儿成婚,可有此事?”
啬夫在旁看着,目透冷笑。
亭长硬着头皮立在哪里,却是一句话也答不上。
时间耽搁久了,胡英颇感不耐,见父亲只是低头被人训斥,不免上前道:“三位大人,小女子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长老轻道:“讲。”声音悠长。
胡英道:“你们既然来此,该当对事情有所了解。我弟胡二已死,是也不是?”语气颇为强硬。
全乡上下只怕也找不出第二人敢与长老如此说话,亭长听得一惊,想要喝止女儿。可女儿自幼在外习武,对父亲之言向来不放心上,便是呵斥也是无用。
啬夫与游徼均是眉头一皱。那长老却面色平淡,点头道:“确是如此。”
胡英又道:“我二弟是否被那胡山、胡川两兄弟活活打死?”
长老道:“听闻,也的确是被他们所伤。”
胡英道:“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该当先抓胡山、胡川,再谈其他?”
长老淡淡道:“一笔归一笔,谁也逃不了,谁也跑不掉。”
胡英见长老故弄玄虚,心中怒起,冷哼道:“既然如此,我与我爹亦不会逃,不会跑。等抓到胡山、胡川,再来受教。”言罢转身便走。惊得亭长连连道歉,走也不是,留亦不是,踌躇半晌,最终向三位告退,追着女儿去了。
游徼呵呵笑道:“好有活力的小姑娘。”
长老道:“我们也去吧。那胡熊可绝非好说话之人,若是双方当真动起手来,事情闹大,传到县令耳中,便是我也压不住了。”
啬夫、游徼应诺,三人向靠山村而去。
长老到来令胡熊颇感意外,他急忙整理衣装,出村迎接。
长老见他至,笑道:“胡熊,最近村里情况如何?”
胡熊道:“天气尚暖,猎物充足,村子里的生活一起安好,多谢长老挂念。”
长老点头道:“如此甚好。”望着潜在石墙后的弓箭。“这是何意啊?”
胡熊朗声道:“亭长欺人太甚,竟带人要搜我村。我村一向本分,岂能由他说搜便搜?”向亭长狠瞪一眼。“谁若想平白乱闯我村,就让他瞧瞧靠山男儿的血性。”
游徼怒道:“胡熊,注意你的态度。你当是在谁面前说话?”
胡熊连忙躬身,向长老道:“胡熊乃是一粗人,还请长老勿要见怪。”
长老笑道:“若是我要见怪,早在数年前已经怪了。”
胡熊呵呵一笑,道:“多谢长老。”
长老沉吟片刻,道:“胡熊,亭长来是为找人?”
胡熊道:“是。可我村上并无任何罪人。”
亭长叫道:“明明就在你村。”
胡熊瞪眼道:“在我村中均是安善良民。”
亭长气得直叫:“你,你,你……”却也你不出个所以然来。
长老摆手道:“胡熊,老朽的话你可愿听?”
胡熊暗自一惊,口中只能道:“请长老吩咐。”
长老道:“既然亭长不辞劳苦,带人远道而来,你便买老朽一个薄面,让他进去搜搜。若是搜到了人,让他带走便是。”
胡熊道:“若是搜不到呢?”
长老道:“若是搜不到,便是他无理取闹,叫他给你们赔礼便了。”
胡熊道:“这赔礼可要怎么个赔法?”
亭长叫道:“胡熊,你别欺人太甚。若是搜到,便是你们全村上下窝藏罪犯,到时有你们好受。”
长老摆手示意他休言,道:“有老朽作主,自当要你等满意便是。”
胡熊见长老如此说,不好再拖,只得道:“既然如此,我让他进去便是。我这便去吩咐人撤下。”当即转身来到石墙边,故意提高嗓音道:“大家听着,我们立即放亭长的手下进村。若是搜到罪人便由他带走,若是搜不到,自有长老为我们作主。”
村民们交头接耳,三三两两扔下武器从墙后出来。墙角下一十六七岁的少年听到胡熊声音,并不如其他人般起身而出,反而避开人们耳目,绕过后墙来到胡熊家后窗,见左右无人,轻扣窗架。窗子从里打开,胡小花露出头来。
那少年道:“嫂子,不好了,亭长找来长老出面,熊哥也不好阻拦。他们马上就要进村了,快让那些人躲一躲吧。”
胡小花面带哀伤,淡淡道:“他们已经走了。”
少年愕然道:“走了?何时走的,去了哪里?”
胡小花道:“熊哥方才出门他们便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
少年点头道:“走了便好。嫂子,你在家等着,我先走了。”言罢头一缩,猫儿一样去了。
亭长带人入村,乡长命啬夫、游徼在旁监督,自有胡熊相陪。他们在村中搜了两遍,却连一丝胡山、胡川的人影也不见,更别说那身高过马的大汉。
亭长面色惨白,不知所措,搜过两遍却还要搜。胡熊将眼一瞪,怒道:“村子只有这么大,能藏人的地方均已找过,你还要搜到何时?”
此时天已黑了,四周燃起火把,火光在半空跳耀,映得亭长面容焦暗,更显慌张。
他望向乡长,却见其面沉似水,一副兴师问罪模样,慌乱下想寻求女儿帮忙。她毕竟常年在外,见多识广,或有脱此困境之法。可他转头回去,却不见女儿踪影。他明明记得搜索开始时女儿与他一同入村,却不知何时竟然不见了人。他被胡熊,啬夫,游徼,长老四人围在当中,除了陪笑脸,什么也说不出。今夜,怕是他一生中最长之夜。
却说周蛮等人,早已看出僵持下去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双方开战,互有伤亡。二是亭长入村,将他们搜出,将胡熊问罪。为免这两种情况发生,他们唯有一走了之。
他们继续向东而行,打算逃去巴郡。只要出了蜀郡,他们便可安心。便是那亭长如何抓狂,凭他小小乡官,也无权越郡抓人。
几人离开村子一路沿山而行,毕竟有老人妇女,加之夜晚山路难行,行程缓慢,直至三更,方寻到一处水源。众人不敢生火,唯恐被追兵发觉,围拢而坐。时已入秋,夜里转寒。胡莺莺身子柔弱,受不住冷,蜷缩成团。胡山虽担心,却也知对方心中厌恶自己,不管过问。人们沉默不语,一时间气氛消沉以极。
詹小月依靠在詹子身上,不多时便睡熟了。詹子轻轻拍着孙女的背,不知不觉也睡了。周蛮缓缓起身,在河边撩起水花,看着晶莹的水滴顺着指缝滑下,在月光中落入河面。月儿弯弯,倒映水中,宛如飘在碧波上的船。
远处传来狼嗥之声,一声之后便有一群回应。声音悠长好似哀鸣,凄美又令人胆寒。在狼嗥声中,周蛮仿佛见到一个夜晚,一个闪电交加却又不见一滴雨水的夜晚。在那个夜晚中,留存着他心中最美好的梦。
他正自出神,忽闻风中异响,精神一震,急忙来到詹子身旁,将其唤醒,道:“詹老爹,似已至矣。”
詹子皱眉道:“怎如此快?难道胡熊没能将其阻在靠山村?”
周蛮道:“时间紧迫,我们得立即上路。”
胡莺莺不习外宿,天气又冷,又担惊受怕,哪里睡得着。她见周蛮起身,立即问道:“可是有人追来了?”
周蛮点头道:“十之**。”
詹子将其他人逐一唤醒,带众人藏入附近树丛中。
老太太担忧道:“这荒山野岭,若是被人围上可如何逃脱?”
胡山道:“詹老爹,您看俺们如今该怎办才好?”
詹小月道:“爷爷,我们快些逃吧。要是被追上可不好玩哩。”
詹子观望天色,叹道:“只怕逃也不易。再过一个时辰便将天明,到时我们失去夜幕保护,行进速度又缓,很难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