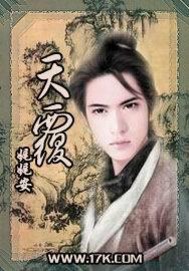詹小月猛噎口菜,喘息良久,方道:“那要我们如何是好?菜已吃过大半,若是现在告知他们我们没钱,只怕他们不会笑着送我们出去。”
詹子肃然道:“我便是考虑到事情严重才与你们商量。”
詹小月叫道:“这叫什么商量。”她愤然而起,未压低声音,饭馆中人同时向其望来。她咧嘴一笑,又缓缓坐下。
詹子道:“你叫什么,怕人不知我们没钱?”
詹小月轻道:“都怪你,吃饭前如何不提?若是你先说清楚,我们不将大饼交给胡川,自己吃了多好。”
周蛮叹道:“事已至此,再如何埋怨詹老爹也无济于事,不若考虑一下脱身之法。”
詹小月叹道:“还怎么脱身?没钱,人家老板怎会轻易放我们离开?”
詹子眯着眼,仿佛下了莫大决心,斩钉截铁道:“当前之计唯有一个字。”
周蛮与詹小月同时问道:“什么?”
詹子左右顾盼,见无人在意他们,低声道:“逃。”
詹小月胳膊从桌上滑下,险些撞了鼻子,没好气道:“装得一本正经,还道你有什么惊天妙计,原来只是如此。”
詹子道:“不然你说该当如何?难不成把我这身老骨头卖了,看是否换得一顿饭钱?”
周蛮忙道:“你们先勿吵,再仔细想想,或尚有转还。何况便是将詹老爹卖了,只怕也值不上一个馒头。”
詹子闻言愕然,凝视周蛮良久说不出话来。周蛮表情严正,全不似说笑。詹小月在旁看着,忍不住噗哧一笑。
周蛮自知失言,忙道:“詹老爹,我并无折辱你之意,只是就事论事。啊不,我之意……”
詹子摆手道:“好了,蛮,你无需多说。你说得越多,我就越气。”
周蛮长叹一声,甚为无奈。詹小月在旁咯咯娇笑,笑得颇为欢畅,引得附近人们纷纷注目。
詹子道:“别笑了,你唯恐别人不注意我们啊?”
詹小月强忍笑意,道:“这都怪蛮,平白的逗人发笑。”
周蛮委屈道:“我倒从无此意。”
詹子道:“有空胡闹,还不如想想如何脱身。”
詹小月轻挠着头,盯着桌上一盘红烧牛肉,忽道:“我想到了。”
詹子与周蛮同时道:“当真?”
詹小月点头,得意道:“要脱身还不简单,只要爷爷一句话便可。”
詹子寒着脸道:“你该不会当真要把爷爷卖掉吧?”
詹小月道:“怎么会。爷爷,你不是有个小金牛么?把那金牛给他们,何止一餐饭食,便是日后的盘缠亦无需发愁了。”
詹子双眼瞪大,骂道:“你这小混蛋,尽惦记着爷爷的金牛。与你说过多少次,那乃是祖上传下的传家之宝,便是饿死也不能卖。”
詹小月哼道:“传家之宝又如何?难道老祖宗希望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为守这身外之物而活活饿死,平白断了他们的香火?”
詹子道:“小孩子胡言乱语。总之不行便是不行。”
詹小月道:“不然你说怎办?事已至此,难道当真要逃?若是现在惹起麻烦,只怕多生枝节,夜里动手时岂非不妙。”
詹子道:“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逃。惹出事端便会惊动亭长。自然,他不会在意此等小事,但事情发生时,街上一乱,护卫民兵定有反应,我们也好趁机看清村中防备,以便留下退路。”
詹小月哼道:“大道理说得好听,其实不过是舍不得那只破金牛。”
詹子气道:“那乃是传家之宝,怎可说是破金牛?”
周蛮劝道:“区区小事,何必争吵。我们就按詹老爹的方法行事便是。”
詹子道:“什么区区小事,这可是大事。你们听我说,那可是有相当历史的。”詹子兀自说起没完,詹小月却已听不下去。她推着爷爷道:“是啊,是啊,知道啦,那不是区区小事,是区区大事。”
詹子道:“当然是大事。丫头啊,大事是不能用区区的,要知道……”
詹小月全未留意他的话,满口道:“是了,是了。”只是推着他向外走。
小二正从厨房回来,将毛巾在肩上一搭,见周蛮等欲走,叫了声:“几位爷,请留步。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詹小月道:“忘了什么?啊,难道还有菜没上?那就退掉吧,我们已吃不下了。”推着詹子已至饭馆门口。
小二笑道:“不是啊,几位爷,你们忘记给钱了。”
詹子道:“钱?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脚刚迈出门槛,突然加速,拉着詹小月便跑。周蛮一时反应不及,直看着他们跑出三丈才回过神来,追着去了。
见他们跑了,小二慌忙叫道:“站,站住,钱,还没给钱呢。掌柜,不好了,不好了,有几个人吃饭不给钱。”
村子人声鼎沸,一下便喧闹起来。三人沿进路逃出,一口气冲出村外,钻入树林。
胡川早在树林等候。他将大饼吃得干净,正心满意足的躺在树下休息,见三人出来,正欲迎上,却闻人声嘈杂,竟有一伙民兵从村中追出。他乃被通缉之人,哪敢露面?吓得缩在树后,盘算一阵,向树林深处逃了。
周蛮三人不停奔逃,足跑出一里方才止步。见无人赶上,方舒了口气。
詹小月道:“爷爷,如今我们也与那胡川一样入不得村,这救人之事可如何是好?”
詹子胸有成竹道:“不碍,不碍。救人之事只管放心。”
周蛮道:“詹老爹已有办法?”
詹子道:“方才进村时我已将地形记清,亭长家位于村子正中的红门小院,极易辨认。村中民兵共二十一人,亭长门外二人,院侧二人,后院三人,其余则分布在街上。方才追赶我们的仅有七人,其他人虽也有来看,却仍旧守在各自岗位。”
周蛮惊叹道:“不过短短时间竟然看得如此清楚。詹老爹,你是如何做到的?”
詹子沾沾自喜道:“区区小事,对老夫而言算不得什么。”
詹小月道:“先把晚上的事放一边,胡川那黑炭头跑哪去了?若是没了他,我们劫了人后要送去哪里?”
周蛮和詹子向四处寻望,却不见胡川身影。
詹子埋怨道:“嘱咐他数次,要他在林中等候,切勿走得太远。没想到结果仍是如此。那小子也不知都在想些什么,若是耽误了时辰,救不出人来,看他要如何与他兄长交代。”
周蛮忧心道:“若是没有胡川,莫说无处可送,只怕便是连人也救不出来。”
詹小月道:“是啊,人家一个姑娘家,又不识得我们,凭什么与我们走?万一我们是歹人,她跟我们走岂非害了自己?”
詹子轻咳一声,抚着胡须,装腔作势道:“老夫何处看来似个歹人了?”
詹小月哼道:“凭你那句‘老夫’便不似个正经人。又非富家老爷,或世外高人,还‘老夫’,也不怕咬了舌头。”
詹子气得半晌无言,只是一张老脸憋红,胡子吹起老高。
周蛮道:“你们别吵,当务之急还是先找胡川要紧。”
詹子瞪了调皮的孙女一眼,微微点头,和周蛮商量一下,分头去寻。詹小月看看周蛮,又瞧瞧詹子,犹豫片刻,追着詹子去了。
詹子略感意外,奇道:“你这丫头,怎不缠着那大块头,却来找我这老头子?”
詹小月嘻嘻笑道:“这山林里面荆棘重生,危机重重。我担心爷爷一个人有危险,特地跑来帮忙。”
詹子哼道:“说得好听。你当爷爷是老废物,还需要你个小娃娃保护?”
詹小月道:“当然不是,但多一人总多一份力不是?”
詹子哼了一声,脸上却堆起个美滋滋的笑容。
周蛮与詹子背向而行,未久,穿过小树林,眼前赫然出现一片田地。田中种植着小麦,时正晚夏临秋,地中麦谷半熟,青黄相间,顺山势成美丽的阶梯状,绵延而去,仿若在山脊上披挂一层青铜铠甲。时而有风经过,谷物摇曳生波,趋势而走,宛如另一条黄河,万马奔腾,浩荡远去。
周蛮初识谷物,心下好奇,顺坡而下,不多时便奔至田边。将一缕缕麦穗托在掌中,轻轻抚摸,别有一种温馨之感涌入心田。世上万物尽皆大地子孙,而此时,周蛮便仿佛感受到大地母亲的呵护一般,全身充满温情。
此刻正是午休时间,劳作的农人三三两两去阴凉处吃饭,田边无人。周蛮望着麦田出神,不自觉已过了足个时辰。农人们复又返回田间,一位老汉见到周蛮,叫道:“小兄弟,你这是在干嘛?”
周蛮向老汉问道:“老丈,这,这些可是何物?”
老汉笑道:“小兄弟,你莫非是在戏弄我老头子?”
周蛮莫名道:“老丈何处此言?”
老汉见其神态真诚,不似说谎,道:“你当真不知?这不就是寻常的麦子。平时吃的面条,馒头,都是用这东西磨碎之后做成的。”
周蛮口中道:“原来如此。”眼中放光,好似顽皮的孩子,充满难明的兴奋。
老汉不禁摇头轻叹,道:“多好一个小伙子,可惜是个傻子。”扶正草帽,扛着锄头走入田中。
周蛮正自兴奋,忽闻身后有人唤自己,那清脆的声音除詹小月以外再无他人。他回身正欲招手,却见山坡上站得不止詹小月一人,其身后另有两个粗壮男子。但见那二人身材中等,穿着粗布衣衫,头巾缠发,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颇有些乡土气息,便似方才那老汉一般。
在周蛮迟疑间,詹小月却已等不及的催促起来。“蛮,快,快过来啊。”
周蛮知道定是又遇了事情,否则怎么只见詹小月而不见詹子。他登上山坡,至三人面前。距离远时尚不明显,待至面前那二人才发觉周蛮竟是如此高大,不由得双腿打颤。
周蛮道:“唤我何事?詹老爹呢?”
詹小月见周蛮已在眼前,胆也壮了,笑道:“老样子,爷爷又被抓了。”
周蛮气节一笑。心道:“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却又怎去说别人。”口中却道:“他人在何处?”
詹小月道:“大概被其他人押着。”扭头向后张望。“应该就在附近。他们有十几人,也不知这一会藏到哪去了。”
那二人见周蛮与詹小月肆无忌惮的交谈,不由得恼怒,怒骂一声:“给我闭嘴,谁让你们胡乱讲话?”将詹小月向后一拉,扭得小姑娘手臂酸疼,禁不住轻呼出声。
周蛮眉头一紧,虎目圆睁,飞身向詹小月扑去,比饥饿的山熊还恐怖三分。詹小月将眼一闭,身后那两名男子对此突变反应不及,呆立当场。周蛮如同魔鬼般冲至二人面前,在他二人眼中仅有周蛮那对仿佛闪烁红光的双眼。
周蛮猛地俯身,展双臂仿佛一件巨大披风将詹小月抱住,同时向前撞去,双肩顶在二人腹部,将他们撞飞出去。那两人在地上翻滚几圈,起身时满目惊骇。他们头脑一片空白,记忆中仅存那双闪着红光的眸子。
周蛮简单查看詹小月身上,见并无损伤,安心道:“他们似乎并未为难你们。”
詹小月扭着肩膀道:“还好,就是被他们抓着手腕,肩膀扭得有些酸。”
周蛮道:“詹老爹呢?”
树林中传来一声叫喊,一个青年叫道:“你若想找人,还是来问我吧。”
周蛮见那人年纪轻轻,与己相仿,体格甚是结实,便道:“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那人哼道:“你不用知道我的名字,你只要知道那老头在我手中,而你则必需回答我的问题。”
周蛮道:“可否让我与詹老爹见上一面?”
那人道:“我已经说过,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周蛮叹道:“既然如此,不知兄台有何指教?”
那人道:“你们是什么人,从哪来,到哪去,为何来我们胡家村?”
周蛮随口道:“我等乃寻常路人,从西而来,向东而去,路径此地,便来讨口饭吃。”
那人面色阴沉,喝道:“满口胡说八道。”
周蛮道:“我句句属实,并无虚假。”
那人叫道:“放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来这北胡村所谓何事?若是再不老实,我马上砍了那老头的手。”
周蛮眉头紧皱,沉吟片刻,道:“我们确是路人,只是路上遇到些事情,到此北胡村来找人。”
那人冷声道:“还不说实话?”
周蛮忙道:“我句句属实,并无虚假,你千万莫伤了詹老爹。”
那人又道:“你们来找何人?”
周蛮向詹小月望去,后者东瞧西望,也不知在找寻什么。他暗叹一声:“如今詹老爹命在旦夕,怎地你还有心玩耍?”口中道:“亭长的儿媳。”
那人眼光似乎闪了一下,又问道:“你找她做什么?”顿了片刻,续道:“你最好老实交代,那老家伙已经都和我们说了。”一招手,两人携着詹子从一棵树后走出。
詹子苦着脸道:“蛮,我全都说了。”
周蛮长叹一声,道:“我便与你明说吧。我等此来便是为了潜入村子,将亭长家的儿媳救出。他倚仗亭长之势,强抢民女,如此专横之人,我们怎能坐视不理?何况那姑娘本已许配人家。”
那人沉吟半晌,道:“我如何能够相信你们?”
詹子叫道:“喂,我说了你不信,他说了你又不信。我们又未曾事先串供,如何能说得一般无二?何况这并非好事,若是被寻守的民兵抓到还不马上送去挨板子。我们为何要用这种事情来骗你?”
那人左思右想,犹豫不定。
便在此时,树林中传来一阵呼喝声,一人拖着长长的尾音从远方荡着一根树藤而来,直冲到詹子身边,本以为会撞开押他之人,却不想方位略偏,正撞在詹子身上。詹子连皮带肉不过**十斤,一撞之下包裹般飞了出去,掠过众人头顶,直砸向周蛮。
周蛮向后翻倒,顺势减低冲击,将詹子接住。接住后的詹子歪着颈子,口吐白沫,一副活不多久的模样。
詹小月大惊,叫道:“爷爷,爷爷,你,你没事吧。”又转头向那冲撞之人。“你这死炭头,黑炭头,我让你撞开那些人,谁让你撞我爷爷了。他一把年纪,哪经得起如此冲撞?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与你没完。”
来人正是胡川。在周蛮等人寻他之时,他也回返寻找众人。他与詹子相同方向,可惜尚未见面,詹子和詹小月便被人捉了。他一路寻来,寻到此处,见双方形势,大略猜到一二。他粗中有细,未惊动他人,先与詹小月联系。方才詹小月东张西望便是在找他。
他被詹小月骂得面红,低声辩解道:“有两人押着他,旁边还有人看管。俺一人只能撞倒一个,便是撞开了他也逃不了,倒不如俺直接将他撞飞来得干脆。”
詹小月气道:“干脆,干脆,你干脆把我爷爷直接撞死,他现在是死得干脆了。”
詹子噗的喷了一下,脖子挺直,呼吸逐渐恢复,颤抖着抓住詹小月的手,艰难道:“娃儿,娃儿。”
詹小月道:“爷爷,我在。”
詹子悲声道:“莫非你也死了?我可怜的孩子。”
詹小月一拳敲在他头上,叫道:“爷爷,你说什么胡话?我没死,你也没死。”
詹子张开眼睛,惊奇道:“当真?我,我当真未死?”
周蛮道:“詹老爹,您未死。我检查过你身上,除脖子有些扭伤,其他无碍。”
詹子哭道:“你骗我,你定是在骗我。我老骨头一把,一下子飞了五丈,怎会没受伤?”
周蛮为难道:“可詹老爹,你确实没受伤。”
詹子道:“当真?”
周蛮点头道:“当真。”
詹子在詹小月的搀扶下起身,对那些捉他之人看也不看,道:“那我们便走吧,寻个清静地方休息,晚上还有事做。”
胡川叫道:“喂,你们等等,俺,俺还没出去呢。”他将詹子撞飞,自己却陷入对方包围之中,此刻有五六人提着各式家伙凶狠的瞪着他。
詹子如同未闻,自顾和周蛮道:“晚上你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和娃儿只能在外把风,入府救人便全指望你了。进去后不要管其他,直奔后院。人才被抢去几天,新婚的房子该很易辨认。你只消将里面年轻的姑娘带走便可。若是她不肯与你走,你便将其打晕,扛她出来。以你之膂力,伏个轻盈少女该不成问题。”
詹小月道:“爷爷,你这不是让蛮去当土匪么?”
詹子道:“反正都是抢人,她自愿走还是我们强迫她走,其结果还不都一样。”
周蛮为难道:“如此不妥吧。”
詹子道:“不然你说如何?她不和你走你便不带她走了?”
周蛮回头望向胡川,道:“带他一同入府。有他在,说明情况,那姑娘定会相信我们。”
詹子皱眉道:“他,他是何人?”
周蛮道:“胡川啊。”
胡川在远处大叫道:“俺,俺便是胡川。是俺啊詹老爹。”
詹子瞥他一眼,一副今日才见的神情,淡淡道:“这位公子是谁,为何老夫从未见过?”
周蛮担心道:“难道詹老爹撞到头了不成?”
詹小月甩手哼道:“爷爷只是小气而已。”
詹子跳将起来,大叫道:“何为小气?这小混蛋竟然敢撞我?若非我这身老骨头还算结实,方才便被他撞得去见你奶奶了。便是不被撞死,也好个骨断筋折,半身残废,余下残生只能在榻上度过。如此狂野凶残之人,我不识得,不识得。”
周蛮知詹子又耍小孩脾气,若要劝动只怕不易。
胡川嚷道:“詹老爹,俺,俺知道错了。俺方才不是有意的。”
詹子哼道:“你不是有意便将我撞出五丈,若是有意,岂非将我撞上了天?”
胡川本就不善言语,此刻焦急得说不出话来。身后一人不耐,提一把耙子向他打来。他匆忙向旁一闪,让过耙子,转身冲入那人怀中,将其拦腰抱起,仗着一身蛮力,双臂勒紧,夹得那人惨叫不止。
两侧人急忙上前营救,他用力一摔,将那人丢在地上,拾起耙子无章无法的一阵乱舞,惊得人人后退,无人敢靠近。
詹子哼道:“看,他不是好好的,何必我们去管。”正言间,耙子啪的打在树上,几个钩子刺入树干,震得他手臂发麻,丢了耙子,向后倒退几步,坐倒在地。
詹子又道:“看,那种废物便是带上也无用处,便让他在此自生自灭,何必我们去管。”
詹小月道:“爷爷,若是胡川死了,我们如何向他娘和他哥交代。”
詹子不负责任的道:“又非老夫将其杀死,何许交代?”
周蛮无奈,眼见数人靠近胡川,无法放任不理,只得甩大步冲去。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几把锄头已然砸向胡川头顶。
眼前胡川要被砸得头破血流,先前那年轻人忽地大叫一声:“住手。”锄头纷纷停住。有些停不住力道者索性将头一偏,砸在别处。有几人因此碰撞,震得锄头脱手,乱成一团。
那年轻人疾走上前,盯着胡川道:“你,你莫非便是胡山的弟弟?”
胡川傻愣愣道:“俺哥是叫胡山,怎地?”
那年轻人喜道:“果然是你。你和你哥长得真像,不然我也认不出。”
胡川道:“你认识俺哥?”
那年轻人道:“你可知我是谁?”
胡川奇道:“你一来便虏了人去,俺如何知道?”
那人道:“我叫胡豹,我有一姐,名唤莺莺。你娘到我家提亲时,我曾见过你哥一面。”
此言一出,不仅胡川,便是周蛮,詹子,詹小月亦是一怔。四人面面相觑,不免一叹。这岂非自家人打了自家人?
胡豹道:“亭长那畜牲,竟带人去抓了我姐与他那已死的儿子成亲。抓人时我上山采药,不在家中,回家时人已被他们带走。我气不过,叫上几个好兄弟,专程来此,便是为救我姐。半路遇到他们,怕是亭长眼线,通风报讯,坏了我的事,这才出手捉了。”向詹子和詹小月抱拳道:“二位,方才多有得罪,还请恕罪。”
詹小月道:“不知者不罪,且也未将我如何,便算了吧。”
詹子瞪着胡川哼道:“我这伤也怨不到你们头上,倒是有些人,哼。”
胡豹向胡川望去,后者垂着一张黑面,不敢言语。
周蛮道:“既然都是自家人,前者之事不提也罢。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晚上如何行动。”
詹子向胡豹问道:“你们有何打算?”
胡豹道:“我姐与亭长家本无婚约,他们虽下了聘礼,但我娘已原物奉还,并未收下。他如今抢人,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我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姐受这份罪,一时气愤便带人来了。心中只想着先把人抢出来,其他倒未考虑。不知老先生有何安排?”
詹子道:“凭你们几人,趁其不备,抢人尚可成功,但防得一时,防不了一世,之后亭长大可再将人抢回。”
胡豹点头道:“老先生说得有理,那我们该当如何?”
詹子道:“以我们商量,莺莺姑娘万不可回家。”接着将与胡母、胡山等一同逃离的计划讲述一遍。
胡豹沉吟片刻,点头道:“如今也只有如此。我娘也收了胡山聘礼,我姐本就是他胡山的人,随他离开也算夫唱妇随。”
詹子点头道:“既然你也答应,事情便简单了。我们暂且休息,三更行动。”
胡豹这次带来十二人,皆是弱冠之龄的青年,与胡豹青梅竹马,情同手足。对胡莺莺之遭遇感同身受,故此豁出性命前来助阵。
年轻人聚会总是相熟得快,未久便热情交谈起来。气氛变得轻松,时间亦过得轻快。詹小月开心得四处乱跑,周蛮则被十几人围拢,赞叹他体格与力量。胡川向之前被己所伤之人道歉,对方也是豪爽汉子,两人敬了一杯酒便前隙解除。唯詹子一人坐于众人之外,眼见年轻人说笑打闹,他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只得兀自蒙头大睡,生着闷气。
话说入夜后,四下漆黑。谚云:二十一二里,月从半夜起。这片黑暗正给了周蛮等人方便。他们二更三点启程,悄悄绕回村口。他们人数众多,不可尽入,只周蛮,胡川,胡豹,另选两人同去。余者三人一组,两组于村口接应,一组盯住护卫民兵,剩余一组留守小树林中等候。至于詹子与詹小月自然留下。若是没有胡豹等人,他二人也许进村以便在亭长家外把风。可如今人选众多,詹子怎会情愿担此风险?
一切布置妥当,周蛮在先,胡豹断后,五人潜入村中。村里寂静无声,各家均已睡去。他们向前行过街口,方一转,便见一所红门小院。院中微见灯火,似有鼓乐之声。
胡川道:“这就是亭长的家。听说他有一房小妾,会唱几首曲儿。哼,这老东西倒会享受。”
周蛮点头,继续向前。他们自然不能从正门进入,转向西墙。西墙较其他处稍矮,只与周蛮等高。周蛮稍一颠脚便可看清里面。他认定里面无人,一纵便跃入院中。其他人两人一组,搭脚而上。
五人进入院中,正要去后院,忽闻人声,急忙缩身在墙角几株枯瘦小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