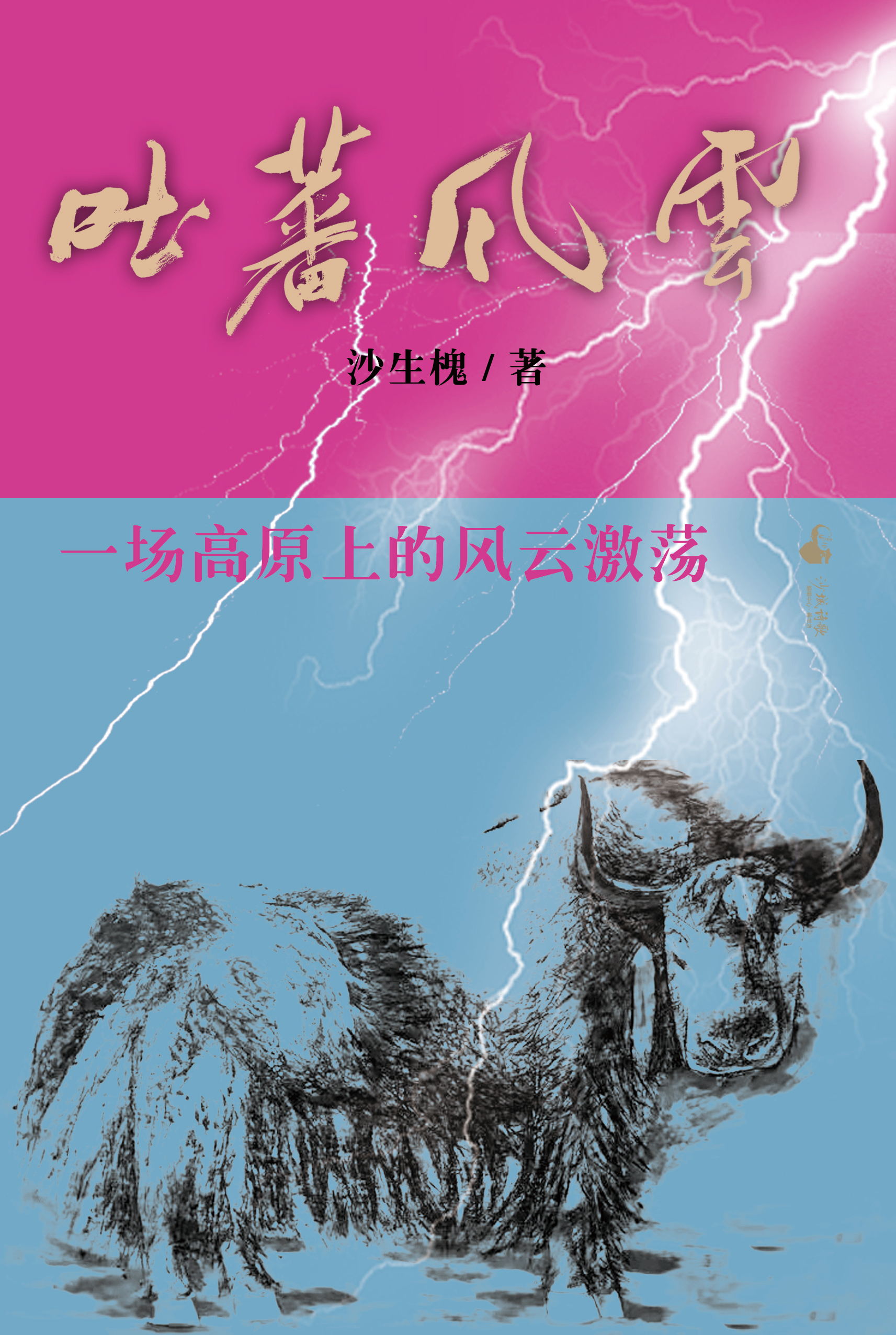周蛮长叹一声,甚是沮丧。
詹小月忙道:“蛮,你别担心。上次也是仅有一块碎片,你不一样找到了地方。这次我们三人一起,一定可以找到。”
周蛮知她只是安慰自己,勉强点头一笑。
詹子道:“其实你们无需担心,那地图我早已熟记于心,便是没有也无妨。”
周蛮一惊,望向詹子,道:“詹老爹,此话当真?”
詹子笑道:“自是当真,我何时骗过你。”
詹小月皱眉道:“蛮,你别高兴得太早。爷爷的话十有**是假话。”
詹子叫道:“你这丫头,尽会数落你爷爷。那地图我是当真背下。你们以为这些日来我们只是漫无目的的乱走?我们正走在前往地图所标之处的捷径。”
詹小月仍有狐疑,道:“当真?”
詹子哼道:“你们以为我老人家与你们这些孩子一般,玩得忘了正事?”
周蛮喜道:“多谢詹老爹。”
詹子笑道:“好了,如今没事了,可以睡觉了吧?”
周蛮点头道:“嗯,可以睡觉了。”
一早醒来,三人吃过早餐,继续前行。周蛮只觉寻父之旅越来越清晰,心情自然大好。三人顺山路而走,逐渐偏向东南一方。
山势并不陡峭,遍野青翠,景色秀丽。三人边走边聊,周蛮凝视山林,思及小城,不免感触道:“人当真古怪,在地上盖起房屋,垒起城墙,在获得安逸的同时却也失去了笑傲山林的自由。如此自我禁锢,难道就不会闷?”
詹小月笑道:“自然不闷,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啊。”
詹子笑道:“你可又知道些什么?从你懂事起便住在山里哩。”
詹小月哼道:“就算不知道,我也想象得到。哪像蛮,大笨蛋,连想象都不会。”
周蛮伸手将詹小月提起,在空中晃了几晃,直晃得她头昏脑胀才放下,笑道:“看你可还敢说我?”
詹小月丝毫不惧,只是咯咯的笑个不停,别提多开心。
经过一片小林,前面出现一块空地。空地中央一座古怪的高型建筑吸引了周蛮的注意。
他指着那建筑问道:“詹老爹,那是什么?”
詹小月抢着道:“那个你都不知道,那个是,是……爷爷,那是什么来着?”
詹子笑道:“那是塔。看这破损的模样,只怕已有数百年历史。”
詹小月连忙道:“是了,是了,就是塔。我刚才本要说,只是爷爷嘴快,抢在了前头。蛮,听我说话。”
詹子无奈苦笑。他如何能比伶牙俐齿的詹小月还要嘴快?
周蛮笑道:“我在听。那是塔。可为什么塔和其他的建筑不一样?”
詹小月哼道:“哼哼,你可真笨。如果都一样,那它还叫塔来做什么?”
周蛮和詹子面面相觑,不禁为之气节,莞尔一笑。
詹子想起什么,突然问道:“蛮,早几日我便发觉,你右臂上何时多出那条红色纹身?”
周蛮淡淡道:“它如何出现我也不知,只是当日……”话到一半却停住,瞥了詹小月一下,未免她记起小城惨状,避过她耳目,压低声音道:“当日在那小城与野人交战时突然出现。当时疼痛难当,我只道这条胳膊就此废了,谁知只多出这样一个印记,还平添一股诡异之力。那股力量坚不可摧,怪哉,怪哉。”
詹子微微颔首,面色凝重,喃喃道:“该不会是……蛮,你日后要多加留意这纹身,再有变化立即告诉我。”
周蛮正欲回答,却被詹小月抢先。后者未听到周蛮之言,知其有意避她,心下不满,正巧听到詹子的话,便哼道:“区区一个纹身有何了不起?山下村里很多人身上都有,只不过他们是干农活时不小心画上去的。”
詹子无奈道:“那是疤痕。”
詹小月理直气壮道:“又差不多。”
詹子心思仍在那红线之上,不与她争辩,兀自沉吟。
三人又行一段,进入另一座小山。小山不高,但地势崎岖,怪石嶙峋。树叶甚是茂密,连接在一起,青天白日也很难见到阳光。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树叶沙沙响,树洞呜呜鸣,颇有些阴森感觉。
詹小月一手拉着詹子,一手拉着周蛮,每每有声音,便缩到周蛮身边。久了,周蛮索性将她抱起,又折条树枝给她。她拿着树枝拍拍打打,玩性上来,也就忘了害怕。
前方峰回路转,出现一条吊桥。吊桥老旧,悬于峡谷之间,怕有五丈开外。吊桥上绳索单薄,每每有风吹过,在半空悠悠颤颤,飘飘荡荡,甚是可怖。
詹小月打个寒颤,道:“我们该不会要由此而过吧?”
周蛮道:“要想前进,别无他路。”
詹小月一个头摇成几个,鞭炮般噼里啪啦的叫道:“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这破桥落根羽毛便会掉两条木板,若是人走上去还有得活?反正我们也并非定要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不是一样?是了,方才的地方若是右转,也许有新的下山路径。我们不若回头重走,不用与这岌岌可危的险桥对眼睛。”
詹子为难道:“回头是可以,但如此一来便过不了这条山谷。”
詹小月道:“不能过便不过。对面又没金子,又没珠宝,过去也讨不得什么好。”
詹子道:“偏了方向,要如何寻找蛮父亲留下的线索?”
詹小月低声嘀咕道:“不寻就不寻嘛。”偷望周蛮一眼,叹息道:“大不了我们绕路而行,只是多耽搁些时间罢了。反正又不着急,怕得什么。”
周蛮在桥上简做尝试,点头道:“桥板虽然简陋,但还算结实。就算我们三人走在上面亦不会有事。”
詹小月躲得老远,抱着棵大树嚷道:“我都说不去,你还试来干嘛?”
周蛮笑道:“自然是要过去。”言罢不顾詹小月反对,径自走了上去。他每踏一步,桥板便咯吱吱响上一声,虽吓人,却平安无事。
詹小月大叫道:“臭蛮,死蛮,竟然不管我。好,你走,我偏不走,看你如何?”
詹小月双手抱胸,坐在桥头发脾气,詹子却也跟着上了桥。詹小月大出预料,叫道:“爷爷,你平时不是胆小得很,怎么这时来了勇气?你,你难道不该与你可爱的孙女统一战线?你,你这是背信弃义,小人行径。”叫了大半晌,见无人理她,周蛮此时已过了中点,不由焦急起来,跺足道:“好,好,一个个都是坏家伙,欺负我,看我以后还睬不睬你们。”口中如是说着,却也乖乖的跟着上了桥。
就在周蛮即将过得桥时,在对面树丛中忽然跃出两人。那两人中等身材,生得皮肤黝黑,面容粗犷,须发蓬乱。他二人手中提着砍柴的斧头,拦在桥边高喝一声:“站住。”
周蛮与詹子同时止步,詹小月胆小,吓得紧跑几步,躲在詹子背后,侧身露出小脑袋朝周蛮叫道:“都是你这头大笨牛。看看,被人截了吧。若是早听我之言,绕路而行,怎会遇此窘境?”
其中一个劫匪叫道:“闭嘴。”他面目凶恶,声音憨声憨气,惊得詹小月缩回头去,不敢再出来。
另一劫匪道:“你们三人听好,将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扔过来。”
詹小月低声道:“全不扔过去?既然不扔,又说来干嘛?”说完自己噗哧一声笑了。
她声音虽低,但童音清脆,那两名劫匪听得真切。其中一人急了,嚷道:“俺说全部,不是全不。”
詹小月抑扬顿挫的道:“什么全不全不的,同样的话反复说两遍,真是莫明其妙。”
那劫匪怒道:“俺说全部,不是全不。你小娃娃耳聋是不,听不懂人话?”
詹小月道:“本姑娘是人,人话自然是听得懂的。你明明说的全不,全不者全都不是也。这便是人话的理解。怎么,难道你说的话不能如此理解?那便是说你所说的并非人话。嗯,原来你说的不是人话,难怪我理解不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那劫匪急了,可又说不过詹小月,气得哇哇直叫。
周蛮未免詹小月将对方逼急,高声道:“你见我等可像富贵人家?身上何来值钱之物。”
那两人同时愕然,寻思良久,稍稍年长那人叫道:“总之你们得交出些东西,否则俺就斩断这绳桥,让你们大的小的统统跌下谷去,摔个稀巴烂。”
詹子忙道:“壮士且慢动手,你,你看看我们。我们祖孙老得老,小得小,身上哪能有钱。钱都在他身上。”他向周蛮一指。“大约有百来钱,虽然不多,若是两位壮士有意,统统拿去便是。”实则他们的钱都在詹子身上,最多不过五两,十枚半两钱。
那两人一听有百钱,顿时眉开眼笑,指着周蛮道:“你身上果然有钱,速速拿来。”
周蛮向詹子一瞥,心头暗叹:“您老怎地老毛病又犯了,遇到事情便将我向外推。”却也是无奈,只得道:“钱确在我身上。你先让他二人过去,我再将钱给你。若是不然,我把钱给了你,你再砍断绳索,我岂非丢了钱财又丢了性命。”
年纪较轻的劫匪叫道:“难道你信不过俺们兄弟?俺们兄弟在这附近最是说一不二,决不毁约,谁人不知?”
詹小月撇嘴道:“既是如此好人,又为何要拦桥抢劫?”
二人语塞,神情尴尬,支吾半天也回答不出。
詹子道:“两位壮士,我们身上又无钱财,又为老弱,便放我们过去吧。”
年长的劫匪寻思良久,点头道:“好吧,就让你们过去。快点,我们还等着钱吃饭。”
詹子道:“是是,立刻就过去。”他拉着詹小月过桥,忽地一阵风起,将吊桥吹得如秋千般荡起,几欲翻转过来,吓得詹子祖孙抱紧绳索一阵惨叫。
他们惨叫声甚是骇人,便连那两个劫匪也不由得一惊。其中一人慌忙道:“咋,咋了?小心,别,别摔下去。”
周蛮虽闻他二人叫得惊险,但见詹子紧紧抓住绳索,料定不会有事,趁那两名劫匪尚未回过神,纵身跃过桥去,双臂张开,一手一个,抓着那两人的头脸,好似扔石子般将二人甩了出去。那两人腾空飞起,身在半空仍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周蛮抓住两条绳索,向怀中一拉,竟将原本弯曲的桥拉直。他道:“詹老爹,娃儿,快过来,免得再起风。”
詹子搭在绳索上,心有余悸的抹着汗,点头相应,口中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拉着詹小月以最快速度通过吊桥,到了对岸,祖孙两人一同躺在地上。面色苍白,通身是汗,仿佛死过一次般。
那两名劫匪站起,盯着周蛮叫道:“你这卑鄙之人,竟然偷袭俺们。”
周蛮道:“若非你二人卑鄙在先,将我们截在桥上,胁迫我们,我又怎会偷袭你等。”
那两人应答不上,若非黑脸看不出颜色定是大红一片。年长那人不服气道:“就算不在桥上,关系也没改变。你们快些交出钱财,否则我将你们全都砍成碎片。”他将斧头在空中晃了晃,斧刃寒光闪烁,可见经过细心打磨,锋利非常。
以他二人体格,再加上手中的斧头。若是寻常人见了定会心惊胆跳,应了他们要求,乖乖交出财物。可惜周蛮身材强过他们,又见识过比他们凶狠百倍的角色,全未将这二人放入眼中。
詹子脱离险境,胆子也壮了。他叫道:“你们两头呆子,用树叶擦擦眼,我们哪里像是有钱人?劫谁不好,偏偏选中我们?我们自己连吃饭的钱也不见,何来钱物送你们。快快回家种地,讨生活去。”
年长劫匪道:“你们瞎说,休想骗俺。你们一定有钱,速速拿来,也免得动手伤了皮肉。”
周蛮只觉这两人本性不恶,拱手道:“两位兄台,不若我们打个商量。我们尚有几块干粮,尽数赠与你们,你们则让我们通过。如此一来省去一场无谓争斗,两位意下如何?”
年轻劫匪欢喜道:“有干粮?好唉,是什么?”却被年长者很揍了一拳。后者道:“你们休想哄俺,留下钱物,放你们过去。若不然便留下你们的尸首。”
詹小月才从吊桥的惊骇中回过神来,气煞了这两个劫匪,咬牙叫道:“蛮,给我教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呼,险些没要了本姑娘的命。”
周蛮无奈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动手了。”
那两个汉子见周蛮走来,嘿嘿笑道:“你小子身量倒高,却不知中不中用。”将斧头挥舞几下,朝着周蛮胸口便是一斧。
斧头挂风,应声而来。见那气势凶狠,詹小月又不免有些后悔。若只为她出口恶气,却使周蛮有个闪失,伤了皮肉可得不偿失。
周蛮毫不惊慌,扭身闪过斧刃,探掌抓其手腕,向怀中一带,那两人便是一个趔趄。手腕翻转,向外一推,那两人丢了斧头,倒摔出去。
周蛮哈哈大笑,道:“凭你二人的本事也来劫道?速速拾回斧头返回家去,日后做些个砍柴伐木的生意维持家计吧。”
那二人傻呆呆瘫坐于地,惊愕的看着周蛮,良久说不出话来。
半晌,年长者垂首道:“俺们败了,你们走吧。”
詹小月跳出来道:“走?想得容易。方才本姑娘所受的惊吓,如今要你们双倍偿还。”
那二人就地盘膝而坐,仰头道:“俺们兄弟啥也没有,你要杀便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模样。气得詹小月哇哇跳脚,大叫着:“蛮,给我揍他们,揍他们。真气死我了。”
周蛮无奈一笑,望向詹子。詹子上前道:“你二人叫什么名字?”
年长者道:“俺是哥哥,叫胡山。”
另一人道:“俺是弟弟,叫胡川。”
詹子点头,又问道:“家住何处?家中尚有何人?因何上山做了劫匪?”
胡山道:“问这些来干嘛?”
詹小月飞扬跋扈的叫道:“你们既然输了,就该服从我们。问你们什么便如实回答,没资格提问,更没资格反驳。听到没有。”
胡山实心肠,一根筋,不知詹小月故意耍弄他,叹道:“俺们兄弟本是山下七里外一个小村的农户,家中尚有老娘和一个妹子,叫胡小花。妹子去年嫁入邻村一猎户家,家境丰厚,日食无忧,家里剩下俺们兄弟和老娘三人。家中有一块田,虽然不大,但每日耕田锄地,辛苦是辛苦了些,倒也能养活家口。”
詹小月刁蛮道:“既然如此,又何故跑上山来劫道?我看你们定是未说实话。”
胡川忙道:“俺哥并未扯谎。俺家原本日子过得不错,两月前还托人联系了一户人家,要与俺哥成亲。本来一切都好,可气那亭长家的儿子胡二,仗势欺人,瞧上了俺那未过门的嫂子,竟硬要俺家退亲。俺娘不允,他竟动手打了俺娘。俺和俺哥一时气不过,上去揍了那龟儿子两拳。谁知那小子水货得很,经不起拳头,才几下就那么死了。摊上了人命,俺和俺哥怕吃官司,只好趁夜逃到山上,避避风头。”
胡山道:“开始时娘她尚且每日上山送饭给俺们,可时日久了,亭长又调查得严,便没法再送。俺们并非猎户,不善打鸡抓兔的手艺,在山上过了整月,最近十天仅以树叶充饥,已经挨不下去了。正巧这时见到你们,便想打劫抢些钱来,也好吃顿饱饭。”
詹子道:“就算你们抢到钱物,打算去哪里吃饭?”
胡山道:“自然是去馆子。天下有了钱还怕没有饭吃?”
詹子问道:“馆子在何处?”
胡山道:“山下几个村子里都有。嗯,说起来村东头二伯家的辣子肉最是香,想起就流口水。”
詹子叹道:“你们难道不是为避风头才上山的?此时下山进村,就不怕被亭长的手下抓起来?”
胡氏兄弟面面相觑,竟是全未想到此处。詹子与周蛮相视摇头,这兄弟人虽不坏,脑筋却不灵光。
胡川瞪着周蛮,不服的道:“若非俺与俺哥饿得发慌,全身无力,咋会被你一下撩倒?”
詹小月气呼呼的道:“被捉还趾高气扬,你们两个黑炭头打死人还有理了不成?”
胡山道:“那胡二不是好东西,想抢俺媳妇,又打俺娘,便是被俺打死也是活该。”
詹小月道:“那你们逃上山来,把老母亲一人留在家中便不是过错?你们这两个不孝的黑炭头。”
兄弟二人垂头不语,他们均是孝子,如何能不担心家中老母。若非惹下人命官司,被逼无奈,便是断了腿也会下山。
周蛮拦住还要训斥他们的詹小月,叹道:“他们也是可怜,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们了。多余的干粮分他们一些,就算不能吃饱,总比没有强些。”
詹子点头道:“你们走吧。事情过了一月,也许风声已过,早些回家去看看你们的母亲吧。”
两兄弟感激涕零,接过两张大饼,磕头道谢,含着泪跑了。
詹小月看着他们离开,嘻笑道:“他们两个还真有趣,呼的一下跑出来,又嗖的一声跑出去。”
詹子道:“他们也是可怜人。正好我们也要下山,不如便去他们的村子瞧瞧,若是风声过了,也好通知他们回家孝敬老母。”
周蛮点头道:“如此甚好。”
三人下山,依照胡山所讲,在山下七里外找到一座小村。村子不大,约有二十几户人家。土墙砖瓦,木栅小院,看起来十分寻常。村中多是农户,从各家门口摆放的农具便可见一斑。
三人进村,由村西走到村东,竟未遇一人,不禁奇怪。村东头有一家小酒馆,门面不大,仅有一个酒字招牌迎风招展。三人进入,里面早有一桌人四个汉子,点了酒肉边吃边聊。
周蛮在旁边一桌坐下,詹子唤小二,可村里小店哪来小二,只有老板一人而已。詹子欲点菜,向老板讨要菜单。老板却道:“村里识字人少,小店没有菜单。”
詹子一想,也是道理,便道:“有什么拿手菜,随便上几道。另外馒头十个,再包二十张大饼。”
老板听了并未离去。詹子还道他等候其要酒,便道:“我们赶路辛苦,酒就免了,上一壶茶便可。”
老板仍旧不动。
詹子微微皱眉,略带不悦道:“老板,为何不去准备?”
老板道:“几位爷,你们确定要点我这的拿手菜?”
詹小月奇道:“怎么?难道拿手菜还不能点了?”
老板露出一丝别样的笑容,道:“并非不能点。但那几道菜多是附近人吃,外地的商客怕是吃不惯啊。”
周蛮笑道:“正因是外地人,才希望到各地品尝当地土产。老板,你只管上来便是。”
老板道:“既然几位爷如此说,那小得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三道小店招牌菜,马上便好。”
老板下去,不多时端上三大盘菜和两盘馒头。那三盘菜只一上桌,周蛮与詹小月顿时傻了眼。那是三道怎样的菜,红彤彤好似三盘烧红的火炭,热气蒸腾,整个酒馆都热了几度。
詹子笑眯眯道:“哦,这辣子肉的火候刚好,老板手艺不错。”
老板笑道:“这位爷很懂行啊。”
詹子道:“年岁大了,活得久了,见的东西也自然多了。”见周蛮和詹小月那副惊叹模样,洋洋一笑。“我年轻时初尝这辣子肉,亦和他们一般。哈哈,如今想起,还真是怀念啊。”夹了一块,闭目咀嚼,似乎十分享受。良久,续道:“嗯,恰到好处,好,好,好。”
见詹子连说三个好字,又吃得那般享受,周蛮好奇,也夹了一块。肉方入唇,只觉一股酥麻感传遍满口。他正自吃惊,那股感觉却一瞬即逝。肉香飘逸,满口酥滑。他越吃越香,不禁又夹了一块。
詹子略带吃惊的看着周蛮,就连那老板与另一桌的几个村民也被其吸引。
詹小月见爷爷吃了,周蛮又吃得香甜,料想这肉只表面吓人,便也夹了一块放入口中。才一入口,她便大叫一声,将肉吐在地上,眼泪汪汪,舌头伸出,含含糊糊的也不知在叫着什么。
那老板早知会如此,忙递上一杯清水。詹小月喝了水放好些,可舌头酥麻,满口火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桌汉子哈哈大笑,个子最高的一人道:“姑娘,这二哥的辣子肉香是香,却也不是谁都能吃的。”
詹小月气呼呼哼了一声,指了指詹子,又指了指周蛮,似乎在说:“他们既然吃得,为何我就吃不得?”
詹子才吃几块便通身是汗,款掉外衫,笑道:“丫头,爷爷若非曾经吃过,现在也与你一般了。”
周蛮却是一副莫名的看着詹小月,他吃得正香,全然不懂詹小月所受的苦。
那老板惊叹道:“这位小哥好厉害,便是我也不能这样吃。”
周蛮不明所以,对老板道:“这肉香醇可口,再来一盘。”
老板笑道:“好嘞,能有小哥这样的客官,我便是再做十盘也甘愿。这盘我请。”
周蛮笑道:“多谢老板。”
詹小月吃过那辣子肉后得了教训,另两道菜也不敢动,就见周蛮吃得香,心下有气,在他身上狠掐一下。可周蛮体格结实,全不在意,依旧大块朵颐。
那高个汉子问道:“几位,哪的人啊?”
詹子笑道:“三川郡来的,做些小买卖,办货正巧路过此地。”
那汉子道:“哦,这离家可够远的。”
詹子道:“小本生意,就是得多劳累些。”
汉子道:“这位小哥是?”
詹子道:“这是我外孙,人高大些,吃得虽多,力气却足,有他帮忙搬货,我也省心些。”
汉子点头道:“那这小姑娘。”
詹小月抢着道:“我是爷爷的孙女。”
汉子笑道:“小姑娘跟着爷爷来办货,难道不怕辛苦?”
詹小月哼道:“整天闷在家里才叫辛苦,这大好机会出来游玩,我怎能不来?”
詹子惭愧道:“这孙女是我心头肉,她硬要跟来,我也无奈。”
汉子道:“年轻时让小孩子多走走也是好的,不过女娃家,还是留在家里为是。”
詹小月心头不满,要争辩却被詹子拦住。詹子点头道:“说得有理。对了,敢问此村叫什么村?”
汉子笑道:“这有什么名字,远近四五个小村都姓胡,都是胡家村。我们这距离后山正巧七里,人们都叫这为七里胡家村。”
詹子又道:“附近可有什么事端?你知道,我们小本生意人,出门在外,最怕就是遇到劫匪强盗。”
另一个矮胖汉子几杯酒下肚,面铺一层粉红,道:“乡里的啬夫、游徼还算卖力,这附近连小贼也不常见,盗匪之类更是没有。要说不太平,除了上月亭长家的儿子……”
那汉子还要说,却被高个汉子打断,后者呵斥道:“老三,别胡说,想挨板子么?”
那矮胖汉子一惊,闭口不言。
詹子暗自揣摩,虽然未得确切消息,但看那高个汉子的反应也知风声未过。想那胡家老母怕是还要受些苦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