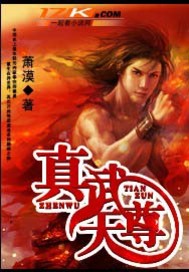顾翼托着腮帮,心中着实郁闷。要不是他在陛下面前说了不该说的话,表哥怎会撇下他独自离去?
晖夜与晖日那是多年不见的亲兄弟啊,自然有很多贴己话要说,于是乎嚣张跋扈的顾二公子,独自一人呆在房中属实郁闷的很。
秦铃挎着食盒走了进来,一眼就看见趴在桌子上玩杯子的顾翼,说道:“听婢女说,你没有吃晚饭,我带了些,你吃点。”
顾翼闻言抬起头,表情颇为无辜、难过的问道:“表姐,表哥还没回来吗?”
秦铃一边摆着点心一边摇了摇头。
顾翼撇了撇嘴,不再说话。秦铃望了望窗外的天,暮色临落,外面已经开始掌灯了。兄长很少会这个时间回来,想必定是有什么事情拦住了,而今日进宫面圣,乔安、晖夜都没跟着,秦铃心中难免不担心。
顾翼一点也没有今天面圣的事情跟秦铃说,到底是怕她一个妇道人家知道后难免会瞎担心、自乱阵脚,还不如瞒着她比较好。
秦铃坐了下来,柔声问道:“阿翼,你老实告诉表姐,今日面圣,到底发生了什么?”
顾翼闻言避重就轻的与秦铃说了,秦铃听完眉头都皱紧了,一指头戳在顾翼的脑门上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儿?那怡亲王好歹是皇上的亲叔叔,那李鹤烨怎么说也是皇上的堂弟,如今出了兵败案这件事情,李鹤烨的事情多少有些敏感,你怎么还往上面撞啊?”
就在秦铃还在训顾翼的时候,有侍女来报说世子回来了,现在在王爷书房。顾翼听到秦熹回来,立刻起身想要去见状,可一听到秦熹去了书房,心中又难免害怕。
虽说,漠北王秦霄是名儒将。但还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不怒自威的气势让人胆颤心惊。更何况那人到底还是自己的威名在外的姨夫,顾翼面对谁都能游刃有余但唯独自己这个姨夫。
与狼王相比雏鹰实在是太过弱小了,秦铃安慰他道:“陛下叫你独自入都,目的已经不言而喻。我与兄长只能护你一时,不能护你一世。你独自一人在京都,更要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你且呆在这里,我去探探口风。”
这些道理顾翼都懂,他也明白皇帝召他入都是为了牵制渭西和漠北。渭西和漠北是表亲,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牵制渭西就相当于间接牵制漠北,这天麟帝倒是下的一手好棋。表面上对漠北皇恩浩荡,打压渭西。暗地里却借打压渭西的借口,牵制漠北。
帝王之心,如大海捞针。秦熹他难道不明白吗?就是因为他太明白了,所以就要在这种事情上装傻。
有时候,装傻也是保全自己的一种必要手段。顾翼当真如此蠢笨会分不清什么场合该说什么,什么场合不该说什么吗?
他当然明白,只是因为秦熹在他身边。他信赖和依赖自己的这位表兄,他本无兄长。至于他们为什么都叫他“顾二公子”,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个长姐。
因为他知道不管他犯什么错误,闯了多大的祸,他的表哥和晖日都会帮他完善。虽说他有个长姐,但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据家里的乳母说是远嫁了。
母亲也是长期以泪洗面,家里人也是很少谈起自己这位长姐。都恐让母亲想起伤心事,自己对这位长姐没有什么感觉,若是就心而论的话,自己还是心里更会偏向秦熹多一些。
可是吧,狼崽要放逐野外学会残忍的历练,他不可能陪着雏鹰一起继续幼稚,他肩负着整个西北的荣耀。而雏鹰也要离开一直依靠的狼崽去完成独自飞翔的历练,最后成为那个展翅遮天、护佑一方的雄鹰。
不会独自狩猎的狼崽面临着死亡,不会翱翔的雏鹰要面对的也是死亡。顾翼很明白,他只是想在秦熹身边多待一点,只是一点就好,这样他才觉得他们还是幼时,一切都没有变,不用想象自己背负着怎样的荣辱,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
因为金吾卫的这一层关系,秦熹骑着良骥急行在神武大街,几乎是畅通无阻。宵禁之后的街道清净通畅,秦熹丝毫不用担心在大街上疾驰会撞到人。
临漠北王府近来,就看见院府门前那两只大且通红的秦字灯笼。晖夜在门口踱步,焦急的向门口张望。直到离王府不到五十米的距离,这才看见黑夜中的一抹棕红,之后秦熹整个人就映入他的整个眼眶。
晖夜欣喜的跑过去牵过良骥,对秦熹说道:“王爷吩咐了,要是世子回来,就去书房一趟。”秦熹点了点头,晖夜将手中的缰绳塞给旁边的小厮,就跟着秦熹去了书房。
漠北王秦霄这时提着毛笔,在纸上不知写着什么。看着地上的几个纸团,便可以猜测是想了好久,况且都不满意,就一一作废了。临近书房的时候,秦熹就看见书房房门大开,屋内明亮通透。他挥了挥手,打发晖夜去找晖日。
而自己悄声的走到秦霄的身边,拿起放在砚上的墨块默默的研磨着。父子之间一时间无言,气氛温馨且冷清。最终还是秦熹开口说道:“爹,我今日…”。秦霄开口打断他道:“今日之事,我已经听说了。事情错不在你,但你作为兄长应该看顾好阿翼。”
秦熹低着头,沉默不语,好像今日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失一样。秦霄头都没抬就知道秦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表情,自己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心思太重了。哪怕一点小事,都会往心里去。凡是弟弟妹妹的过错,他都认为是自己的过错。
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阿翼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不需要你的保护。雏鹰和狼崽都需要长大,你的过分保护只会害了他。”秦霄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实在是太了解,这性情简直和他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死心眼啊。
秦熹的神情晦暗不明说道:“儿子知道。”秦霄这才偏头看向秦熹,这小子哪里还有武将的样子?这分明就是个文弱书生,也就高了点、壮了点。
这是秦霄忽然想到了周将军家的那个小子,与阿熹的年纪也差不开多少,明明是个武将世家的公子,偏偏却喜欢舞文弄墨。也不知是好是坏。
秦霄看着秦熹略带单薄的肩膀和后背,眉头轻皱说道:“明日将拳多打两遍,后天就是你的束发礼了,这表字可取好了?”秦熹摇了摇头,依旧垂首磨墨说:“还没。”秦霄看着秦熹的动作,心里稍微有点不痛快。他向来直来直去的,最烦的就是秦熹这有话藏着掖着的样子。
秦霄一巴掌呼在秦熹的后脑勺上,有些微怒道:“我怎么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唯唯诺诺的,也不知道随谁了?”秦熹被拍的有些踉跄,皱起了眉也有些不满说:“爹,取表字也不是闹着玩。这表字是何其重要,你可比我要清楚。”
“再说了,”秦熹揉着自己的后脑勺道,“这表字你不是早就取好了吗?”秦霄瞪了眼秦熹,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这个臭小子。若是打开秦霄扔在地上纸团的话,就会发现上面无一例外的都写着“微阳”二字。
“想好了?”秦霄不确定的问了一句,毕竟儿子已经长大了。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主了。秦熹笑着将秦霄面前已经写好的“微阳”拿了起来,对着灯火仔细观赏,笔力穷劲,苍劲峻逸,是幅不可多得的好字。语气何其认真道:“嗯,早就想清楚了。”
微阳。露气寒光集,微阳下楚丘。倒是个好名字,就是不知道这太阳微微日火是否能将这李唐江山给复燃。
————
待李鹤烨彻底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烧已经退,身上的伤也被上了药,衣服也被换过了。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手里竟然攥着一条蓝色的帕子,上面用紫线绣着并蒂莲。怪不得,自己会迷糊中抓住这条帕子,实在是和娘的那条太像了。
他记得很清楚怡亲王妃的那条手帕上绣着晶白如玉、金蕊送香的芙蓉。不过这到底是谁的帕子?
李鹤烨捋尽脑内所认识的人,但都一一否认了。阙都可没有怡亲王的旧部,即便是有人,他们也会避他李鹤烨的霉头。
直到李鹤烨想起踢他一脚的那人,福龙海那个贱婢叫他“顾二”。李鹤烨年龄也不小,其实也只比秦熹小一岁,大顾翼两岁罢了。
说他闭锁深院,但这天下之势他还是了解一二的。漠北位高权重这天下何人不知何人不晓?那漠北世子的名声更是极好的,世人多是赞誉。不过,既然有那种表弟的人,怎么想也都是个纨绔子弟,传言罢了,多有夸大的成分在。
他攥紧帕子,左右瞧了瞧,似是想找找能证明主人身份的东西,然而除了那并蒂莲,便再也没有其他的绣花。不过那帕子是香的,嗯…香料的气味。
至于是什么香料的气味,李鹤烨没有闻出来。这阙都自是与荆南不同,不像是官宦家女常用的香料。不过既然能进这刑监司,想来也不是什么昏庸无用之人。
并蒂莲并非是寻常女儿家最爱绣的,也有不少君子也偏爱莲花。李鹤烨突然一笑,这帕子的主人总不会是个爱好偏奇的姑娘吧?
李鹤烨小心翼翼的将帕子叠好,又仔仔细细的贴身放好,这可是他的救命恩人的东西,他可得小心的收好。或许将来能用这个搭条线,得个好姻缘呢。
此时牢门之外响起沉重的脚步声,非练武之人的脚步声可没有如此厚重。那人带着的纱帽厚的很,根本看不清容貌,他一开口便是极其沙哑的嗓音,让人一听就觉得是用了伪装。
“这就是怡亲王的次子?呵,命可当真是硬啊。葛川!”葛川时机卡的非常完美,不急不躁的从不良帅的身后走了出来,向他弯腰拱手道:“大人。”
“今日起你就专门负责怡亲王次子,待怡亲王“世子”殿下伤好之后,你们就搬去国昭寺吧。具体内容本帅就不说了,本帅多说“世子殿下”也不会相信,不急这一时儿,皇上的圣旨一会儿就到。”
不良帅负手而立,李鹤烨可以清楚的感觉到那纱帽之后,神情凛冽的眼神。这简直让人不寒而栗,葛川俯首称是。不良帅转身背手离开,脚步声越来越远。
就在不良帅走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福龙海就捧着圣旨来到了刑监司,尖锐的嗓音宣读着圣旨上的旨意。
大致意思就是念在李鹤烨年幼,念在怡亲王是太上皇的弟弟,对朝廷有功绩,皇恩浩荡,将他放到国昭寺,没有皇帝命令,不得私自外出,不得私见他人。
此时之景不难不让李鹤烨想到那天的场景,自己就如那天天麟帝手上的那条鱼,先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今又将要被困在国昭寺这寸方之地。宛如困兽,受人随意摆布。
可真当他李鹤烨是个善茬吗?他本为怡亲王的一位侍妾所生,是怡亲王妃收养了他,养在身边视若亲子。如今最爱他的那个女人已经离世,自己答应她要活下去。就一定会活下去!
————
秦铃提着灯笼轻步细语的来到书房外,看着房门大敞四开。里面的烛光很足,哥哥和父亲在桌案拿着一张纸有说有笑的。秦铃怔怔的站在外面,没有上前去打扰这温馨一幕的父子之情。
她与秦熹本是一母双胎的兄妹,都说世人最是不喜双生子的。尤其是她们这种官宦之家,作为较为瘦弱的那一个,秦铃非常庆幸自己是个女人。
只可惜幼年丧母,自小就没有母亲的疼爱。庆幸的是父亲和哥哥都是顶疼她的,可年纪大了总是有父亲和兄长不能照顾的地方。
她今年也要及笈,如果可以甚至明年就可以考量夫家。兄长束发代表了她们漠北新一任王的崛起,而自己呢?难道真的会沦落为政治的牺牲品吗?
想到这里秦铃内心不禁悲凉起来,她羡慕母亲纵马江湖与父亲的侠义初遇。更羡慕哥哥能够上战场手刃外敌,自己自幼学武也不过是些自保功夫。
唯一拿的出手的就是这响尾鞭,如何与真才实学的兄长相比?秦铃抿了抿嘴,自己的名声在这些阙都贵女中向来是不好的,她也不愿嫁给一个阙都纨绔为妻。
实在万不得已,那她就下嫁给一位漠北的将军为妻。她不想离开漠北、离开父兄,她要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漠北、守护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