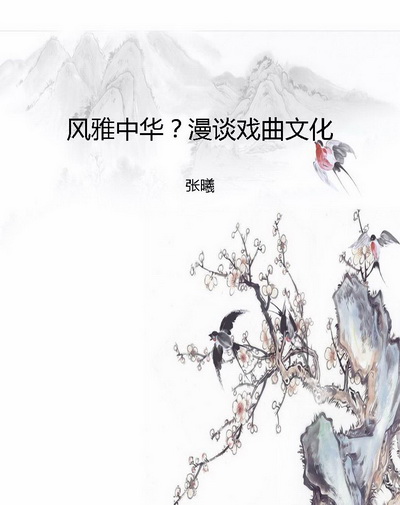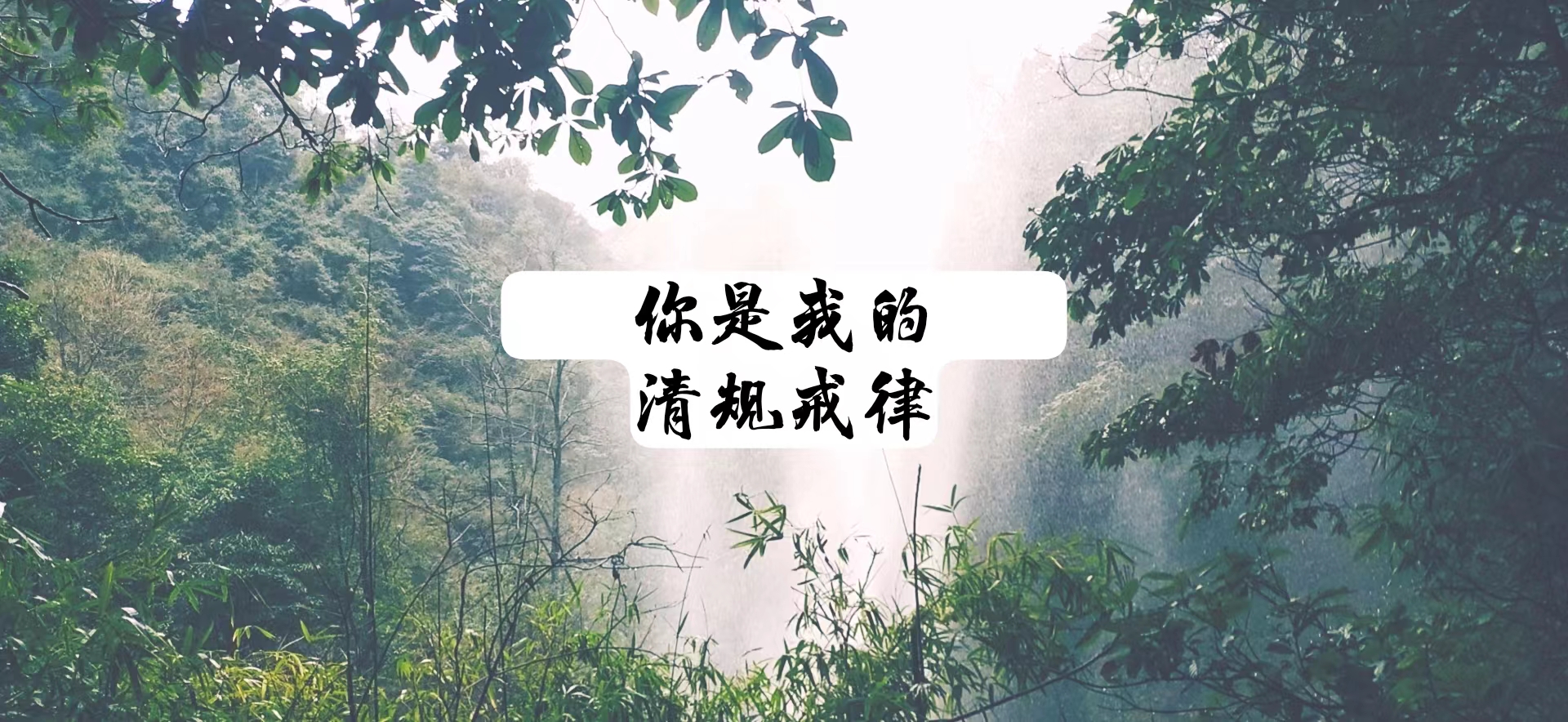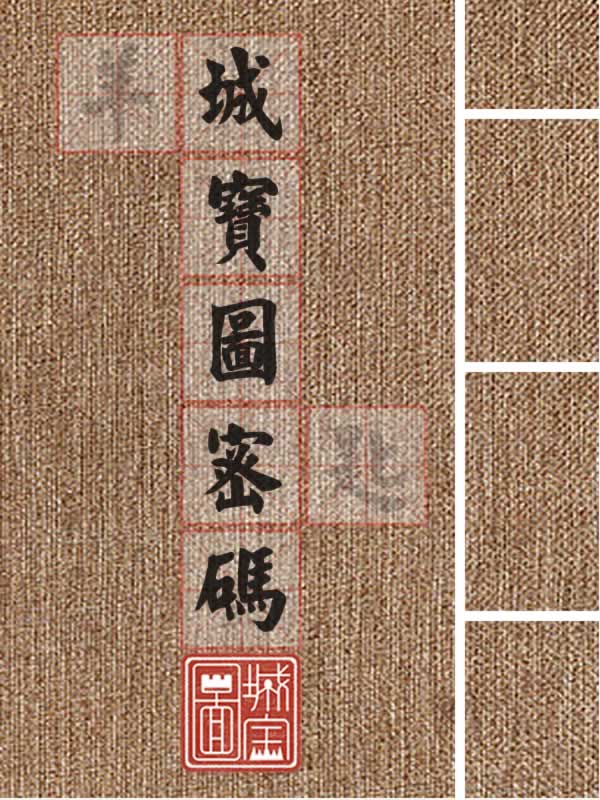黄道十二宫又称十二星座,即金牛座、白羊座、天称座等(图7-9)。是西方对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圆圈路线即黄道及其附近恒星所划分的十二个区域。十二宫与十二星座虽然都叫金牛座等相同的名称,但意义不同:十二星座是对黄道上的恒星所作的分区,由于恒星数目、排列方式不同,各星座范围广狭不一;而对黄道的分区则是均等的,每宫30°。为什么要称为十二宫呢?因为在西方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是天神,它住的地方按理当然应该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因而每年十二个月它在黄道上巡行时停留的十二个地方即称为十二宫。
首先提出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十二辰次有相似之处、两者在起源上存在联系并进行论证的是郭沫若。
摄提格、阐阏、大荒落、等是人们在太岁纪年法中新创造出的十二个用以纪年的被称为岁名的符号,人们后来又创造了屠维、重光、昭阳等被称为岁阳的十个符号,岁阳与岁名分别与天干、地支相对应,而且可以象干支那样搭配成六十对以纪年——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全国开始正式通用干支纪年法。
郭沫若正是从岁名摄提格开始入手探求十二宫与十二辰次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两者相似且后者源出于前者的结论的。
《史记·天官书》说:“大角者,天王帝庭,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摄提,摄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时节,曰摄提格”。这就是说大角星别名摄提格,而在太岁纪年法中太岁在寅时,岁名也为“摄提格”。因此,郭沫若认为:“西方之十二宫采用少女,少女当中国二十八宿之角;而中国之十二辰采用大角……古人用之以代替少女之角”(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62,第一版,239页)。
稍后,郭沫若又说:
“既知寅为大角,与西方十二宫之少女相当,以此为基准,以十二辰逆转之顺序以安配之,则当如下表
就此表以考核有可惊异者数事。
一、阐阏与轩辕音之一致……是则轩辕乃阐阏之音转。而卯之骨文作□若□,与希腊狮子座之符号□绝相类似。
二、巳之初文作‘子’,罗氏以为‘此疑终不明’者,而此当希腊之双子。
三、未本为穗,而所当之娄胃,《天官书》云‘娄为聚众,胃为天仓’。
四、申字作□若□,象以一线连接二物之形,而此当于双鱼,与□之符号同意。
五、酉象壶尊之形,而此当于水瓶。
六、房心尾即蝎形之分化:古人室有左右二房,房喻蝎之二螯,心即蝎之心,尾即蝎之尾。是中国本有蝎星,于制定二十八宿时始由一化为三。《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三星合而为一,即其证。
七、亢氐亦天秤之分化,亢者抗也,氐者底也。《尔雅》‘天根底也’即是底义。与底上有物抗举,斯为天秤矣。古中国古本有天秤,于制定二十八宿之时始由一化为二。
有此七事连摄提格之为大角,十二辰有八辰似已可用星象说明矣……”
将郭沫若所列的表与前面尧典中的第四幅星图也即仲冬之月的星图(图7-2)相对比,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
郭沫若还认为,十二宫在公元前“四四〇〇年至二二〇〇年之间”即已出现,并列出了叶列妙士所译的公元前二一〇〇年的一项文献记录上的有关月缠上十七星的内容来说明:
一、昴;
二、毕;
三、参;
四、培尔脩士(天船);
五、大双子(东井);
六、天五潢;
七、蟹(舆鬼);
八、狮子(轩辕);
九、少女(角)(愿意为禾);
十、天秤(亢氐);
十一、蝎(大辰房心尾);
十二、射手(箕斗);十三、山羊(牛);
十四、水瓶(女虚);
十五、南鱼与北鱼之尾(南鱼之尾为奎,北鱼在营室东壁下,双鱼全长略等于室壁奎三宿);
十六、白羊(娄胃)。
郭沫若解释说:“此始于昴毕(即金牛),叶列妙士以为此必春分点在金牛宫时所制定。其年代即当在公元前四四〇〇年与二二〇〇年之间。叶氏又谓十七之数为天数中所绝无,故此中已含有十二宫之根蒂,盖天五潢本属于巴比伦双子星之西部,而培尔脩士本属于牡牛。”(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科学出版社,1962,第一版,245页)
郭沫若接着又列举了于亚马尔那时代赫提特王国首都波华池奎野发现的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代的一项纪录中的星表,此星表中含有黄道之星宿十个,也大致与巴比伦之十二宫相当。然后,郭沫若说:“此外尚有若干较晚之古物与文书之证明,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之说已成为学界上之定论。”
在肯定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的基础上,郭沫若后面将中国的十二辰次与巴比伦之十二宫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除过前面所列的七点相似一点相同之外,他还认为:“摄提格”等12个岁名为外来词,其发音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语或亚加德语的12个星座的发音;子、丑等十二辰各个字形的结构都与巴比伦黄道十二星座有密切关系,甚至有的字形直接就是对相对应星座形象的模拟。最后,郭沫若得出结:“古十二辰实即黄道周天之十二恒星,而此十二恒星则与巴比伦之十二宫颇相一致”;“十二辰始于子(干支表均始甲子可证),此与巴比伦十二宫之始于牡牛者相同,盖其制定时期乃春分点在牡牛、秋分点在蝎座时也。其年代约当公元前四四〇〇年至二二〇〇年。故十二辰之输入或得其暗示而另行制定者,至迟当在公元前二二00年前。此时代虽甚古远,然盘庚迁殷至纣灭已有‘七百七十三年’,可知殷代之开幕至迟当在公元前二千五六百年代也。”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十二辰就是巴比伦之十二宫,是它的翻版货或得其暗示而另行制定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上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十二辰大约是6500年前在中国独立产生的,其产生与巴比伦之十二宫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可能却是存在的,即巴比伦之十二宫的产生受到过中国十二辰及与之相对应的十二次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十二辰及帝尧时代仲冬时节与十二辰相应的十二次与巴比伦之十二宫之间确实有一些惊人的相同与相似之处——郭沫若提出的七点相似一点相同中有一些就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这些相似都只有从巴比伦十二宫受中国十二辰及与之相对应的十二次影响而形成的角度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首先,太岁纪年中太岁居于寅辰之年岁名为摄提格,而摄提原本是大角星两旁的两组小星的名字,此处大角是用来代替角宿,而角宿又相当于西方黄道十二宫中的少女座。这一条相同点显然是的确存在的。
第二,我们来看“酉象壶尊之形,而此当于水瓶”这一条。郭沫若在将中国的十二辰与巴比伦之十二宫进行仔细比较时说:“巴之‘水瓶’为Gula(华言为‘巨人’),其星象作一人捧瓶倾水之形。”中国十二辰中的酉为尖底瓶的象形,而相应的巴比伦的水瓶座也被想象为一人捧瓶倾水之形,都是瓶子,这真是惊人地相似!当然,如果只有这一个相似点,完全可以解释为巧合,但问题是下面还有一些相似,如果都用巧合来解释就说不通了。
第三,我们再来看郭沫若所列七点相似中的第四点“申字作□若□,象以一线连接二物之形,而此当于双鱼,与□之符号同意”。不但双鱼座的希腊符号与申的甲骨文字形同意,都有一线连接二物之意,而且双鱼座的巴比伦星象也为双鱼形象。
第四,郭沫若所列七点相似中的第一点说:“阐阏与轩辕音之一致……是则轩辕乃阐阏之音转。而卯之骨文作□若□,与希腊狮子座之符号□绝相类似。”
认为“轩辕乃阐阏之音转”,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郭沫若认为“摄提格”等12个岁名其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语或亚加德语(阿卡德语)的12个星座的发音这种观点总的来说都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吴宇虹在《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中说得很有清楚:“郭老大胆地推测汉代出现的与12辰对应的木星轨道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为外来词,其发音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文作‘酥美’)语或阿卡德语(‘亚加德’)的12个星座的发音。然而,从公元前1800年起,苏美尔语已成为死亡语言,所有的苏美尔词符都被读成阿卡德语(如日文中的汉字被读成日语而不是汉语),他使用的苏美尔星名符号(一些符号读音有多个)可能已经被当地人读成阿卡德语星名。因此,他用的苏美尔星名对应中国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的方法很不可靠。实际上,他在文中给出的中文12岁名和楔文(多为苏美尔语)12星名对照读音、以及《尔雅》中12月名对应苏美尔12个月名的对照读音十分勉强或相差甚远,这些读音很难成为他所谓的这些中文岁名和月名术语来自两河流域文明的证据。”(《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不过,这一条中关于卯的甲骨文字形与希腊狮子座之符号类似的观点则是正确的。卯之骨文作□若□这是有其自身原因的,就是出于对有耳尖底瓶两耳的模拟,而希腊狮子座之符号□与此“绝相类似”则说明希腊狮子座之符号有可能是受卯的甲骨文字形影响而产生的。
第五,郭沫若所列七点相似中的第二点说:“巳之初文作‘子’,罗氏以为‘此疑终不明’者,而此当希腊之双子。”郭沫若还在后面说:“然可注意者则《波表》(即波华池奎野发现的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代的一项纪录中的星表)中以参星代替双子。公元前五百年代抄录之‘TE简’(华言为‘星’)原文当系前一千二百年代之物,其当于双子之处亦参星与大双子并举。此点与中国古十二辰用参星而不用东井之事实相同。”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有与巳、参星相联系的双子传说(上一节已提到过),而恰巧在巴比伦也有与相对应的星宿相联系的双子传说。都有与一定星宿相联系的双子传说,那么究竟是谁模仿谁的呢?中国的双子传说与一定的历史人物相联系,因而极有可能讲的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巴比伦的双子传说则纯粹是一种神话传说,神话可以随便编造,事实却是不需要也不能编造的,因而巴比伦的双子传说显然是受中国影像而产生的。况且,王宁说“郭沫若云:‘(巴比伦之)双子均西向,视为Nabu与Marduk二神之显示。此二神乃兄弟神,于位置上每相对立,如在四陆之中Marduk立于东极而司春,Nabu立于西极而司秋,正合于我国的参与商之位。’则巴比伦曾有Marduk为参星神之说,Marduk即马尔杜克,乃巴比伦的主神,在诸神中地位最为崇高……但是马尔杜克为主神之事大约是在公元前19-公元前16世纪左右,似乎要后于我国的夏代,而且似乎仅见于此,别无佐证。”(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释支干〉研究之二》,《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这就更说明了巴比伦的双子传说产生较晚,是后起的。
郭沫若所列七点相似中剩余三点则是不正确的:关于中国本有天秤座后于制定二十八宿时始才分化出氐亢两宿、中国本有蝎座后于制定二十八宿时始才分化出房心尾,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二十八宿在7000多年前已产生,氐、亢、房、心、尾几宿原本都是存在的,它们完全都可以从代表龙身体一部分的角度加以解释;关于未为穗的观点也是不对的,未的本义不是穗,未字字形的来历我们前面已说过了,它只是以自身特点表示它代表的是倾斜方向的位置而已。
另外,郭沫若还提到中国与巴比伦都有与箕、斗星宿相联系的“二首六身”的说法。
亥字除用为十二辰外还是殷人一位先祖的名字,即《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为有易所杀之王亥。“王亥的事迹古书多有记载,他作服牛,宾于有易放牧牛羊,有易人为了夺他的牛羊杀了他,把他肢解,剁成数块,《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王子夜(亥)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这是说王子亥的两手、两腿、胸都被分离,头被从中间横着斩断,上部为首,下部为齿,符合《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说‘亥有二首六身的说法’,二首即首、齿分为二,六身即头、胸、两手和两股也。”(王宁:《申论“契即王亥”——〈释支干〉研究之一》,《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
十二地支中的亥当于十二宫的射手座。郭沫若说:“巴之射手座每与邻近之蝎座相并,其星象每不一定,然其最可注意者有Meli-sipak所出土的界碑(约当公元前一二00年代之物),上有射手像最为奇特,今摩录如次:
此像二首,一人一犬;身则上体为人,下体为马,而有鸟翼、犬阴、牛尾、蝎尾。二者合计,也恰当于‘二首六身’”。
郭沫若的意思是,中国关于“亥有二首六身的说法”源于巴比伦对于射手座星象的构想。王宁更直接说:“笔者的看法是,王亥是殷人历史上的一位很杰出的王……因为殷人的星历知识是自古巴比伦输入,他们的星象里也是射手与天蝎相拼合的,所以就用天蝎座之神的表征物书写用的刻刀‘亥’来作为他的名字,并说他有‘二首六身’,因为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奇怪,为了解释,古人又结合王亥被杀的事实,创造了他被杀后被砍成“二首六身”之惨状的说法。”(王宁:《申论“契即王亥”——〈释支干〉研究之一》,《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
中国关于“亥有二首六身的说法”真的是源于巴比伦对于射手座星象的构想吗?我们以为事实可能正相反。因为,说“亥有二首六身”这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巴比伦射手座被构想成“二首六身”却完全可以是随意设想的。
由于以上共六点相似一点相同的存在——王宁在《十二辰与巴比伦相关星座对照研究——〈释支干〉研究之五》(《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1期)中还列举了更多的相似,我们可以肯定巴比伦十二宫在其形成之初是受到过中国十二辰次影响的,十二宫的最初形成当然也就不会早于中国十二次形成的下限,即公元前2494年——这与郭沫若推测的十二宫的最初形成时间在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2200年之间并不矛盾。
郭沫若之所以得出中国的十二辰次源于西方黄道十二宫的错误结论,主要是他有两个错误前提:第一,先入为主的想当然以为中国的十二地支产生时间晚于西方黄道十二宫;第二,错误地认为,十二辰次体系原本是与黄道附近的恒星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后来十二辰才单独脱离了天体而固定下来,而十二地支之所以是现在那样的顺序则是因为,作为十二辰次代表符号的十二地支挪作文字时由于某种原因不幸发生了逆转。这两个前提其实都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错误的前提导致错误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
虽然巴比伦十二宫从其源头上说是出自于中国的十二次,但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十二宫从其最初开始形成到完整的十二宫的出现这中间实际上又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因为十二宫毕竟不是十二次的直接翻版,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的。
关于完整的十二宫出现前的一些情况,吴宇虹说:
“公元前1千纪初,巴比伦学者已经对星空有了比较科学的掌握和研究。他们把天空划分三个天道,把每个天道中的12标志星和12个月搭配以校正每年12个月的开始日、5日、10日、15日或25日的准确时间。1900年,亚述学者品克斯(Pinches)首次发现这种12个星座和12个月份的组合方式被记录在几块注释天象学系列泥板《当天神和恩利勒神…》和天象占卜的泥板文书中,他把整理后的每月之星文件命名为《星盘》(Astrolabes)。后来又发现了早于《品克斯的星盘》(Pinches Astrolabe,写于公元前720年左右)的把星体和12个月关联的天文学文件《星盘乙本》(Astrolabe B,写于巴比伦王Ninurta-apil-Ekur统治期:公元前1190-1178)。这些星盘文献把天空划分为三个天道,每个天道在每个月都有一个标志星在空中升起。星盘文献按1到12月的次序,以‘三星于一月’的分组,给出了的每月的三个天道的星,形成12个三星一组,共36个星的组合(见下表)。这样太阳的周期被设定为360°圆周,每月的星座被理想地定为占30°(实际上各有差别),代表30天,形成天道12星座代表一年12个月的占星和天文理论。由于星盘中的各星时空位置可能是部分根据神话、部分根据天文学知识,每月的标志星的出现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一些星座所属天道和它们在天文学文献《犁星》中的天道不一致。但是,这种把天空划为分区、以12月为时间标志、以12个星座为空间(天区)标志的观察方法被希腊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现代还在使用的星象学和天文学的黄道12宫(到现代都产生了位移)。”(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可见,虽然公元前1190-1178年巴比伦人已明确形成了“天道12星座代表一年12个月的占星和天文理论”,但真正的黄道12宫的出现似乎也还要晚一些。这从江晓原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他说:“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本意是‘兽带’
(zodiac,这可能是较为后出的名称)。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出现了。在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即MULAPIN,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吴宇虹将其翻译为《犁星》——本书作者注)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列的星座那时有18个(即郭沫若所引用的“月缠上十七星”——本书作者注)……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们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前3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已用于埃及;然而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江晓原:《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