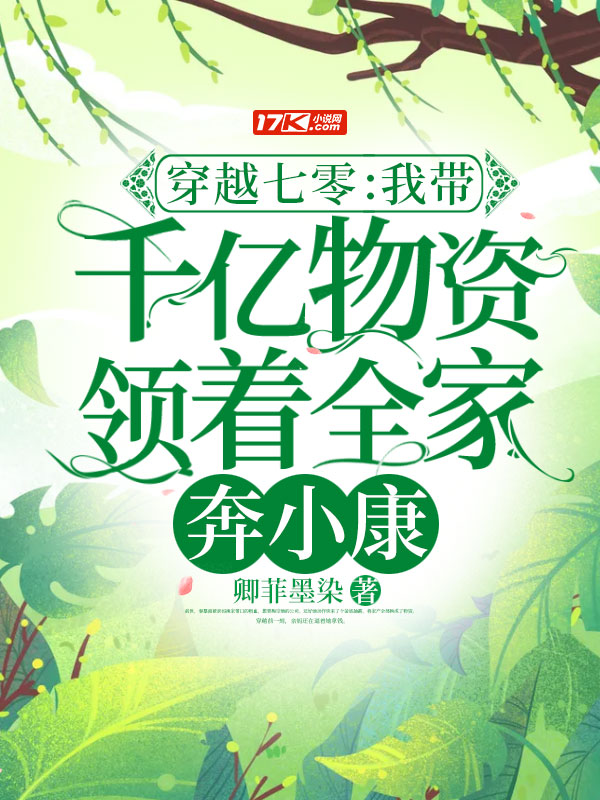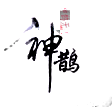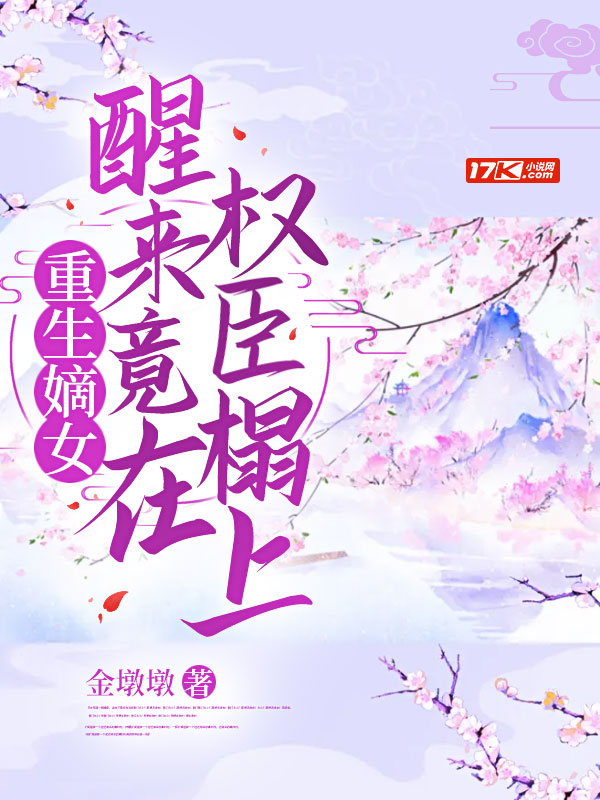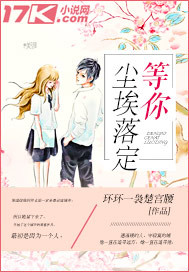十二地支产生的大体时间既已清楚,那么十天干产生于什么时间,十天干的产生是在早于还是晚于十二地支的产生呢?
郭沫若认为天干是商人所创造的,他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说:“《山海经》又云:‘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南经》)。王国维云帝俊即帝喾。帝喾为殷人所自出,则十日传说必为殷人所创生而以之属于其祖者矣。十日旬制既始于殷人,则以日为名号之事,亦当始于殷人。始于殷之何人虽不可得而知,所得而知者,则殷以前不应有以日为名之事。古史中载夏有孔甲、履癸,果有其人,则‘甲’、‘癸’之义,要亦不过鱼鳞、第一与三锋矛之类耳。”(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科学出版社,1962,第一版,188页)针对郭沫若的这种认识,王宁在《〈释支干〉辨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中反驳说:“此说未确……夏人自启始凡十六王,今可知即有六王以天干为名,几乎占了一半,恐非偶然。笔者认为夏人之王必亦如殷人之王,有私名,有庙号,而后人为不使与殷王之庙号相淆混,乃去其庙号而专用其私名,此由将夏王之大庚、中庚、少庚之庚改为康即可明白,此六王之庙号乃幸存者。故以十日为名乃自夏代有之,则十日之创作恐亦非殷人之专擅。”王宁这种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夏代帝王名号中天干的存在说明天干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夏代。
天干产生的时间是否还能继续往上追溯?仍然是可以的。
由于十二地支符号的制定原则与十天干的一致,两者都是一次性制定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具有紧密联系的十二地支中的“戌”与十天干中的“戊”字入手来探求十二地支与十天干产生的先后顺序。
前面我们说过,十二地支中的“戌”字是在十天干中的“戊”字基础上增加一个部件形成的,就是说先有“戊”字后有“戌”字,那么实际情况有没有可能正好相反,是先有“戌”字后有“戊”字,“戊”字是由“戌”字减掉一个部件变化而来的呢?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存在的。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在简单的字形基础上通过增加笔画形成新的字是顺理成章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如果反过来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字的基础上通过减少笔画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字就不大合情理了,造字的人会想既然减少笔画能形成一个新的字,说明原来的字是过于难写了,完全可以用新的字形代替旧的字形,至于所需要的新字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可以从完全新的角度去考虑创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两个外形上非常接近的字了。具体到“戊”字和“戌”这两字来说,不仅前者简单后者复杂,先有前者后有后者合乎情理,而且前者代表的位置在上面,后者代表的位置在下面,在前者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在其中下部添一笔形成后者表示下方很合理,相反,如果先有代表下方的“戌”后有“戊”,则难以说新形成的“戊”就一定代表上方——它只是去掉了中下部的一横,不代表下方而已。另外,“戊”字由5个笔画组成,这也符合十天干前面的几个字其主要笔画数与各自对应的序数一致的原则,很像是在没有任何相似字做依托的情况下凭空临时构思而成的——当然,如果说先有“戌”字,将其笔画减少一笔很也能形成一个符合要求的字,但“戌”字怎么偏偏正好是6笔,这不也太巧合了吗?总之,认为先有“戊”字后有“戌”字是自然合理的,相反认为先有“戌”字后有“戊”字则不合逻辑。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实际情况必定是先有“戊”字后有“戌”字,从而,我们可以断定整个十二地支都是在十天干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形成的,十天干的形成早于十二地支。
就是说,根据戌字、戊字相似及事情又总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可以断定戌字应当是在戊字基础上形成的,十二地支产生于十天干形成之后。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十天干、十二地支分别成为十母与十二子,这也说明了应该是先有十天干后有十二地支。而天干、地支这种称呼本身也说明了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基础,前者的产生早于后者。
天干的产生比地支能早多少呢?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上的纹饰符号表明仰韶文化前期形成十天干的条件都已具备,而且可以据此猜想,这些条件可能远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十天干可能在仰韶文化时期之前已产生。
那么,十天干的起源究竟可以进一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之前什么时候呢?
夏商时期人们对参宿、大火星非常重视,分别用它们做观测主星,说明人们应该远在此之前很早就已经先后它们用做过观测主星了,其年代应该是参宿恰位于春分点附近、大火星恰位于秋分点附近的时候。
十天干所代表的历法既然是一种星辰历,那它就应该是以参宿或大火星为观测主星的历法;另一方面,仰韶文化之前这两个观察主星中又只有参宿能位于春分点附近,大火星距离秋分点则还比较远。因此,可以断定,十天干所代表的历法就是以参宿为观测主星的历法,其具体产生时间应是春分时节黎明时分恰好可以在东方地平线上看到参宿的年代或稍早一些时候。
天文学上有一种现象,叫作岁差。其原因是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地球自转轴方向会发生轻微变化,从而春分点(春分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冬至点等都会逐年西移——大约71.6年西移1°,此即岁差。正是因为岁差现象的存在,回归年即地球过冬至点后绕日一周再复过冬至点所需时间365.2422天才比恒星年短一些。参宿的组成恒星之一、位于参宿最东边的参宿四现在的赤经值为88.79°,也就是说现在参宿四在春分点东面的88.79°,根据岁差推算,则春分点位于参宿四的年代约距今约6357年,而春分时节黎明时分恰好可以在东方地平线上看到完整参宿的年代则还需向前推至少1289年(即春分点距参宿四18°的年代,彼时春分时节黎明时天文晨光开始时最后能看到天上所有星星时参宿恰位于东方地平线上),即约公元前5646年前。
这样,十天干所代表的历法的产生时间,也即十天干的真正起源时间,也就应该不晚于公元前5646年前。
从实际情况看,构成参宿的七颗星都是二等以上的亮星,在黄河流域的天空中很醒目,当时它又位于春分点附近,在春分日前后黎明时分正好位于东方地平线上,所以古人在那个时候注意到它并将它作为观测主星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古人对春分的认识,显然是来自于立杆测影的活动。立杆测影很简单,古人在公元前5646年前完全有可能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而且不仅根据这个方法测出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还会以此为基础测出回归年的比较精确的长度。
这里需要深入讨论一下的是,7000多年前的古人对回归年长度的测定究竟能精确到什么程度。
7000多年前的古人是否已经知道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365天多一点?
我们认为古人知道这一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郑文光曾说过:“最早测定回归年长度的方法之一,是用土圭测定每天午时的日影长度,由日影最长的一天到下一个日影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日,古称日南至),或由日影最的短一天到下一个日影最短的一天(就是夏至),正是一个回归年。但是这样的测日影法十分不准确,因为在冬至前后和夏至前后,日影长度变化甚微,回归年长度的误差可达数天之多……”(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第一版,102页)这就是说,若以冬至或夏至为年首、为起算点来直接测定回归年的长度,误差会比较大。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以冬至或夏至为年首、为起算点呢?为什么不以日影变化明显的春分或秋分前后任意一天为年首、为起算点呢?(只要那一天天气睛好,日影可以清楚标记就可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元前5646年前的古人应该是能够测定出回归年的长度是365天多一点的。
公元前5646年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地湾文化早期。大地湾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关中及丹江上游地区,存在于约8000年前至7000前年,与仰韶文化具有延袭承传的密切关系。大地湾文化遗址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出土有骨耒、磨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那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历法,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因而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公元前5646年前在我国产生最早的历法也是完全可能的。
江小原在其所著《天学真原》一书中曾对“天文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论断提出质疑,他说:“中国的农业生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准,那时当然不存在历法”(江小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一版,143页)。现在看来他的质疑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他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主要目的都是为帝王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情况,应该都是在华夏民族建立国家并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可以肯定,中国从上古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天文学不但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在民间亦具有极高的普及率。
说十天干所代表的、以参星观测主星的星辰历产生于公元前5646年前,不但是因为做出这样一个假说非常自然,更是由于有下面的有力证据:公元前5670年前后不但产生了二十八宿,并且参宿还同时受到了特别的对待。
二十八宿是赤道、黄道附近的恒星划分成的二十八个群。二十八宿不仅中国有,印度、埃及、阿拉伯、伊朗等国也都有。由于不同国家的二十八宿显然是同源的,因而二十八宿最初起源哪里就显得很重要,二百年来中外学者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目前已有的有关证据,可以肯定二十八宿最初的发源地就是中国[1]。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李勇在《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0卷 第1期)一文中又使用天文计算的方法,根据当前国际天文界使用的最新的岁差模型,研究认定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5670年前后:那个时期二十八宿相对成偶(即两两相对成偶,相隔半个周天180°)的宿数最多;那个时期二十八宿与赤道、黄道相合的宿数最多,达到18宿;那个时期二十八宿间的距离基本上也是相等的,符合一天一宿的意义和标准的月舍宿数最多,达到24宿(图5-9)。
根据二十八宿的特点与作用,我们认为,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中国古人应该有过一次制定历法的活动高潮:
要制定能精确预计时间、季节变化的历法,就要寻找一种合适长度的周期作为“月”。
首先被考虑用作月的应该是朔望月。朔望月周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周期,月相的变化很直观明了,因而对它的长度的大致测算也不会太难,因而,古人应该首先对它进行了的测算。当然,由于发现朔望月周期数值不是整日数并且一个回归年中不包含整数个朔望月因而并不方便应用,而如果以塑望月周期为月的长度,以回归年周期为年的平均长度,编制阴阳历,则不但首先要测得回归年的精确数值和塑望月的准确数值,然后还要通过计算或者长期的观察找到一种能够很好协调两者的恰当地置润规则,而这些任务对于7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说是很难一下子完成的,于是他们便暂时放弃了将这个周期用作月的想法。至于后来什么时候中国古人开始研究精确的闰周规则问题并发现了十九年七闰规则、创造了八卦体系、制订了十九年闰周的阴阳历,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月亮不但会发生阴晴圆缺变化它在天空的位置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古人就会去探求月亮旋转一周天的周期的长度也就是恒星月的长度,看能否将这种周期用作月。结果,发现恒星月的长度是27天多,也不适于用作月的长度——但为了使人们记住恒星月的长度是27天多一点却特意创造出了二十八宿以记录、说明这种规律,因而,可以说,二十八宿是古人这次制定历法活动的副产品和遗留物,它正体现了古人在创造历法方面的努力。
在发现朔望月周期、恒星月周期都不适宜用作历法的月后,古人自然就会想到人为地确定一个时间长度用作“月”来创造出一种历法。
这种最早的历法应该就是十天干所代表的十月星辰历。因为,十天干所代表的十月星辰历所具有的特点正是这种历法所应具有的特点:十天干所代表的十月星辰历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历法,而二十八宿产生时中国古人创造出的历法也正是中国古人创造的最早的历法;夏商时期人们对参宿、大火星非常重视,说明人们应该很早就已经认识、使用过参宿、大火星了,十天干所代表的十月星辰历作为最早的历法也就应该而且能够以参宿为观测主星,而二十八宿产生时中国古人创造出的历法恰好也就正可以以参宿为观测主星(参宿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时正好为春分时节)。
关于十天干所代表的十月星辰历的产生过程,大致可分为月的长度的确定与十天干的产生两个步骤。
首先是要月的长度的确定。由于朔望月周期、恒星月周期两者都不是整数,也都不能整除回归年长度,都不适宜作为月的长度单位,于是人们必然要自然人为地确定一个时间长度来用作“月”——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即一年中设多少个月。因为一年中月的个数确定后,月的长度自然也就确定了。人手有十指且可以用于记数,因而古人应该早在此之前就有了“十”的概念,于是在最开始创造历法而又没有适当的自然天文周期可以作为月时古人也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将一年确定为十个月,将每个月定为36天(剩余5天作为过年日使用)。
接下来是十天干系统的制定。古人注意到了参宿在春分日前后黎明前正好位于东方地平线上,当然也就会注意到随着时间、日影的长短变化参宿黎明时在天空的位置也会自东往西周期性的发生变化。一年时间既然已经划分为十个月,则就可以同时将参宿周年视运动路径相应的也划分为十段(实际首先是将与其相平行的天赤道划分为十段,天赤道划分为十段则参宿周年视运动路径也就自然划分为了十段),一段对应一个月,时间上的起点定为春分日,空间上的起点(也就是天赤道、参宿周年视运动路径的起点)则定为春分日前后黎明时参宿所处的正东方,这样,十天干就产生了。
十天产生后,年的时间变化也就可以直观地通过参宿在天空的位置变化表现出来,同时月份也可以用十天干来标记。于是,一种以参宿为观察标准星的以十天干来纪月的十月星辰历就也在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的中国诞生了——实际上,何新在1986年出版的《诸神的起源》一书中就做出过十天干最早可能是用来纪月的推测,认为我国远古时代可能存在过以十天干来纪月的十月历法。何新的推测与本书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
不但二十八宿的产生揭示了公元前5670年前后古人创造过以十天干来纪月的十月历法,二十八宿本身对参宿、觜宿的特别关注也提示了以参宿为观察标准星的以十天干来纪月的十月星辰历在那时的产生。
二十八宿产生时绝大部分的星宿不是在天赤道上就是在黄道上或在它们的附近,只有参、觜两宿很特殊,它们既不在赤道上也不在黄道上而是“远远偏离赤道和黄道,似乎与其它二十六宿不属一个体系中”(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0卷第1期),但却都被意外地选进了二十八宿。这就说明公元前5670年前后的人们的确已经注意到了当时的参宿非常特别——春分日黎明时分恰好处于东方地平向上,是春分的独特天象,于是对它特别重视,已经或者正准备让其扮演重要角色——用其在天空位置的移动来划分、标记月份形成一种星辰历,同时在制定二十八宿时也特意将其纳入了其中。而之所以将不太显眼的、位置几乎与参宿重叠的觜宿也同时放进去作为二十八宿之一却也是大有深意的:由于一个恒星月长度约为27天多一点,在27天还有个零头,于是就用几乎与参宿重叠的觜宿来表示那个零头。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是由古埃及人制定的(起算年代有公元前4241年、公元前4236年、公元前2781年、公元前1881年四种说法)。古代埃及人注意到天狼星第一次和太阳同时升起的那一天后再过五六十天尼罗河就开始泛滥,于是,古代埃及人就把那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并按尼罗河水的涨落和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把一年分为三季(泛滥季、耕种季、收获季),每季分为4个月,一年共12个月,每月30天,岁末增加5天节日,共计365日。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就是后来的罗马人根据古埃及人的这种太阳历制订出来的。
现在看来,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并不是由古埃及人制定的太阳历,而应当是我们祖先在公前5670年前后所创造的作为一种特殊太阳历的十月参历(以参星偕日升为每年开始)。因此,中国才应当算是远古时期世界上在天文历法方面成就最为辉煌的国家。
[1]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版;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