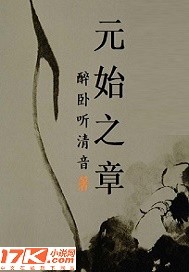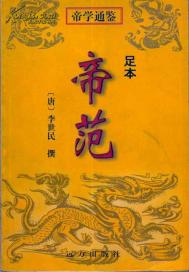二
此时的乡下与孩提时的印象大相径庭,尤其是村后的那条小河,它是我童年的小河。只见孤寂的小河干涸了许多,两岸只剩几棵稀疏的杨柳,几间新建的民房掺杂其间,成群的鸭鹅闹浑了浅浅的河水。我不敢相信童年,不敢相信这水托起过我的童年时光,记得那时,小河很长很美,河水很清很纯。
我无法忘记,小河伴过我的童年,我是顺着那哗啦啦的河流长大的。曾经,
岸柳低垂,碧波荡漾,笔直通向无垠的田畴,蓝天绿水之间,这条小河宛如一条裙带,系着一路的欢声笑语与瓜果飘香,那是我记忆中童年的小河。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雨下得总是那么大,淅淅沥沥,飘飘洒洒,布满天空,笼罩大地,回荡于天地之间。极目远望,茫茫一片,无边无际。
每当这时,我心里都喜滋滋的,我喜欢下雨,在下雨天玩耍,便是我童年的乐趣。雨哗啦啦泼下来了,我和伙伴们一个个像泥鳅般跑出屋外,顺着小道奔跑,雨水顺着小道滚滚地流淌着,汇集在小河之中,那哗哗声显得特别悦耳。
我的童年有着父亲的相伴,他曾多次背着我,沿着这条小河讲过好多故事,我经常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道进入梦乡,醒来时张口迎来母亲的第一勺鸡蛋羹。童年是无忧和纯净的,它也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快快长大,脱离父母的羁绊;外面的人渴望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躲避雪雨风霜。唉,回不去的念想,总让人在时光流淌中不时地想念。
儿时的伙伴大多都离家打工去了,留在乡下的所剩无几,偶尔遇见一二个,却又显得拘谨和陌生,无话可聊,彼此的寒暄是格式化的,吃饭了吗?嗯。干啥去?下地干活。回到乡下,我也是孤独的,乡下的幼时伙伴把我当成县城里的孩子,而县城里的同学把我看成是农村来的孩子,我犹如站在禾场的草垛上,上不沾天下不落地,是一种郎不郎秀不秀的角色。
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母亲把我的回乡当作一种荣光,这既炫耀着大哥大嫂的仁义与大度,把我抚养成人了,也觉着我在县城生活成长,白白净净的,举止言谈与众不同,身上有了城市的味道。于是她总护着我,不让我参与任何农活和家务事,生怕我再迷恋上了农村的泥土气息,我也无所事事,甩手安心闲玩,时间一长,二哥对我两手不沾阳春水的行为有了看法。
二哥两次高中复读,最后一次仅差两分而落榜,平时学习成绩比他差很多的生产大队书记的儿子却榜上有名。就当时来说,没有试卷查分的概念,家里也没那背景和能力,从此他与同学的命运天壤之别。
自我去县城跟随大哥大嫂读书后,二哥在家一心一意务农,他把扎根农村“修地球”认作了自己的宿命。见我“学败归来”,已是大龄青年的二哥便迫切希望我与之同步,向他学习务农知识,共同建设农村家园,这样他结婚成家以后就不用担心我的生计问题了,但我一直不表态也没有行动,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一天,他把铁锹箢箕摔在了我的脚下,勒令我出工干活,母亲由此与二哥爆发了冲突,结果是母亲揍了他一棍子,二哥踹了我一脚,而我跑去父亲坟前坐到了半夜。现在想来,沉浸于伤心难过的时候,胆子也够大的,后面直到母亲打着手电筒寻到我并把我拽回家。
深夜,母亲给我做了一碗汤面,她仔细地端详着我,捋捋我头上沾着的杂草,拍了拍我膝盖上的泥土,说:“幺儿啊,娘知道你不甘心回农村种地,你这样子也不是这块料,我琢磨好了,等你玩一阵儿,我带你去集市上的周家学裁缝,干干净净的,风不吹雨不淋,以后有个手艺不是,到哪儿都有饭吃,听话啊。”
母亲的一番话,让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肩膀上搭着软尺,一手画粉一手剪刀的模样。想起那抻着布料、穿针引线、比长量短,日复一日的单调和重复动作,还有不断吵闹在耳旁的 “哒哒哒” 缝纫机声,瞬间,我感到这一切模糊了我将来的岁月。
看着母亲已布满皱纹的脸庞和头上挂满的丝丝银发,我无话可说,挑起面条和着簌簌而下的泪水一并咽下。
我的第一次机遇是大哥大嫂给的,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高楼大厦与低矮农舍的差异、霓虹闪烁与灯光暗淡的不同、宽阔街道与泥泞土路的区别……我的心没法再重归乡下了。
翌日,我躺至中午才起床,二哥下地干活去了,母亲也去菜园忙碌了。我穿上衣服抹把脸,掩上家里的大门,从后门出发,拐进一条乡间小路朝镇上方向疾步而行,目的地是县城。这是我的第二次机遇,它得益于二哥的一脚踹和母亲对我未来前途的定义。
时值五月初,阳光正好,气温逐渐升高,农村的活路多了起来,稻田里、沟渠边、菜地里、小河边到处都有三三两两忙碌的身影,耕牛的哞哞声、小狗的汪汪声、儿童的嬉闹声、大人的吆喝声互相混杂在一起。小路两侧树影婆娑,沙沙作响,蛰伏在树根周围和低洼处的各种野花竞相盛开,不时能闻到各种植物的淡淡清香,还有树上清脆的鸟鸣,悦耳动听。
此刻,我无暇欣赏这一幅乡村景色,它不是我心中的诗情画意,我只想尽快逃离这里,我相信只要走出去了,就一定会有所改变,这是我的信念。
我所在的村庄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通往县城的道路是由多年前的老路修整而成,一半是硬面土路,一半是碎石马路,沿路途要经过其他村庄、田野、沟渠、堤坝等,公共汽车一路行驶,摇晃得像过山车,还经常抛锚,需要乘客下来帮忙推车。不像如今已改道缩短了路程并铺上了水泥,小车可以一溜烟地跑。
匆匆上路,没有行李,两手空空,有些衣物还放在县城大哥家。我没有“盘缠”,农村挣钱不容易,平时养鸡生蛋换油盐,哪有多少闲钱给孩子花。我当时裤兜里只有一块五毛钱,坐公汽到镇里都不够,而镇里距离县城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我决心步行到达。
临近镇上,太阳已西下,迎面遇见了姐夫,他骑着自行车从镇上买了东西回家,姐夫问我:“干什么去啊?怎么一个人呢?”
我觉得很委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硬硬地回了一句:“二哥打我,我去县城找大哥去。”
姐夫顿时疑问:“娘不是在家吗?她晓不晓得你跑出来啰?二哥打你一下,你就跑啊,你晓得到县城还有多远吗?天黑都走不到!回去!我顺路带你。”
我倔强地摇摇头,绕过他的自行车,欲继续前行。姐夫一把拽过我的肩膀,我用力挣脱,姐夫就势呼了我一巴掌,干在我的后脑勺上,我没有停留,撒开脚丫往前狂奔,身后留下他不断的叫喊声,渐行渐远。
我没有计算后果,就觉得我要回到县城找大哥大嫂,那是我脱离农村的唯一希望,哪怕走到天亮,我一定会到达!
经过镇子时已近天黑,在昏暗的路灯映衬下,街道两边居民家里的荧光灯显得稍许亮堂,灯光下人影绰绰,,家家户户都有着大人小孩的应呼声,偶尔飘来的饭菜香味,更刺激了我的胃肠蠕动,我好羡慕这一家一户的温暖。在街道中心的十字路口,估计是最后的一辆班车还在不断地吆喝着买票上车,盯着车上卖票汉子的魁梧身材和粗大的嗓门,我欲言又止,最后恋恋不舍地看着班车离去,疾驶过后一阵尘土飞扬。
我掏了掏裤兜的钱,到路边的小卖部花一块钱买了一袋饼干,想买瓶汽水喝,钱却不够,讨点水喝又不好意思张口,算了,饼干填肚子更实诚。于是啃着干巴巴的饼干继续前行。怨气再大,胆子再大,雄心再大,我也怕天黑找不到去县城大哥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