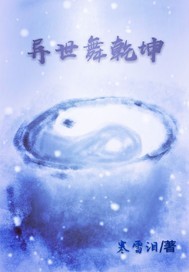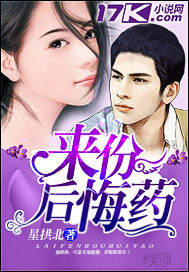学生公寓小区里有座鸡心状的小花园。小花园很简陋,单单是铺着一张石桌和三个漆成树墩模样的石凳。几株春树倒也应景。偶有几人聊聊天光,或是朗诵诗歌和散文。
花园里来过一个女孩;望见他时,她笑得有如春花儿齐齐开放。“我本来有点怕你死掉了!”她说,“看来你活得挺有滋有味的。”
每当路过小花园,他总情不自禁朝小石桌望一眼。那段不见天光的岁月,再也没有什么比等不来她更磨人的。老师的照本宣科驱不走他的念想,电影的感动或惊悚钻不进他的眼球,动漫和考试全不足以吸引他。他几乎夜夜失眠,恨不得拿撞破南墙!
于是,为了体现时间的悲悯,撑一把小黄伞的程小鱼从梅雨的季节里走向了他。她披着过肩的长发,鹅蛋脸圆乎乎。她有双聪明的眼睛,偶尔戴戴黑框眼镜,小拱桥似的架在鼻梁两道。她的唇角似乎时时翘起,唇色饱满而丰润。她的嗓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海和沙滩。她热爱音乐、动漫、电影等等关乎生活的微末之道。另外,她不喜欢高数。这就够值得深交了。
顾年实在记不起搭讪程小鱼是哪一版本的自己干出的漂亮事。坦白说,他甚至搞不清他们俩到底怎么混熟的。等到他们的交往水到渠成地密切后,他对她说:“你的名字挺有意思的。”
她说:“这是我妈取的昵称。因为我是双鱼座。”
他说:“我是水瓶座!你说是不是好巧?”
她说:“你才不是。你可以叫我小鱼。”
关于程小鱼很有点意思,我可以作如下补充:顾年有点捉摸不透程小鱼的心思。她有时敏感得怕人,比方说她会没头没脑地问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走丢了,你会找我吗?”
“当然!我会找到你的!”他不假思索地说。
“万一一直找不到呢?”她又问。
“直到找到为止。”他答得很是坚定。
程小鱼并未表现得多么感动,她心知顾年只是在复述自己期待的情话。这就是她教给他的:怎么讨女孩的欢心。
有时候,她又冷酷得紧,对他的杞人忧天简直不屑一顾。她说:“我不知该怎么说。生老病死是常事,我说不通透。要是你想听些矫情的、善意的谎话,我建议你找别的女孩去。”
由于以上种种,他们差点成为情侣。差一点儿。
那是个中秋夜,星星少得可怜,月亮分外的圆。他们租来辆脚踏车游车河兜着风。两轮月亮漂亮得有些妖异。茫茫的夜,粼粼的湖,路人识趣地退出了他们的镜头,好让他们演绎偶像剧戏码。
“你没谈过恋爱?”顾年熟练地捏造着错愕表情。
“是啊。”程小鱼尤其淡然。“一次都没有。”
“那么,你有喜欢过哪个人吗?”
“我数数。高中一个,大学……算有。”
“听起来怪有趣的,请说出你的故事。”
“我才不会告诉你!”
“我自己打听!”他狡黠的眼神在说:我才不。
“我怕你一打听发现,那人就是你呀。”
他一下子笑开了。她的幽默感多么对他的胃口呀。
一来二去,好事者们纷纷调侃起顾年来,说他考试前抱佛脚是程小鱼管教得好,说他睡前读书是因为程小鱼,说他练习夜跑和听陈奕迅的歌是想和程小鱼有共同话题,诸如此类的。
终于,“你是不是喜欢她?”他们质问他。
“我也不清楚。”顾年作思考状。
“怎么可能?”他们怕是为此开过赌盘。
“我和她之间好像差点东西。”
“差点什么?”他们不由心生愤懑。
思索了一会儿,“就是差那么一点东西。”他说。
他们不甚满意,继而着手策划起第二出好戏。新学期伊始,顾年莫名对社会活动显出了非比寻常的兴趣。他参加话剧社、他热心公益、他报名佛学讲座和唬人的创业竞赛,包括两院联谊。他们把握得一清二楚,从而确信他不会拒绝一次永生难忘的“万人徒步”活动。
万人徒步的里程约莫百公里,会横穿城市,跨越小山。他们一大堆人顶着毒日唱着歌,跳进小溪戏过水;山间的天空格外清澄,一程一程的路和幽幽的星空令他们沉默也生欣喜。
对他而言,唯一的收获是:路那么长,我终于找到了我和程小鱼之间缺差的东西——她眼里有我。
于是,某个不见星月的寒夜里,他对程小鱼表明了心迹:
“你听我说。明天到来之前,请你听我说。
“我说不清我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知道,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能够形象化,我想它正是爱情的模样。是你的样子。
“你知道,我曾有过十分暗淡的时刻,我仿佛活在折磨的、冰冷的困室里,一无所有。我好不容易借着这窗口渗进的微光,煎熬着、坚强地挺过来了。当我睁开眼的瞬间,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是你替我打开了那透光的豁口,是你让我相信我可以走出困室,是你……你是我咬牙坚持的唯一信仰!
“我欠你一句:我喜欢你。我还给你。你欠我的答复呢?”
程小鱼沉默了好久。“我需要时间想想。”
“我会等到你的。”他像是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