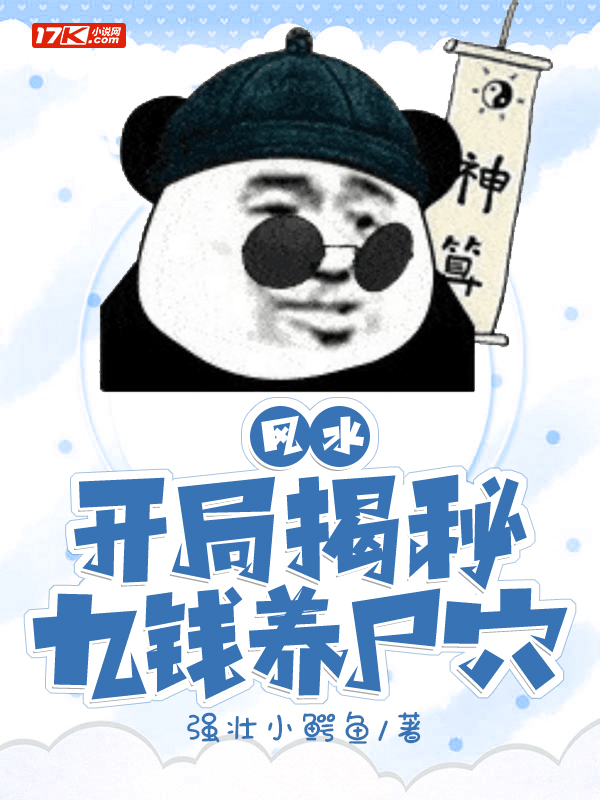有点类似沙丁鱼与鲶鱼,顾年观察着行色匆匆的旅人,他们倦容憔悴、面目隐晦,像极了罗曼罗兰所说的死在了二三十岁的人。而他,一心想要探究他们在追随的是什么。
想家么?他自问自答:不是这样的,他无处可去。
列车时刻表显示了晚点信息。顾年很是烦躁,早知道该订高铁票,搭什么夜班火车!任时刻表慢慢龟爬吧,他实在伺候不来,是时候验证相对论了。他这样想,然后检索网络小说排行榜,轻易寻见了斗字辈龙头。突然间,手机的震动彻底搅乱了他的实验。
“您好?”顾年谨慎而紧张地接通了电话。
“二狗!快出来!我来找你啦!”是个女孩的声音。
顾年登时惊得含住了一口冷空气。她的声音、她喊他的绰号无不昭示着她的身份。他神经质地环顾候车室。祝远远哪里晓得自己新号码的?有内鬼!他的脑壳像运转过热的傻瓜机般宕机了。
“我在火车站。”顾年支支吾吾。“你跑我学校做什么?”
“火车站?你偷偷回家?”祝远远说,“不通知我!”
“不然,我跑天安门升旗阅兵?”
“你一点不感到意外吗?这对我的惊喜现身很不尊重啊。”
“同城陌生号码,我脚趾头都猜得到是你。”
“万一是小妮子呢?看来你脚趾头考虑得不够全面。”
“是我弟弟干的好事?我记得旧号码是他在使用。”
“你脑筋转得那么快,是想让我夸夸你?话说,你们两兄弟声音好像,我一直以为他是你假扮的,骂了他个狗血淋头。”
“然后这二五仔就出卖了我,是吧。”
“等国骂到第十分钟左右,他说:对不起,你找错了人。我一想,这不像你的台词啊。由此,我确信他不是你的什么第二人格。”
“从来没有哪个笨蛋相信我有什么人格,你是第一个。”
“一阵子不见,你这嘴磨得跟刀子似的。难怪找不到女朋友。”
“我要什么女朋友,我不是有你么!”
“烟花!快看!好漂亮!你刚说什么难听的话呢?”
“我是问,我学校那么吸引你的话,你来我们学校读书吧。”
“我就知道你刚刚又在怼我!句式长度明明不一样。星期六,烟花祭!你这么聪明,自己推理咯。”
“祭谁?又不是端午。”
“话说你这样的好意思混二次元圈?每逢星期六,江边放烟花。这样够清楚吗?别让我又开骂!”
“我晓得!所以你为什么说我学校?”
“你学校不挨着江么!你拿我寻开心呐!”
“我头一次听说学校承包了一条江,倒是知道有座山。”
“你不会想告诉我这么长时间来你一直蜗居着,对自己学校完全没有概念吧?真是白瞎了你依山傍水的学校。”
“有你在,就不算浪费啦。”顾年说,“你回家吗?”
“我后天的票!”祝远远说,“这样好不好,你撕了票,我姑且赏赏光领你在贵校走动个把圈,我把车次告诉你啊!”
“除非你报销我的出场费、交通费、食宿费……干不了,谢谢!你领我?在我学校?我不嫌丢人?”
“这又不是你第一次丢人,有什么好怕的?”
“我从没丢过你啊!倒是你每次喊我不用特意带脸出门。”
“抖机灵的小气鬼!”祝远远说,“顾二狗,算你狠!”
她一点儿没变,顾年莫名感到有种说不清是怀念、是安慰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深觉自己理应讨厌她。她害他错过了日出!
“你好吗?”顾年发觉自己不大适合这种生硬的试探。
“我简直大写的好!”祝远远说,“好吃好喝,无忧无虑。”
“我也挺好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我没有问你好不好,你别那么自作多情!”
“你早晚会问!毕竟你那么的关心我、在乎我、想念我。”
“懒得听你打屁,我们赏烟花啦!到时候再找你算账!”
冷清的嘟嘟声犹然在耳。顾年收敛了笑容,复归僵硬而落寞模样,活像被抛弃的流浪者。时间和旅人纷纷遗忘了他的存在。他盯紧了掌心的纹路,直到慢慢失了焦。
他突然忧心如焚地翻找起小熊书包。原来暗藏在夹层里的硬币早不见踪影了。什么时候?猛回头,他却连贯不起情绪。
“她和谁在一起?”顾年忽然有些感慨。
“阿猫阿狗!干你屁事!”手机屏幕里的他变换了张脸谱。
“我对她有责任!希望他是个好人。”
“是坏人岂不更好!等她被伤得体无完肤,不正应了你的愿重投你的怀抱,一切水到渠成,不是吗?”
“我不是那样的人!”他险些要扇自己一巴掌。
“你是什么样的坏胚,你难道不比我清楚?”
“我真的衷心祝福她遇到一个真心喜欢她的好人。”
“真的、真心,这玩意听着就很假。”
“她和……反正不是我,对么?”
“瞧瞧你自己!你以为她会回头吗?才不!你演的什么戏?狗屁不是!你想把这蠢电影演砸吗……”突如其来的耳鸣刺得他脑仁生疼。他如黑镜里的自己般偏过头望向火车时刻表。
“旅客朋友们,列车即将进站。请到站的旅客朋友带好随身携带的行李……”嗡嗡的喇叭声彻底唤醒了装睡的人。
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他倚靠着硬座怔怔出神。四小时、返还的餐车和跨过他半身的旅客让这趟归程显得尤其难熬。漫漫的夜,窗也黑蒙蒙的,倒映着他洞黑的眸子和苍白的线条。
火车倾轧着铁轨嘎嘎的响。
越过漫长的黑暗,他路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夜灯。黑窗倒映着张张人影,披着蒙蒙的光。窗玻璃里也似有个她。
“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请准备好随身的行李……”
汽笛乍响。窗外微微亮着光;喇叭循环播报着站台信息。
小城尚在酣眠。宽阔的街道冷冷清清的,唯独路灯散发着昏昏暗暗的线光。路心有张长长的人影,凭着街灯一会儿照得细长,一会儿又分裂成好几个,彷如某种狂舞。
“顾年?”有人操着矫揉的台湾腔唤他。
一回头,一连串的关键词撞进了顾年的脑壳——沈谦、黄金时代、那个女孩!“老子再也不搭夜班车啦!”他暗暗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