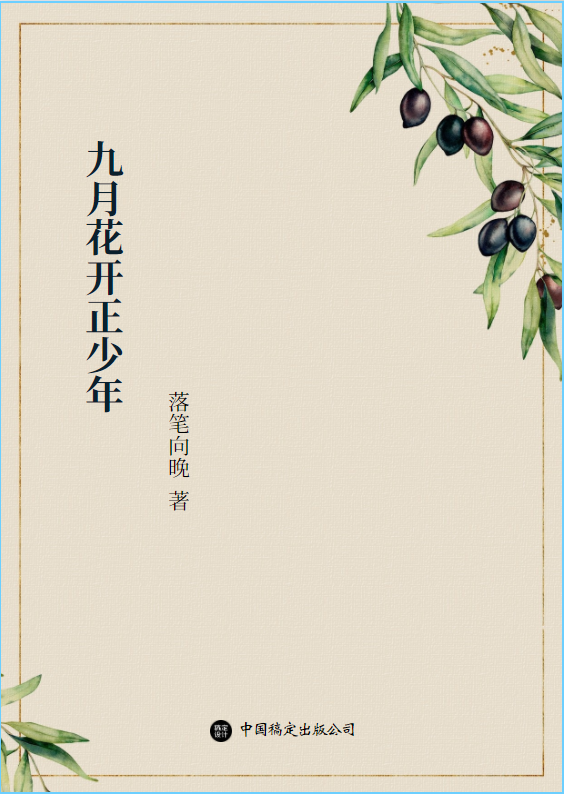他是我的病人。然后我想声明的是:他的病没得治。
他罹患的是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疑症。有的医生曾建言使用药物外加心理疏导的方式进行治疗,有的主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有的极力宣说万不得已时必须采取禁欲的手段!可我不能告知他这残酷的事实,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当然,我的私心也是驱使我为他诊治的动因——我需要他的故事。我想弄清他究竟想变成什么样、他怎么实施计划、他的动机、当他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模样时的心理活动……这样,我或许能以此典型案例写就一部医学专著,或者小说,我这饭碗就算彻底保住了。
我们的会谈里,他是唯一的主角。我不消动耳朵听他,不必对他微笑,我唯一必要的身体活动就是速记,然后根据他的讲述编造出三种无懈可击的故事,好让他相信这一切不是他的错。这当真不是份简单的工作,倘若真想图轻松,我倒不如干律师的活计。
言归正传。为厘清事态发展的逻辑顺序,让我们将时间回调一小点儿:他在敲门。他已经推开了门。
咔嚓!我摆弄傻瓜相机给他拍了张大头照。
“好久不……见?”我有点发愣。他在扮演正经人?
这是我头次见他真容,比想象的要普通点。“请坐。”我说。
为了让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舒适,我特意将办公室拾掇了一番,茶座设得简约:欧式玻璃茶几混搭纯色沙发;一架是红皮,一架是绿布。沙发墩儿是配套的,好放些细琐物件。
“你好。”他迅速打量了我一眼。“王医生?”
“一阵子不见,”我信手摘掉了铭牌。“你快忘了我吧?”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上次接待我的也是你?”
“是我的导师。”我说,“从今天起,由我负责你们。”
我对他的行为毫不意外。他对记忆环境、方向和男人的面貌特别的不在行。我暗自窃喜,这小把戏奏效了。他调整了下自己的坐姿,环顾四野。一窥见跌跌撞撞捣开了门的身影,他着实吃了一惊!
“这是我的助理,唐吉诃德,你见过的。”我说。
他全身罩在毛绒套装里,扮演着某类形象可爱的水生生物,毛茸茸的,有脚蹼,像只鱼猫,怀抱着一只竹篓。竹篓里是有关心理健康的宣传册,夹带着关于诊所的介绍材料。
“有点印象。”顾年暗暗琢磨这唐吉莫非是新复姓?他依稀记得名单里紧挨着自己的全是外文啊,难不成这是位外国人?无论如何,他的存在感着实逼人。“他为什么这副打扮?”
“是这样的,最近经济不很景气,诊所连月赤字,所以安排他外派传单贩卖焦虑。唐吉诃德,你随便找间办公室歇会儿。”
顾年仍处在失神当中,怔怔地偷眼望了望他。
“咩?”鱼猫操着口很不标准的白话。
“我还以为他和我一样。”顾年似乎有点落寞。
“确实不太正常。”我笑了笑,“他在试验我们的新疗法。”
扮演法,是我研究了几千则案例并结合了实务经验,经过亲身试验后总结出的黄金疗法。由于该理论涉及的医学术语和玄学原理深奥难懂,我作为外行在此不作赘述。总而言之,是有一天我梦见自己闯进了电影世界:主角端坐在告解亭里忏悔,然后神父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宽恕了他的罪孽。那一刻我深受感动,如受神启。
经过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技术研究后发现,信徒之所以蒙受神恩,告解亭实在功莫大焉!试想:若无告解亭里的阻隔,信徒就不得推心置腹、坦白从宽,那么神也将因其有所隐瞒而保留宽恕的权利。考虑到在非教堂场所搭建告解亭有渎神的嫌疑,基督徒可能对我人身攻击,从而导致身陷囹圄的恶果,我唯有退而求其次——任由他们蒙头遮面,或是装进戏服和套装里。
“你通知我来有什么事吗?”
“是你主动联系的我。你有给我写信,记得吗?”
“写给你的信?”
“明信片可以算作信吧。你老爱抱怨工作无趣、生活重复,不想结婚、不想买房;将来一览无余,毫无奔头,如果因抑郁死掉,墓志铭就是:无聊死了。你说失恋常围绕着你,但从未喜欢过哪个女人;你说你忘记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一旦记起就将重获新生,诸如此类的。我一次又一次建议你接受心理治疗,而你始终不作答复,直到我启动了全新医疗项目。我猜是‘无偿’的表述吸引了你。”
“……听起来很像我的作风。我忘记了什么?”
“我指望着你来告诉我哩。”我耸了耸肩。“你不用紧张。我们权当是次访谈,相信你不会感到陌生。我来问、你回答,好吗?首先,我需要搞清楚你的状态是否适宜……我们的访谈。”
他喉结鼓动,吞咽了口唾沫,显得很有些紧张。
“第一个问题:谈谈你的梦吧,为什么会困扰你?”
“梦?没错,我有做梦的习惯。我原以为是药的副作用。你知道,有的药会让人嗜睡、多梦之类的。我有时也有知觉,很清楚自己是做梦。因为它太不合逻辑了!有的人根本不该出现的,在某个特定时期,奇怪的是她的存在却让梦境显得合情合理。”
“你的梦全关于他吗?”
目前来说,学界主流观点倾向认为梦是潜意识活动所致,能反映人的深层次情绪,比如暴力倾向、性癖等等。
“我不常梦见她。”他眼光闪动,语气迟疑,明显在撒谎。
“没关系。我们换道问题。”我认为他有严重的心理阴影,这是相当典型的防御机制。“这样:假设这是片没有逻辑和秩序的空间,你有权任意杀死一个人。你希望是谁?”
他像是被打火机电激了,猛腾起身慌里慌乱地扫视。
“这种说法是有点浅白,我们按完整的原题来:有个疯子设计了某种陷阱,他在两条交汇的电车铁轨绑着受害者,一条绑了我,另一条是……唐吉诃德。失控的电车正急驶而来。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根拉杆救人,你会选择哪个?”
“一旦选择错误,我就是那个疯子么?”
“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这仅仅是个测试,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你看我自己都出现在测试题里。同样的问题我问过好多病患。”
他稍稍缓和了些又落了座。
“你的答案?”我微笑着望着他。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反复拉杆导致电车脱轨翻车?我记得曾有类似的新闻,说是并未造成死亡案例。”
“你倒是挺有新意。”琢磨了一会儿,我说:“但并不存在这种选择,或者说电车脱轨将导致全体死亡,你仍坚持吗?”
他皱着眉剜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给他难堪的蠢货老板。
“这是基本的诊疗流程,你实在不必有任何顾虑。”
“你。”一阵踌躇后,他做好了决定。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是我吗?”
他别开了眼睛,欲言又止。我返身在抽屉里摸索笔记时险些抖落了一封鲜红得艳俗的卡片。记录显示:他曾七次选择倾覆电车,三次希望自己能够替换受害者,而这是他第一次正面地做抉择。
“最后的问题:你昨天如何度过的?”
顾年全然没有料到终极问题会如此平实,支吾了一会儿后说:“我是接近晌午时醒来的。然后我随便吃了个快餐就赶到了片场。我靠演戏为生。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开了工,是在公园凉亭里,我搭档的角色名是陈欢。我老念错台词,我说我喜欢杜妍……我怎么可能对她说这些话?不该这样的!”
他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皱皱巴巴的,好似有什么重要的线索正一点一点从他的身体里抽离而去。“我想不起来了。我搞不懂为什么自己非那么做不可?有人、有人改过我的台词!”
“我们慢慢来,横竖是常规操作。”我安抚住他。这是意识混乱阶段,意味着得重新理头绪。“我们从自我介绍起头?”
这是我们的纠错机制:混乱——清理——再混乱——再清理。但他有自己的线索,有时平铺直叙,有时是圆形叙事,有时会穿插些奇思妙想。所以说,假使我这记录不够清楚,是真怪不着我。
“我叫顾年。”稍一迟疑,他又说:“我一开始不叫这名字。”
“很好,就像这样!”我对他的无条件配合给予了充分肯定。
眼见我忙活着整理记录,“这有必要记吗?”他问。
“当然!这是很紧要的素材。无论多细小、多琐碎的事,只要反复地小心验证,准能还原最初的真相。”
“我偶尔写日记。你的笔记本很漂亮。”
“这不是日记。”我合起笔记,现出了笔记的原貌。
“演员的自我修养?”他讶异得合不拢嘴。
“不好意思,是书皮。”我翻到扉页。“这其实是犯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