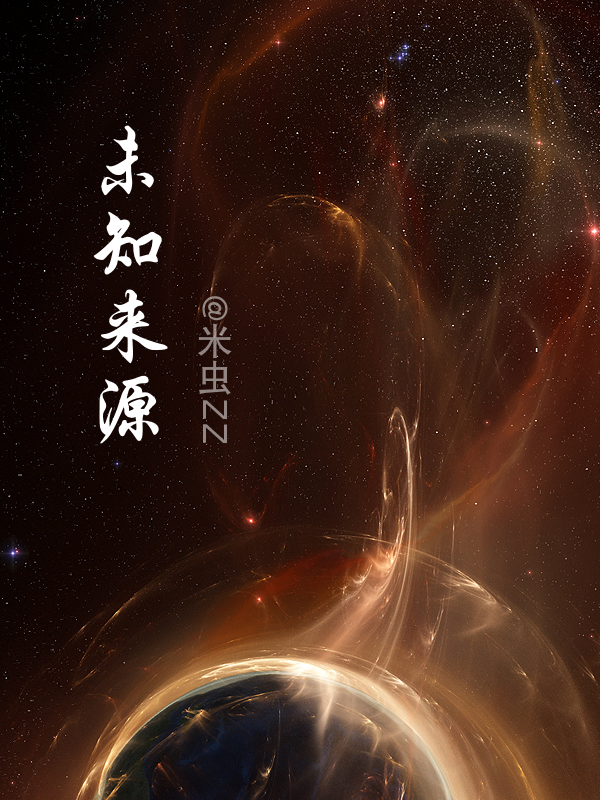“不好意思,让你久等……唐吉诃德?”我愣在了门口。
“完蛋!”身披白褂的“我”登时一激灵,脸深埋在衣领里。
“唐吉诃德,他在洗手间。”顾年迷糊地站起了身。“对吧?”
“你瞎说,唐吉诃德不在洗手间!”鱼猫摆正了头套,对我说:“医生,唐吉诃德他冒充你的事穿帮了。”
“你是王医生?”顾年如坠云里雾里。“他又是谁?”
“我不是什么王医生,你可以喊我顾博士。千万别再搞错头衔。而他,如你所见,和你一样,显然不是医生。”我说。
为了理顺故事逻辑,我们且将时钟回拨至午后一点一刻,然后将叙事视角切回正主,即是我。我刚结束午睡,脑袋昏昏沉沉的,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冰水。没错,白衬衫一丝不苟,抻着条银灰色西装裤,脚蹬圆头皮鞋,融入人潮后完全沦为背景的就是我。
我照旧刷新着社交头条,忽地被一则配图软文吸住了视线。文字很短,只有四字——恭喜家姐。配图则是一袭纯白抹胸婚纱。
不知不觉的,泪腺不争气地被引爆了。我蒙着头,磕磕绊绊地狂奔着,直奔向日光灯毫无反应的私人车库。我没有代步车,这车库纯属多余。我猜,唐吉诃德正是这时候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医生,我来就诊了,惊喜吗?这尴尬的局面,我可以解释!”唐吉诃德讪笑着脱掉了罩衫。“医生,我就客串了一会儿你,纯属体验生活。你总不至于跟精神病人计较吧?”
“他到底是……”顾年望着唐吉诃德离去的背影。
“是名话剧演员,体验派,来找创作灵感的。”我说。
“所以我……”他眉头紧锁,布满了疑虑。
“你和我就是他的素材。我以你为原型写自传,而他负责改编为剧本,很大几率会自导自演。”
“他演我吗?”顾年忧色浓重。
门被推开了,唐吉诃德的形象已焕然一新——身着中世纪古堡贵族的华服,戴铁皮头盔,眼神宛如一潭死水,颇有点不伦不类。
“你看他像吗?”我轻笑了笑。
“言归正传。你记得Pear吗?或者说,雪梨。”我望着他。
他的故事里,给我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雪梨。但他老不肯给我透透底,我有好几次铩羽而归,仅剩的一星半点成果无非是他有时这里说到过她,有时那里提起了她。他的故事似乎通通与她有关。
初闻雪梨,是有关于他有几任女朋友,以及交往不足三十三天的恋情是否算数的话题。这是他所谓的精神洁癖,仿佛他喜欢过三五个或十几二十个女孩是万分紧要的事。而不论怎么改口,他总是这样介绍雪梨:她是我这辈子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据他所述,他一生有好多的遗恨,大多是自招的,比如他从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十句话里只有标点符号是真;他对喜欢的女孩绝口不提真心,不真喜欢的除外;之类云云的。
“真相是什么?我暴雨天骑着单车狂飙是因为我担心她会不会淋了雨、躲在谁家屋檐,却在半路撞见了她家的小汽车。我认得她家的车牌。放学后,我会等她不是因为要顺道探望奶奶,只是为了她。我说过会为她叠一罐子纸星星。那天在学校礼堂,人潮将我们冲散,我听见有人呼唤我的……”顾年的侧脸映着回忆的暖色。
“她喊过你名字吗?”鱼猫提起了兴致。“就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时候,你只听见了她的声音?”
“有什么问题吗?”他似乎在害怕什么。
“问题就是她有没有呼唤你,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如果有,就说明你真的很喜欢她。我敢打包票,肯定是这样!”
“为什么她喊他的名字,是说明他很喜欢她?”唐吉诃德说。
“我在电影里学过!我研究过各色各样的电影,”鱼猫掰着指头纠结着他(她)是谁。“他们全是这样,一准没错。”
“奥斯卡,你收藏的那些电影片头是不是有红色警告,或者是标明了未满十八岁,需有家长陪同观看?”唐吉诃德揶揄道。
“你好像在跟我对暗号。为什么喊我奥斯卡,我又不是演员?”
“你知道《铁皮鼓》么,你和主人公奥斯卡很像,当你发现成人的世界里充满邪恶和虚伪后,你决心不要长大。某种冥冥力量成全了你的愿景,使你的身体定格在十岁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你对这畸形社会的无声反抗,很具讽刺意义,不是么。”
“我是缺乏生长激素所以发育迟缓。我可以对此作出十分科学的解释:我妈是矮个子。她可能理解不了讽刺的含义。”
“原来我多虑了。我的故事却是这样: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唐吉诃德摇头晃脑的。
“麻烦长话短说!”我说,“我们不要你加戏。”
“总之,那一年我遭受了人生的重大打击,从此浑浑噩噩、百无聊赖。直到有一天,为了振奋我的精神,一号——他是我的室友——将他珍藏的小电影给我解闷,气氛热闹得像过春节似的,我们围坐在电脑前细心检阅。那夸张的镜头、冲击的动作和矫揉的猫叫,强烈地刺激了我,我感到我的精神世界在层层分解、重塑……”
“于是,你遭受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希望通过心理治疗达到重新做人的目的。很寻常的套路,没什么稀奇。”顾年说。
“我沉浸小电影无法自拔,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动作教育,一心追求猎奇的剧情。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精神受到污染的表现。后来,我来到了快活的地方,闪烁着粉色的霓虹灯,女孩们一字排开,像在夏威夷阳光海滩似的。我说我是第一次,小姐说她也是。那一刹那,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你发现了成人世界的邪恶和虚伪?”鱼猫有样学样。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有阳痿症。”唐吉诃德摊了摊手。
“我只是个未成年的水獭啊!”鱼猫拍着假耳朵跑开了。
“别搭理他们插科打诨。待会儿我联系助理将他们通通轰走。”我对他循循善诱:“刚刚你提及学校礼堂,发生了什么?”
“对,是她。像他说的,看来我是很喜欢她。”他露出了一弯苦涩的笑容,显得忸忸怩怩的,兀自念念有词。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说,“喜欢她是自己的事,但知道你喜欢她,是她拥有的权利。你觉得呢?”
“我觉得鲁迅先生没有说过这些话!”顾年说。
“但他承认他可以爱,你呢?”
顾年欲说还休。我们的视线刚一碰触,他忙又敛回了眼光。挣扎再三后,他终于松了口,说:“我不敢告诉她,我是花舌头。”
“花舌头?是缺锌引起的病症吗,可以试试补充葡萄糖酸锌片,加强营养,多吃水果蔬菜,会慢慢好转的。”
“我也少年白。”他又说。
少年白头又不算什么难堪的隐疾,他却羞恼得涨红了脸。
“她说我的眼睛是旧琥珀色。”他叠扣起指头,显得很是局促。“我的、我的食指也比无名指长。”
他低垂着眼。这又使得我没法一下子望穿他眼瞳的颜色。
我本想告诉他这不算什么,完全没必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见他心有惶惶的,我又觉着这不公平。他本是多么骄傲啊!你再瞧瞧他,分明像被激流磨圆的鹅卵石。当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后,他发觉整条河川都辽阔了;他厌烦自己不圆滑的弧度,他生怕渔农看出他色泽暗淡。对他来说,这一切便足以构成天大的麻烦。
这才是他的花舌头,我想。
我起身给他添水,一不小心磕碰了一下脚边的沙发墩儿,所幸顾年没有碰倒相架和玻璃杯。他手忙脚乱扶正了相架。相片是环球旅游时拍的,是张三人合照。那个赌气的姑娘是我的未婚妻。
他接过了水杯,并未如我想象的那样礼貌地抿一口。他忽而停住了动作,玻璃杯就此悬停在半空。等回过神,他怅然若失地放开了水杯,好像记起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很快,他的战战兢兢消逝殆尽了,眉头一掀,目光炯炯地讲述着他的不英勇事迹。他告诉我因为怕羞,不敢在众目睽睽时和雪梨一人一段耳机听歌而落荒而逃,在走廊窃喜好久;放学后那段长长的路和旧旧的街景彷如昨日,他们的剪影越来越近,一程又一程;他为她遇到难题时向他求助而骄傲不已,他为她玩笑般的小抱怨而欣喜若狂,他为知晓她爱吃草莓味的棒棒糖而欢呼雀跃……
“高中也是!”他娓娓地说:“因为一清早洗内裤耽搁了时间,我在公交站碰到了林康,就搭他的顺风车。半路,我发现她在等公交,便忙让司机停车。等不及司机停稳当,我猛地就推开了车门!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举动。”
“范又妮和你并不顺路,”我提醒他。“你应该遇不到她。”
他安安静静地凝视着我。眼眸清明如水,倒映着微光闪闪发亮。我猛地意识到他一直在等我误会他。他一层一层地泛起笑容,活像恶作剧得逞的顽童,对我说:“本来就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