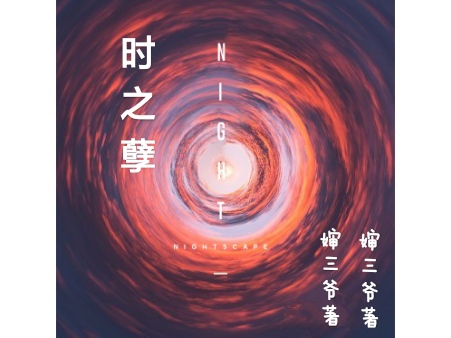当黎明从黑暗中走出,街道上的行车慢慢开始叫嚣的时候,在赢州市东部靠近港湾的一处花园式别墅似乎还在寂静中沉睡。
这处别墅,大门紧闭,围墙高筑,两只肥壮的德国黑贝犬俯卧在院子西侧的犬舍傍边,它们眼睛虽然闭着,耳朵却还在高高地竖起,好象在睡梦里也不忘主人赋予的使命。
当阳光从树林中穿过,姗姗地射在别墅二楼阳台的时候,孙老六依然躺在绵软的大床上鼾声如雷。他全身赤裸,怀中还搂着一个洁白如玉的睡美人,一条薄薄的青纶大花毯子,已被二人踹到了腿的下面。
“铃——”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二人从美梦中惊醒。
那女人懒懒地翻了个身,嘴中埋怨了一句:“真是烦死了!”
孙老六则揉了揉眼睛,伸手抓起了床头柜上的电话。
在听电话时,他口中不停地“哼!啊!”着,最后说:“你马上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
扣上电话,孙老六伸手在睡美人光滑的胴体上俏皮地摸了一把,然后穿上睡衣慢腾腾地下了楼。
保姆立即给他端上了早点,孙老六刚吃几口,就听到大门外有轿车鸣笛的声音,不一会儿有人给打开了门,轿车缓缓驶进了院子,紧接着齐唰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屋门上的门铃响了起来。
孙老六使了个眼神,保姆便从门镜中望了一下外面,随手打开了门,只见五个青年男子鱼贯而入。
孙老六仍然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他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叫众人坐下。
最先进门的两个高个男子,似乎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在孙老六的招呼下,大踏几步就分坐在孙老六的两侧,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这二人正是孙老六的贴身保镖:方保信、杜锋。
而其余三人却明显有些拘谨,三人步履凌乱,神情不定,六眼无光,他们在近门的一个沙发上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这三人则是那天晚上在港湾码头被张雨亭办案抓走后刚放出来的。
孙老六瞟了众人一眼:“吃早点了没有?”
那个扎小辫长脸的保镖方保信忙开口说:“我们刚在外面吃过了,六哥!”
孙老六也没有再礼让的意思,他瞅着对面坐着的三个人问:“怎么样,他们没有难为你吧?”
那三个人中一个矮胖的男子开口说:“没有,六哥,他们就是问我们是谁烧的船,勇哥是不是在船上,我们都说不知道,我们只说是见有人烧船我们前去进行制止,别的什么也不清楚。”
孙老六满意的点了点头:“看不出来你们都还挺机灵的吗?”
其中一个黑脸的满脸堆笑着说:“这不都是六哥教我们的吗!进了公安局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屋里的人顿时都笑了起来。
孙老六拿起一个面包自顾慢条斯理地吃着,又问:“他们没有逼迫你们说一些别的事情吗?”
那三人摇了摇头。
孙老六“嘿!嘿!嘿!”笑了几声,一副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妈的,谁说现在的刑警队大队长张雨亭是个难弄的主儿?他这不是挺开通的吗!还没等我找人疏通,他就把你们放出来了!哈!哈!哈!省了我不少周折啊!”他显得非常开心,就象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
那个黑脸男子立刻陪笑说:“那是,谁敢和六哥作对呀?除非他活腻了,刑警又怎么样?以前的刑警大队长武少军不也是被六哥整的干不下去了吗!”
孙老六边嚼面包边笑骂说:“你这混小子知道的还不少,不过,这件事只能在这说说,千万可不要到外面乱讲,再说,这件事还有他妈的那段二胖子的份。”
一提起段二胖子,孙老六就气的牙根直痒痒:“段二胖子这个王八蛋,他竟敢烧我的座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随即他又想起点什么,盯着几个人人问:“哎?段二胖子不是也有个手下被抓去了吗?他的情况怎么样?”
坐在下位的那三个人几乎一同答道:“听说也和我们一起放了。”
“也放了?”孙老六冷笑了一声:“呵!这张雨亭做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圆滑了,这可和他以往的做事风格大不一样啊!也不知他葫芦里埋的究竟是什么药。”
他摸着下巴六又一字一板地道:“我们可得提防他‘明修战道,暗度陈仓’啊!”
众人领会地点了点头。
这时,平头方脸的保镖杜锋说:“六哥,段二胖子烧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何不主动报案,让公安机关缉拿他段二胖子?”
孙老六将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报案对咱们有什么好处?难道让公安局去查他段二胖子为什么烧船?为什么杀何向勇?查来查去,原来是因为我们窝藏罪犯?”他点燃了一支烟:“这件事,公安机关能停止调查,对咱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咱们既要对付段二胖子,又要对付公安机关,两难应付啊!”
“可何向勇还在警方的手里。”保镖方保信提醒孙老六说。
“这个狗杂种,挨千刀的,都是他惹的祸。他自己闹的事和我有什么干系?”孙老六把手中点烟的打火机往茶几上一摔,破口大骂起来。
方保信心有疑虑地问:“六哥,何向勇这小子醒过来会不会昏了头把咱们别的事情都给抖搂了出去了?”
孙老六眯着眼睛:“这个何向勇我孙老六平时待他不薄,况且他现在也应该知道,犯了案杀了人,说与不说都是死路一条。”继而他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不过嘴长在他身上,终究不太保靠。这个人也参与了咱们不少的事,一旦透露给了警方,就算不要我孙老六的命,也会扒我孙老六一层皮。所以,一有机会……”他抬起手做了一个切的动作。
坐在下位的三个人见状,变得有些惊慌起来,那个矮胖的男子颤声道:“六哥,难道就不能走走关系,想想办法,救救勇哥吗?”
孙老六瞪了那人一眼:“救?怎么救?你说的倒简单,他把事情搞的这么大,公安局不拿他开刀怎么服众?现在就算市长是我爹,恐怕也没办法救他了!”孙老六长叹一声。
转而,他又和颜悦色地说:“你们几个人在刑警队里表现的很好,难为你们了,过几天我自会论功行赏。”
三个人立时喜笑颜开:“谢谢六哥,其实六哥的船被烧了,我们也有责任,六哥这么做真是太客气了。”
孙老六挥了挥手:“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没想到他段二胖子会下手这么快这么狠。”他站起身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停在了杜锋面前:“阿锋,我叫你问的事儿,你都问了吗?”
杜锋马上回答:“六哥,所有的人我都问过了,前天晚上前去港湾码头烧船、杀何向勇的那帮段二胖子的人,大伙都说不认得,只有一个人说有一个浓眉、长方脸的男子隐约有些象……”
“象谁?”孙老六催问。
杜锋缓缓地说:“象金夜迪厅看场子的徐战东。
孙老六哼了一声,斩钉截铁地说:“金夜迪厅是段二胖子的产业,那肯定错不了”他狠狠捏着手中的烟蒂,眼睛布满了血光:“不管是谁烧了我的船,都逃脱不了责任,小到徐战东,大到段二胖子,我都要一个一个地收拾。”他这时已站在窗前,眯着眼睛望向窗外,面部表情变得很诡异,仿佛正在酝酿着一场反报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