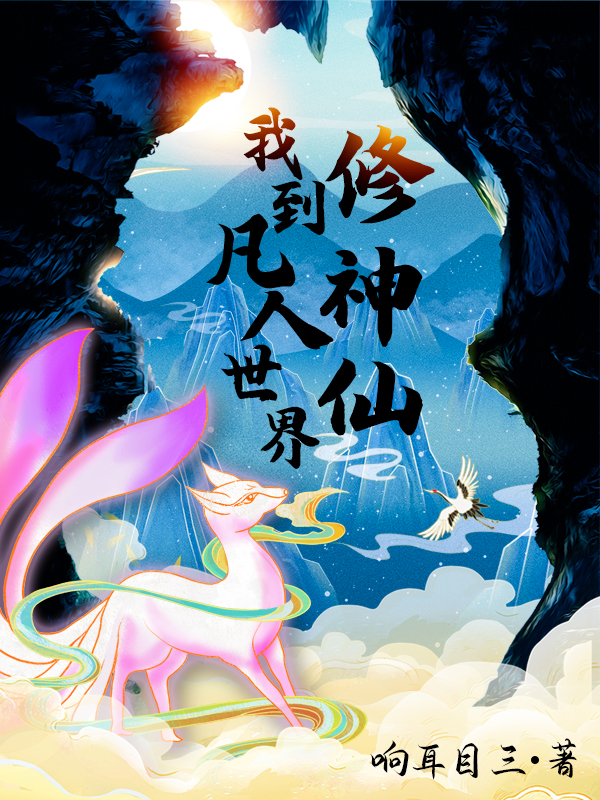夏至过后,吸足雨水的野草、野花,远远的,都能听到生长的“吱吱”声。天有不测风雨,艳阳高照两个月后,就来了一场雪,豌豆粒大的雪,又把草啊花啊冻枯了。
那时,桃有一岁五个月大,她的妈怀孕了。怀孕本是件喜事,可在她们家里,妈的怀孕比不是她家老母牛怀崽高兴,母牛下崽会给家里带来收益,而她妈怀孕,给她和妈带来了春雪般的灾难。
肚子一天天如皮球圆起,家里人就毫不忌讳在饭桌边讨论,让她的妈妈的担心,像装满火药般圆大起来,只要了见火星,就要爆炸了。
孩子没出世,家里人就给判定了两条路,如果是女孩,一条是送人,一条就是不能给见阳光。
晚饭吃到一半,奶奶对桃的妈妈说:“大媳妇,我说你莫火起,如果这个还是个姑娘,就不要了,如果是要留着,就送给你大哥。”奶奶这么说,因为比桃的妈大12岁的大舅爹,在桃出生以后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孩子,夭折了,一直没有孩子。
“如果你大哥不要,就不要留着了……”说着,筷头从碗里捡出一块肥肉,扔给了桌下的大黄狗。
桃子的妈不敢看婆婆的眼睛,可能是长期和那条大黄狗共处,她那满脸褶皱的浑眼里,有大黄狗一样的绿光,看着吓人。
可能是料定可以生过男孩,在孩子没出生前,桃的爹妈有过短暂的“出双入对”恩爱,妈也常对着那面破镜子,把长辫子梳得又黑又长。
春节很快就到了。
春节,桃的老家有回娘家拜年的习俗,那时,妈的预产期两个月。
桃的爹妈带着桃子回阿婆家拜年。在阿婆家住的第二晚,睡到后半夜,桃在迷糊中被妈唤醒,她睁开眼,见阿婆、姨妈和舅爹舅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她还小,不知道大人在商量什么,但后来长大了,三舅爹告诉她,那是在商量着要不要把她的爹叫醒。
别人都说要叫醒桃子爹,理由很简单,桃子的爹是未出世孩子的父亲,桃子的妈却斩钉截铁:“不要叫,不能叫。”她生怕又生个女儿,孩子就没有存活的希望和机会了。
桃子的三舅爹最后做了主:“不叫了,赶紧走!”安排小姨妈背上桃子跟着妈妈,桃子的外婆紧随其后。
像逃难似的地走了一段,桃就不乐意了,她用哭闹来表示她要妈妈背,只有妈妈的背,才是她唯一的安全港湾。挺着大肚子的妈妈,只得背上桃子,恐惧赶着惊慌失措的她们向前跑,向桃子的老家方面跑,向认为安全的地方跑。桃的阿婆家和桃的家中间有一条河,她的妈妈怕还没有过河,孩子就出生了,再过河就麻烦。
跑在最前面的桃子的妈,过了河,手脚并用地爬上一个小山坡,在野外的深夜里,在惊慌失措里,桃的妹妹降生了,惊慌失措的奔波和逃避,让桃子的妹早产了两个月。因为命中注定要活,所以,她出生的时候,计划着要她命的人,一个都不在她身边,身边只有作为姐姐的桃子和苦命的妈妈,另外就是还带着刺刀的寒风。
那时,桃子不明白,为什么出世后妹妹在呱呱地哭,妈妈也在树下下默默地哭,哭泣的声音,让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掉进了恐惧的深渊。她就在她们的旁边,受伤小狗般莫名其妙地看,一直等到阿婆和小姨妈赶来,小姨从地上捡起已快哭得没气的妹妹,放进桃阿婆的围腰里,阿婆把围腰的两个角别进围腰带里,扎紧了带子。妹妹太小了,兜在围腰里的妹妹,就像兜一把小葱小菜。
回到桃的家,桃的爹还在阿婆家做着生儿子的美梦。
推开大门,桃的奶奶正抬着水桶往门的方向走,准备去给要下崽的牛喂水。看见阿婆和姨妈,便明白了几分,她一边走路一边目不斜视地问道:“亲家母,生得个什么?”
桃的阿婆胆怯地说:“哎……!亲家母,添得一个小孙女外。”
桃的奶奶听了,把铁桶丁零当啷地丢在牛圈门旁,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音调,颤抖着仰天长啸:“哎!……!……!啊……!……!……!……,树叉叉就这样折了一叉了!”她奶奶的意思是,一个家族是一棵树,一个儿子就是一个枝条,儿子生儿子,就是枝条长枝条,生不出儿子,就相当于那一枝没了。
牛有水喝,人没有。喝不上水的外婆,觉得自己的姑娘没能给姚家生个儿子,愧对亲家,在桃的妈妈躺下后,就悄无声息、无可奈何地回家了,丢一声哀叹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