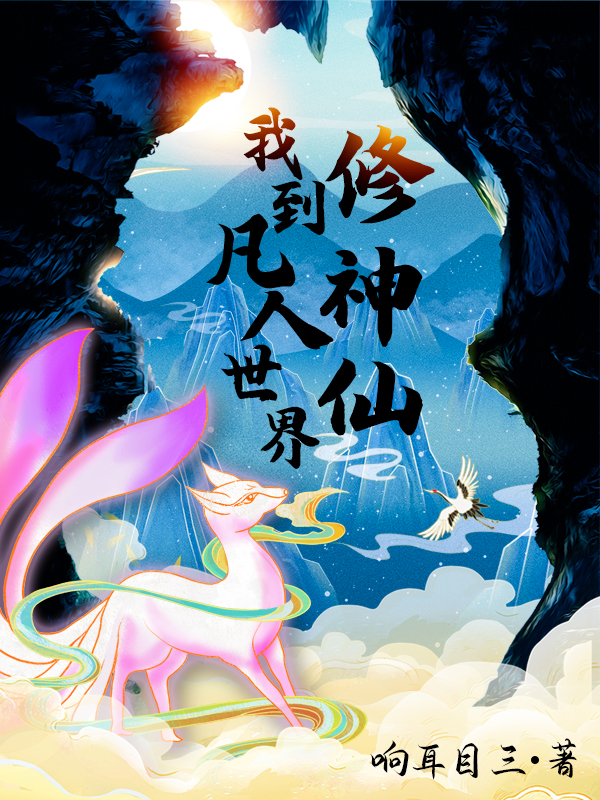一条大河蜿蜒而过,四面喀斯特地貌的石头裸露着,山顶的树稀稀疏疏,像垂暮老人的头发。
冬天让人穿上了臃肿的衣服,让树木落了积攒了一个春天的叶。
桃子家在山中腰的一棵大青树边。那会,她的妹已出世后,与其说是从老家分出来,不如说是被撵出来了。
桃子参加完作文竞赛就回家了,学校放寒假了。
回家闷在屋子里的桃子,郁郁寡欢,妈跟她讲话,她也一句不应。
妈觉得有些不对头,想这闺女是不是痨病了,把手伸在桃子的头上摸了摸,又在自己的头上摸了下,心说,也不见烫啊!
“老婶说你去参加竞赛了,妈还给你煮了个大鸡蛋,我这去你取,闺女有出息了,妈得奖你。”三十多岁的女人,婆婆的责难,丈夫的打骂,气血一点点从眼里抽走了,苍老、木纳、瘦弱得如一个六十的老太太。
“不要说作文了,说就来气,”桃子是开嘴言语了,不过脸涨得通红。
“写得不好?莫怕,不是说你们学校,就只有你一个去吗,独蒜苗喽,我闺女厉害哩……给妈长脸了。”
“长什么脸,丢死人了……”
“这死女子,性子还大,”望着姑娘去睡处的后背,摇了摇头。
桃子进门上了床,用被子把自己捂住,捂不住伤心,委屈的泪水还是不听使唤地流了下来。
她觉得自己是委屈伤了,被爷爷打、爹打,都没有这般委屈。自己写不好作文,她不知道是怪自己笨,还是老师不说给怎样写,总觉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就如老鼠进了上了盖子的大盘箩,找不到出口。
那日,她战战兢兢地,挪步走到贴了自己名字的座位上,没有心绪用眼睛细细瞧下比自己蹲了三年多更大、更漂亮的教室,脚腿子就发摆子般打颤。她不明白什么叫作文,更不知道要怎么写作文,就像是人人都说有鬼魂,也不见人抓着给她瞧过,是有头无身子,还是无头有身子。
老师把三张绿色线条的格子信笺放在她面前时,她发现了拿着笔的手,溢出了细细的汗水,心蹦蹦乱跳,就要跳出胸口了。
她让自己镇静,努力让自己镇静。她咬紧了笔套,一下,就一下,他回过神,说,不能咬,自己就这么一支笔,咬坏了怎么办,她把右手大手指放在嘴里,狠狠咬了一口。
她把注意力拽回到教室,别的同学都在写了,教室除了她的心跳声,就只剩下“沙沙沙”的笔啃食纸的声音。
安静让她更加着急,怎么写作文呀,她左看看,右瞅瞅,样子像麻线脖子系不住橄榄头,由于个子高,她看到了前排的女同学,她把脖子拉伸长,瞧见了,那个同学是在写她与妹妹争小花伞,写的是吵架,这就是作文?
她终于有主意,她在格子上写道:星期六,我跟妈妈一起去割麦子……妈妈割得很快,麦子的刺,像黄泡树的刺,尖尖的,很刺手。太阳很晒,可妈妈和我得不说苦,也不说累……那晚,爹又骂了妈,还打了个嘴巴子,可妈妈没哭,我和她看到院子里的麦子,还乐呵地笑……
她一口气写完,到交卷时,才知道作文要有个题目,开头要空两格……
她觉得自己写的不是作文,给学校老师的脸丢了……
但是,结果却是她想也想不到的。
那天一早,喜鹊在那棵榕树树上叫得很欢。
“小桃,小桃,起床了。”火红的太阳升得一杠子高了,妈叫桃子起床。
“让我再睡会,我不想上学。”
“上那门子的学,是不是睡过头了,不是放寒假了么,今儿妈带你去表婶家做客、吃酥肉。”
“做客?”桃子掀开铺盖,一大块冷黑呼呼向她压来,她又把被子盖上了,可在被窝里一想要得吃香油炸得黄生生的酥肉了,肠胃勾得酸溜溜的,睡意压不住馋猫了。
她一脚踢开被子,左手就往床下站,套上裤子,汲着鞋子,一边扣纽扣,一边往外走,由于鞋子没穿好,走路的样子像企鹅,右脚挪一下,左脚又挪一下,到了院台,蹲下穿好鞋子,就要去找脸盆洗脸。
“你看你的衣服……”妈指她的上衣说。
她低头一瞧,发现纽扣扣错了,正要重扣,又听到妈说:
坐客要有坐客样,快去把那件小花格子衣服换上。”
小格子上衣是她最漂亮的衣服了,穿好了,她还用手把褶皱抹了抹。
走的是山路,路弯得气喘吁吁,把人也走得气喘吁吁。太阳出得三杆子高了,红灿灿地挂着。山上的樱花开了,一树接着一树,在山上缭绕。一只不知名的鸟,振动着翅膀飞向山顶,尖叫一声,飞过山顶去了。
走到办喜事的表婶家,左邻右舍已在热火朝天地忙开了,最热闹的是一伙男人是在杀猪,有人在扯猪脚,有人在拉猪尾巴,咂在男人嘴里春城烟的烟雾,和着大锅里褪猪毛热水的蒸汽,把这个小四合院蒸得热气腾腾。
“我怕!”当桃子看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时,扯紧了妈的衣角。
“怕什么,就要得吃猪肉了,小桃怎么还这么胆小!”与妈坐在一起的妇女说,小桃的妈从进院后,就和一群中年妇女一起捡起了菜,捡菜,就是把一些杂物质捡掉,以备第二天正客天做菜用。
“我家桃做事是胆子正呢,就是怕血,”小桃妈说着话,手还在不停地捡豆芽。
“姚桃,你也来做客啊,这下好了,我不用再跑你家了,你知道吗?你作文得奖了,还是一等奖,”那个养猪老师,是不是太兴奋了,脸上了一层厚厚的又红又腻的油光。
“谁得奖了,得什么奖?”
“有奖金吗?多少钱呀?”
一颗颗脑袋齐刷刷地凑过来,来看个稀奇,如一群抢食的红冠子鸡。
“搞错了吧,我家闺女这两天一天到晚像个‘闷葫芦’,说写的什么作文,写砸了”。小桃妈有些不相信。
“是姚桃,一等奖,这是奖状,”说着,他把镶着一颗红色五角星的奖状递了过来。
“是姚桃,是我们家的姚桃,”姚子的二婶嚷道。
“什么我们家的姚桃,你家的叫姚生……”有人讥笑了她,她就如出气了的猪尿泡,一下干瘪了。
“不管怎样,小桃是给我们长脸了。”四婶帮着圆场。这个女人,因为小桃奶奶的挑拨,她也是时常被丈夫打骂,几年后,桃子新眼目睹了二叔、四叔和小叔把四婶脱了衣服毒打,还要把她放进大锅里煮……那次后,四婶失踪了,一点音讯没有,等好多年后,她带着另嫁人后生得的儿子,回到那个曾经的家,跟四叔离了婚。长大后,桃子觉得四婶是个英雄,她用实际行动反叛了不公平和欺压、侮辱。
那天获奖的情形,多年后,桃子都觉得那天是她最骄傲的时光,虽然作文得奖,为自己以后搞文字工作增加了洪水般奔流的信心,最关键的,是觉得作为没有办法改变性别的,一个活在白眼下,亲人想扔掉的馊菜馊饭长大,比过了同姓同年生的、叫姚生的哥,被左邻右舍欢喜了一番,这欢喜,变成了她身子里热乎乎的筋血。
此时,蜷缩在一角、一直默不作声的小桃,也过来瞄一眼:“不是我吧?”小声得像蚊子般问了句,在她心里,作文是没有写好的,不要给老师和妈丢脸就行了,更不要说得奖。
“姚桃不是你的名吗?”老师问,“你就是姚桃啊!”
“姚桃多呢,老师,我在后两里就有个姚桃,”小桃嗫嚅着。
“是啊,我们这寨子有好几个姚桃,我家这闺女,也是有人叫姚桃,才跟着起的……”每次,想起自己的爹连名字都没给起个,桃子不免有些悲凉。
“不会错,是你家的闺女,得一等奖了,还有资金……”当妈接过奖状,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用有些颤抖的手把奖状递给闺女时,巨大大的幸福紧紧地抱住了她。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感觉比当时能嫁给水泥厂工作、白高帅的桃子的爹都幸福。
多年后,当我坐在桃子妈的面前,谈起桃子,在她的脸上,只能看到散发着甜蜜的骄傲。那时,老人的儿子死了,桃子身体也不好,可她还是觉得桃子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骄傲,用她的话说,是比男人更顶事。
“这真是一等奖啊,大姐姐,你太厉害了,长大我也拿一等奖,这是什么,真好看!”一小女孩歪着小脑袋,一脸羡慕。
“这是五角星,你长大也要向大姐姐学习,呀,一等奖,太厉害了,现在都会写文章了,长大就是大作家了。”小女孩妈妈看着奖状说。
“作家?我要作家给签名,”又有个小女孩说,说着,在口袋里搜了搜,又说:“签名也没带笔啊!”
这时,老师拿出笔,说:“笔我带着,可你们要签到什么地方呀,不会签到脸上吧!”
“就签脸上!”
“你不怕把脸搞脏吗?”她妈妈说。
“不怕,今天先签到脸上,明儿我又找笔记本,再找姐姐签……
小桃昂首挺胸,在那小女孩脸下,写下了几个歪扭扭的“姚桃”,由于笔是红笔,字像一朵红花开到了小女孩的脸上。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很特别的鸟,降临到了这片天地,连孔雀也没有自己美丽。
从此以后,获奖的荣耀,像糨糊一样粘在了桃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