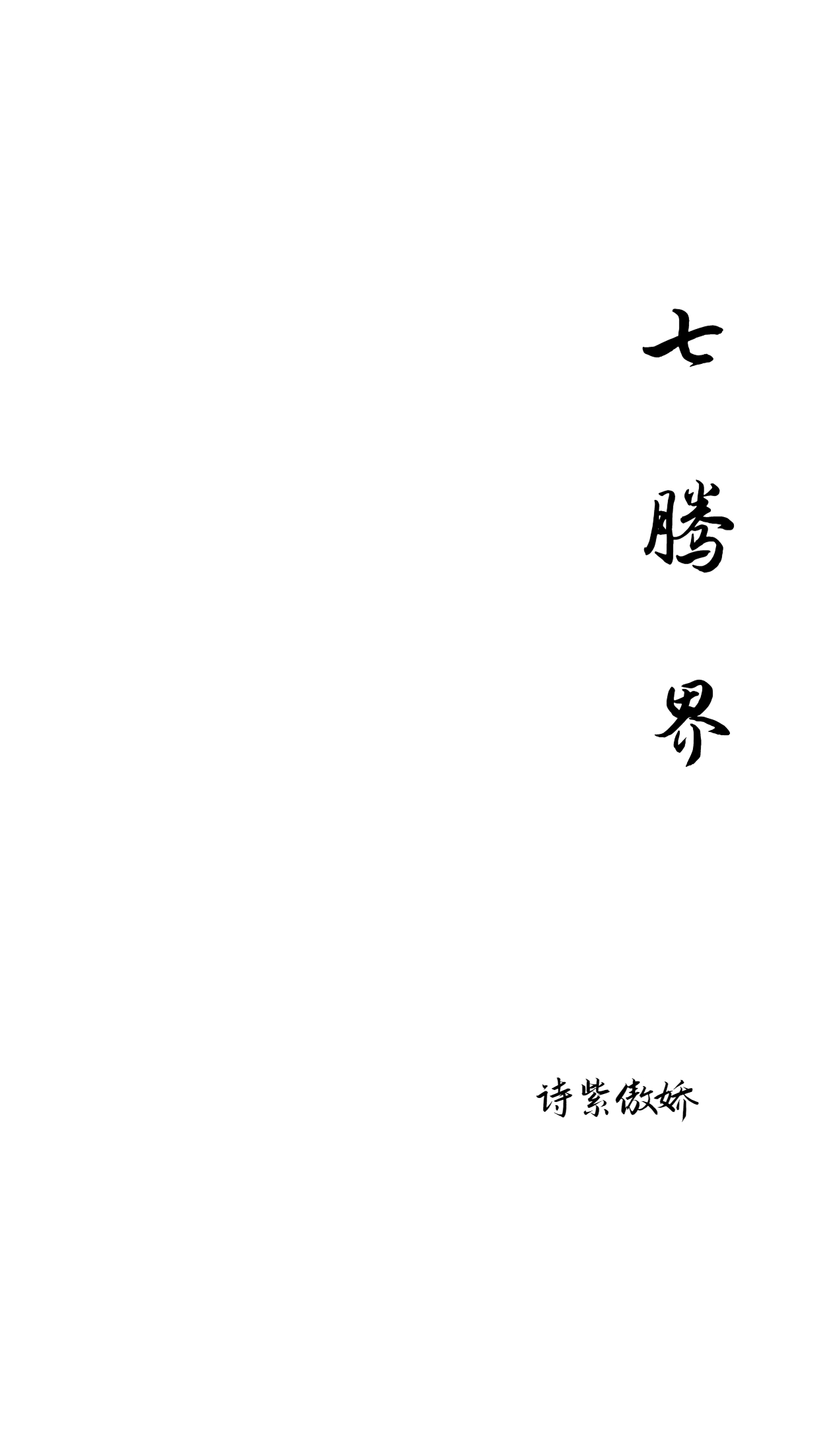她上课时,常常会跟孩子讲她上学时的故事,每每讲时,心酸就会从眼睛喷薄而出,她哭,孩子们就跟着哭,她笑,同学们就跟着笑……
她珍惜人民教师的荣誉,她不想误人子弟。
夜深了,他常常想起自己读小学时的事,她差点就被“误人子弟”惨痛。
到中心校上四年级,才知道什么叫上课,上课老师要一笔一划写板书,要领着鹦鹉学舌读课文、要做作业。
她读书的山村小学,老师是俩夫妇。
两个老师把几头猪喂养得肥肥大大的,肥大的猪,主要功劳归功于这群懵懂的孩子,猪吃的食物,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上课的时间要打,放学也要打,到学校后边的山林里打,到老乡的农地里打。猪食打回来了,还要小孩们用薄刀切碎,春夏秋季还好点,到冬天,要把切碎的猪食撮到大缸里,猪食里不仅有猪食,还有冰块。老师不允许孩子们用撮箕撮,要用手撮,用冻得通红的小手撮。老师说那是劳动课,要认真,就如老乡案板上的猪,要宰杀了,不能叫,嘴要用绳子扎上,不忘念叨一句:我吃你肉,是天经天义的!
中心校要组织作文竞赛,要每个教学点推荐一个名学生参赛。
“不参加行吗?”在村公所,这位平时把教学当副业、养猪当主业的教学组长,有些为难,他心里清楚,他还没有真正给孩子上过作文课,要是让自己教的孩子去比赛,不是去露馅吗?有人叫自己老师怎么好意思应?
“必须参加,知道必须吗?”那头好像线断了半分钟,又听到说话了:“下午就把名单报上来,记住了,到时,娃你要亲自送来,亲-自-。”话语就是上级对下级老子对儿子般的强硬,不容置疑。
“我得同组里的其他老师商量下。”他把“其他”两个字说得很轻。
“其他老师?老李啊老李,要我怎么说你,不就是你婆娘吗?这点球事都要去商量,我看你这个组长也让了吧,省得给我们男人丢脸……”“啪”一声,对方挂了电话。
被训了一通,黑着脸回到学校,看一群娃还在剁猪食,大砍刀剁在木板上,声音很欢快,就如风吹过后山的树林。
“不要剁了,都回教去。”
声音“咯吱”像一根绳子样断了,一双双小眼睛瞧着老师,神情有些不情愿。
“回去,快点!”
没有人动。可他浑重的话把圆腰女人从厨房里拽了出来。
“还没剁完呢,你发什么神经,不叫娃剁,你要剁吗?”
“今有大事!”
“什么大事?”
“中心校说要让我们派个娃去参加作文竞赛。”
“这算什么大事,派去就得了。“
“哪?派谁去?”
“派谁去不都一样吗?”
“这是去参加比赛,不是去赶街。”
“派哪个去,还是要报个名单的。”他心里明镜似的,派谁去都一样,二十多个娃都不会写作文。
“还是回教室说吧。” 他的眼神是在商量,也在企求,猪肚子饿般的企求。
孩子齐刷刷的,把纯净地如山泉水般的眼睛投向叫李老师的女人。
“回去吧”,女老师吆喝了声。
孩子脚没动,刀子还在手上。
“快点回,怎么还一个个不情愿,是想剁猪食吧……不要怕,只要不好好念书,一辈子就可以在这沟沟里放猪讨猪食……”她那吹了卷发的头,摆起来,是一朵发了霉乌黑的阴云。
“姚桃,你还不回去吗?你不是向你妈告状,说我们不让你念书吗?”
桃子“啊”了声,又“噢”了声,感觉还是不对,脸颊不白不红了,放下刀,提着脚跑回教室去了。
其他同学也跟着一窝蜂回了。
“就叫姚桃去吧,我看她个子最高,也最憨,写不好也不光我们的事……”
“就这样定了,让她去……”
这对老师夫妻,当时在桃子看来,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就像看父亲打母亲久了,心疼是心疼,还是觉得男人打女人,也不是父亲的首创,东村的婶西寨的嫂,也天天活在自己男人的拳脚下,也看不出生活的一点点破绽,每天的太阳都走着点儿升起,走着点落下。只是多年后,这对夫妇儿子的夭折,隐隐约约的,桃子觉得有一些善恶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