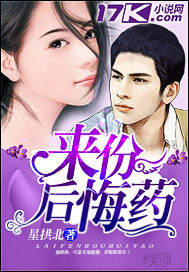公司里的人听说老板病得如此严重,纷纷吵着要过来看他,还是阿路临时做了通知,老板至今未醒,还是不要打扰他休息。
午饭时间转眼将至,未以家里做饭的阿姨送来了温热的白粥,意薇下午还有课,先回学校了;阿路在公司为未以分配工作,毕竟一个人做怎么多实在不好,还好他们公司的人都算善解人意,财务部的女孩子也后悔不已,声称要加班完成。
想到今天就是元旦,未以却身处医院,袁雉的心里有些难过。
不过难过一下子就被治愈系的依兰给打破了:
“袁雉!!你竟然偷偷开溜了!!你知不知道我刚找好衣服换好准备和你出门,一出来发现你人不在了,就剩下电视还在响,你知道我一出来听见‘我真的真的不能失去你!!’这个声音是什么感觉吗?!袁雉!!你不给我解释清楚晚上别想回来!!”
袁雉听到这,尤其是依兰模仿的那段娇嗔的声音,顿时心情好了许多。
“对不起啊依兰,未以他生了很严重的病,我脱不开身 .....”
“重色轻友啊重色轻友,我才不管你,别忘了吃饭,别一激动连饭都没胃口吃。”
虽然每句话都是这么毒舌,但也十分暖心。
好朋友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依兰,我 ....谢谢你。”
那头的依兰一愣,自言自语道:
“真是个单细胞啊,连谢谢都那么简单粗暴。”
“算了,我去找周亦歌去。”
依兰结束了和袁雉的通话,开始给亦歌打电话,那边有些吵,亦歌问道:
“怎么了,依兰?”
“袁雉去医院照顾钟未以了,没人和我逛街了,我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
亦歌的面色一怔,苦笑了一声,答应道:
“好。”
原来她还是放不下钟未以,可我在她心里,又算什么呢?
袁雉,真的要我为了得到你而不择手段吗?
只要能让你在我身边,这又有什么关系?
袁雉用汤匙轻轻地将白粥舀到碗里,仔细地吹吹,一股沁人的米香在周围飘荡,她放下碗,小心地晃晃未以的身体,轻声喊道:
“未以,未以,睁开眼看看我,起来吃饭了。”
“快啊,我给你带了很好喝的粥,养胃的,这样你就不会很难受了。”
一分钟以后,床上的男人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看袁雉,他的嘴角扯了扯,像是梦呓一般小声自言自语道:
“是不是又做梦了,怎么这么真实呢 ....”
袁雉的眼睛里泛起了雾。
“你没做梦,我就在这里啊。”
她拿起未以的手,用他的食指带着他一点一点地触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未以睁大眼睛,可是布满的血丝又暴露了他的疲惫。
“真的不是梦吗?”
他虚弱的声音,差点让袁雉掉下眼泪。
“不是,真的不是啊。”
袁雉使劲再靠前一点,吻上未以的唇,他的口腔里满是药水的苦涩,袁雉闭上眼,握着未以的手越来越热,趋于温暖,她感觉未以仔细地舔舐着自己口腔内的每一处,温柔,心动。
“喝粥好不好?”
袁雉轻轻放开他,笑容四溢地问道,一丝丝宠溺。
“嗯。”
每一口,都是你亲手送进我嘴边,哪怕我再难受,也要把它喝得干干净净啊。
我时常在想,只要有你,爱与不爱又怎样?
袁雉,也许有一天,我会甘愿为你放弃我的所有。
喝完粥,未以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袁雉不动声色地给他擦擦,又测了测未以的额温,烧还没退,她有些着急了。
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心口侵蚀着,她从未想过如此挂念一个人是这样心痛。
那种甘愿为他承受一切的力量,在心里日渐萌发。
袁雉从未感觉过那种心如刀绞的疼痛,就好像把五脏六腑都扯出来细细磨碎,痛到极致。
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人替他承受这一切,她宁愿这个人是她自己。
未以,你不是我,怎会懂我的难过失落。
袁雉倒了一杯滚烫的白开水放在桌上,未以渐渐闭上眼睛,还时不时地握住袁雉的手,眯起眼转头瞧瞧她还在不在。
她从未想过,未以对自己是这样依赖。
时间一分一秒不停地转动着,滴滴答答,转瞬即逝。
眼看将要天黑,夕阳流连忘返,羞红了脸颊,袁雉已经在病房里待了整整一天了,她伸了伸懒腰,小心松开未以紧握着的手,盖了盖被子,转动轮椅来到阳台。
从楼上看去十分美丽,一片白茫茫,素雅又沉静,袁雉想到过了今天就是新的一年,嘴角不知不觉上扬。
未以怎么也抓不住袁雉的手,他连忙睁开眼下床走到袁雉身后,然而脸上却是异样的潮红,袁雉吓了一跳,看着未以单薄的衬衣略显清冷,一边埋怨一边把外套拿过来递给未以,看他穿上才勉强允许他和自己看日落。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未以重新握住袁雉的手,垂着眼轻轻说道。
“嗯。”
袁雉转头看了看未以,而未以呢,有些虚弱地紧紧扶住轮椅,出现昏厥前的征兆。
“赶快好好睡一觉吧,不睡觉你的烧恐怕不会退的。”
袁雉把未以推到床上,责怪道。
“我不睡,我一睡着你就会走,我不睡 ....”
未以喘着粗气说道,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袁雉有些生气地把他一使劲摁在床上,又一把把被子扯过来给他盖好,凶道:
“你再任性我就一定会走,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的吗?!我说过不会走 .....”
袁雉仔细一看,未以已经陷入沉睡。
我说过不会走,就一定不会走。
.
.
.
.
.
.
和依兰分别以后,亦歌悄悄来到医院,瞧了瞧病房里昏暗的蓝色灯光,一丝冷清荒凉,他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袁雉的背影,盯着看了好久,直到一个护士朝这边走来,他叫住护士,问道:
“这个病房里的病人得了什么病?”
“好像是支气管扩张伴高烧咳血,挺严重的。”
护士打量了亦歌一下,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就全盘托出。
“你是去做什么?”
亦歌指了指护士推着的小铁车,问道。
“刚才有个坐轮椅的女孩过来告诉我,给他打一剂镇定剂,说病人情绪有些不稳定,我进去打针。”
亦歌点了点头,向护士道谢之后悄悄走进没上锁的药房。
粗心的护士,监控盲区。
他仔细又快速地寻找着,直到看见一瓶注射药的说明书上清楚写着“不能与镇定剂同用”的字样,才悄悄取出一瓶,放在正好去洗手间的护士的小铁车上,换走了一瓶止痛注射药。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想到未以被送进抢救室的情景,他感觉很爽。
我说过,我会不择手段。
亦歌又去门诊部买了一瓶安定片,不就水吞下,冷笑着走出去。
袁雉,这一切的错误来源,都是于你。
“小姐让一下,我给病人加药。”
护士推门而入,打开灯,刺眼的灯光照得眼睛有些疼,袁雉把手机放到一边,默默地退到一旁,看着护士迅速地配好药,用皮筋扎住未以的手腕,摩挲了几下之后,冰凉的针尖扎进血管,未以微微皱了皱眉,没有醒来。
待护士离开之后,袁雉回到未以身边,将他吊着水的手小心翼翼地放进被子里,摸了摸他的脸,病房重新陷入昏暗中。
约莫半个小时,黑色的天际开始绽放烟花,想必依兰那边也开始狂欢了吧,袁雉托着腮发愣,沉静房间里,呼吸声越发急促。
“未以,未以,怎么了?”
袁雉才发觉有些不对劲,轻轻推推他,问道。
“好难受 ....”
未以捂住心口,回答道。
袁雉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几乎使出全身力气驱动轮椅冲到门口,大声地喊着护士,而未以渐渐地趋于死亡一般的平静。
医生从办公室里慌张跑到病房,探了探未以的鼻息,又看了看垃圾桶里的药瓶,立刻伸手拔掉针管,和几个护士一齐把未以推到隔壁抢救室,门口的红灯迟迟不变绿,袁雉今天第一次掉眼泪。
未以,你千万千万不可以有事。
如果你有了什么事,我恐怕一辈子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
过了一会儿,刚才的那个医生走出来,袁雉赶忙上前,医生摘掉口罩,看了看袁雉焦急的神色,安慰道:
“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是因为药物相克引起的暂时性心肌缺血,护士说她并没有拿错药,所以现在我要去监控室看监控,还这件事情一个真相,袁小姐要不要一起去?”
袁雉望了抢救室的门一眼,点了点头。
不算清晰的录像上,可以依稀辨认出人影,只有短短三秒,只能看见他身穿黑色外套,动作娴熟不慌张,这不是——周亦歌吗!?
袁雉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这个人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情院方已高度重视,想要采取报警的方式解决,袁小姐意下如何?”
医生一边关掉监控录像,一边问道。
“我 ...别报警了,这件事影响不好,再说钟老板在商业界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传出去不好听,再说仇家暗算也是常有的事。”
亦歌,你为何要做这种事?
如果你真的对未以不利,不光是整个社会原谅不了你,我不会原谅你。
我该说,你变了吗?
你变了,是什么让你变得面目全非,是什么让你如此狠心残忍?
可怕的不是你不愿回头,而是你明知道我的心意,却还是装糊涂,伤害我爱的人。
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愿意消失。
可是我偏要任性地履行一点。
我所深爱之人,定当尽全力去保护。
“那好吧,以后多小心啊,这也是医院的疏忽,再次向你和病人道歉。”
亦歌,我决定给你一次机会。
袁雉还是没狠下心,也许亦歌是有苦衷吧,她也不知道这是慈悲还是傻,就算是傻,傻一次就好了,总比伤害他要强。
大不了,过几天去找他。
医生细心地送袁雉回病房,未以早已安顿好,正沉沉地昏睡着,袁雉过去拂了拂他的头发,折腾了一天,他一定累了吧,还好不烧了,不烧了就好,再吊几天水,就可以出院了。
意薇晚自习将尽,这件事还是不要告诉她了吧。
她视哥哥如命,一定不会饶过亦歌的。
“袁雉 .....”
未以梦呓。
“我在。”
袁雉轻轻回答道。